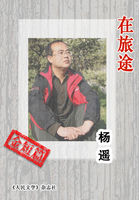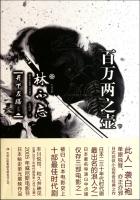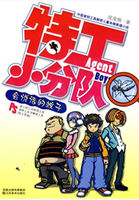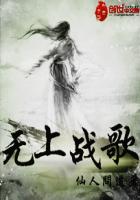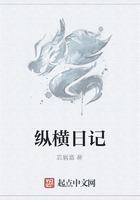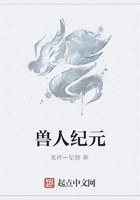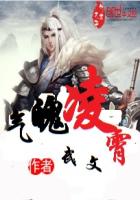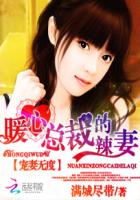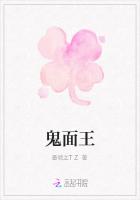佩卡拉已经彻底迷上了这份差事,他阅读着那些陌生的手脚和脸孔,猜想他们活着时候的样子。如同人的穿着,****的身体本身也会透露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握着死去教师的手,在中指上摸到一个突起,那是平日里自来水笔靠着的部位,天长日久,骨头也被磨出了坑。渔夫的手满是厚厚的茧,交织着刀伤愈合后留下的疤痕,摸起来就像皱巴巴的草纸。眉骨和嘴角是否有浅浅的凹槽,则可以表明死者生前是过得衣食无忧,还是常常被责打,过得悲惨凄凉。佩卡拉看着死者的时候,心里完全没有恐惧感,反而萌生出探寻未知之谜的渴望来。
殡葬这份差事并不轻松,很少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不过这一行往往得到人们的尊重。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但又离不开人们的生活。换句话说,不是为了满足死者的要求,而是为了让生者能保留美好的回忆。
母亲的想法则大不一样。她从来不下到处理尸体的地下室来,她只走到台阶的一半处就停住脚步,冲着下面嚷嚷,或者吼着父子俩上来吃晚餐。佩卡拉已经习惯母亲在台阶上露出的半截小腿,圆鼓鼓的膝盖,和看不见的上半截身子。他已经习惯了母亲的嗓音,沉闷地从掩住口鼻的抹布后面艰难地传出来。她看起来有些恐惧,生怕屋子里的空气会钻进她的身体,夺走她的灵魂。
母亲天生就迷信这些。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光秃秃的冰原上度过的,严酷的环境教会她,就算是生火时冒出的烟,都有独特的含义。佩卡拉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向他描述过身披伪装色羽毛的雷鸟躲藏在布满青苔的岩石堆里,被一千年前熄灭的火苗熏得黑黑的石块,或者是一片貌不惊人的洼地,在暮霭中显出清晰的轮廓来告诉人们坟墓的准确位置。
从母亲那里,佩卡拉学会了对细节的观察和过目不忘的本事,其中有些细节用肉眼难以辨别,纯粹要依靠直觉。而从父亲身上,佩卡拉学会了耐心,哪怕在一堆尸体当中,也能处变不惊。
这样的世界,才是佩卡拉应该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有熟悉的街道,湖水倒映出蓝天,远处茂密的松树林,犬牙交错地勾勒出地平线。
可惜事与愿违。
年轻委员造访过的第二天清晨,佩卡拉点燃了小木屋。
他站在林间空地上,看着黑烟翻卷着冲上天空,耳边传来木头断裂的噼啪声与火舌肆虐时的呼哧声。一股灼热感仿佛穿透他的身体,有几颗火星溅到了衣服上,他用手指轻轻把它们弹掉。油漆桶还在木屋的旁边,桶里的油漆被火点着了,吐出黄色的火舌来。房梁被烧塌了,“轰”的一声压在他亲手制成的桌椅和床上,在曾经的那些现实世界如梦境般遥远的日子里,它们是他生活中忠实的伴侣。
唯一没有被投入火海的,是一个用麋鹿皮自制的小包,上面有鹿角制成的扣子。包里面,静静躺着手枪、书和翡翠之眼。
等到一切都烧尽了,只剩下还在冒烟的火堆,佩卡拉转身朝小道的起点走去。一眨眼的工夫,他已经不见了,像游魂飘入林间。
数小时后,他钻出密林,踏上伐木工人进山的路。采伐下来的原木整齐地堆在路边,足足有十英尺高,等着被拉到古拉格的木材厂去。剥下来的树皮像地毯一样铺在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木材特有的酸臭味。
佩卡拉看到了年轻委员口里提到的车。
这辆车的样子他以前从未见过,圆形的引擎盖、小挡风玻璃、像眉毛一样弯曲的发动机散热窗,看起来有些高傲的样子。散热窗上有蓝白相间的小格子,这便是时人熟悉的嘎斯车。
车门开着,基洛夫中尉躺在后排座位上睡着了,胳膊还举在半空中。
佩卡拉抓着基洛夫的脚,晃了晃。
基洛夫尖叫了一声,径直冲出车厢站在路边。好一阵儿,他惊恐地看着面前这个满脸胡须、衣衫褴褛的人:“你把我给吓坏啦!”
“你不是要带我回营地吗?”佩卡拉说。
“不,不是营地。你的刑期结束了。”基洛夫示意佩卡拉坐到后排座上,“至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车子匆匆地拐了几个急弯,终于调转车头,朝着遥远的什利谢利堡开去。在像洗衣板一样坑坑洼洼的路上跌跌撞撞走了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开出了森林,来到广袤无垠的田野。四周太平坦了,让佩卡拉突然感到莫名的紧张。
一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基洛夫一声不吭,只是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看看佩卡拉。那样子就像个焦虑的出租车司机,生怕乘客付不起车钱。
他们经过已经成为废墟的村庄。茅草顶的小屋张开了口子,像极了受伤的马背。地上空空如也,反衬出用白色涂料刷过的墙壁。百叶窗松松垮垮地搭在铰链上,啮齿类动物活动过的痕迹随处可见。村庄后面是沉睡的田野,偶尔有几株高大的向日葵,从杂草丛生中倔强地伸出头来。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吗?”佩卡拉问。
“都是那些反革命分子和所谓的‘美国救援机构’干的好事,他们从西方渗透进来,打着新经济政策的幌子搞破坏。”基洛夫的口中连珠炮似的蹦出一连串词句。
“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佩卡拉继续问。
“他们现在都待在什利谢利堡。”
终于到达什利谢利堡,佩卡拉从车窗向外望去,道路两旁都是匆匆搭建起来的营房。框架看起来还比较新,但是毛毡屋顶已经开始剥落。大部分营房都空荡荡的,看起来当地唯一关心的是修建更多的营房。男男女女的建筑工人停下手中的活儿,好奇地看着嘎斯车从身边开过。漫天的尘土附着在他们的双手和脸上,像带上了灰黑色的面具。有的工人推着车子,其他人的手里握着大号的铲子,铲子上放满了砖块。
田里生长着大麦和小麦,不过对现在的季节而言,栽种得太晚了。本应该是一片深及膝盖的长势喜人的庄稼地,却还没有没过普通人的脚踝。
车子停在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门口。这是这里唯一用石块筑成的建筑物,安装了铁栅栏的小窗,看起来像猪仔明亮的眼睛,一扇厚重的木门上加装了防御用的金属条。
基洛夫关掉引擎。“我们到了。”他说。
佩卡拉走下车的时候,路边的人不约而同地扫视了他一眼,又赶紧把视线转开,仿佛觉得如果跟这个陌生人有联系的话,便会带来牢狱之灾。
他朝大门走去,走上三级木质的台阶,径直来到大门一侧。一个身着黑色制服、佩戴********的男人,正急匆匆地走出来,手里还拽着一个老人的后颈。
老人的脚上套着用白桦树皮做的拖鞋。警察粗鲁地把他从台阶上推了下去,踉踉跄跄之后,老人“扑通”一声扑倒在地上,扬起一阵黄色的烟尘。一把玉米粒样的东西从他紧握的手中撒落在地,就在老人把玉米粒从地上一颗颗捡起来的时候,佩卡拉惊讶地发现,那其实是老人被打落的牙齿。
老人挣扎着站起身来,冲着警察怒目而视,极度的愤怒让他说不出话来。
基洛夫把手放在佩卡拉的背上拍了拍,示意他继续朝前走。
“又抓来了一个?”警察一把抓住佩卡拉的胳膊,手指往衣袖里摸索,“这一个又是何方神圣?”
佩卡拉的哥哥离家去芬兰军团的六个月后,从圣彼得堡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寄给佩卡拉父亲的,签发人是芬兰军团卫戍部队的指挥官。电文如下:佩卡拉·安东暂停军官培训资格。
父亲手握这份薄薄的黄色纸片,面无表情,然后把纸片递给妻子。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道,“暂停资格?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表述。”她捏着电文的手在颤抖。
“意思是,他被踢出军团了,”父亲说,“很快就会回家了。”
第二天,佩卡拉从马厩里挑了一匹马,套上双人马车,去火车站等进站的火车。接下来的两天,他每天都去车站等着。足足有一周的时间,佩卡拉来回奔波,看着乘客们从车厢鱼贯而出,仔细搜寻自己哥哥的身影,直到火车吐着粗气开出车站,只剩下他孤零零地站在月台。
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佩卡拉发现父亲的样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像一个老旧的钟表,虽然外表看不出异样,但机械部分已经失灵,内部已是千疮百孔。父亲在意的并不是导致安东被逐出军团的原因,而是驱逐行为本身,打乱了他为全家精心谋划的发展蓝图。
整整两周,安东音讯全无,佩卡拉也不再去火车站。
又过了一个月,看来安东是不会回来了。
父亲给部队发了电报,想询问儿子的情况。
部队回了封信,信上提到安东被护送到兵营的门口,给了他回家的火车票和餐费,之后人们再也没看见他。
父亲又发了电报,询问安东被驱逐的原因,电报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
伤心的父亲变得愈发沉默寡言,看上去只剩下一具会移动的躯壳。母亲倒是很镇定,坚信儿子等到时机成熟就会返乡。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信念也开始动摇,消失殆尽,像海里的玻璃,在海水和泥沙的裹挟下被磨成了粉末。
有一天,差不多是安东失踪的三个月后,佩卡拉和父亲正忙着对一具尸体做最后的加工润色,以供死者家属瞻仰。父亲俯下身子,用指尖梳理着死者的睫毛,忽然间长吸了一口气,就像腰部的肌肉抽搐了一样,然后他直起身说:“你得出发了。”
“出发去哪里?”佩卡拉问。
“去圣彼得堡,参加芬兰军团。我已经帮你把申请文件都填好了,十天之内,你就去部队报到,取代你哥哥的位置。”父亲竭力避免提到安东的名字。
“我还没有学完你的本事,家里的生意怎么办?”
“都结束了,孩子,没什么可商量的。”
一周后,佩卡拉靠在东去列车的窗口,与父母挥手告别。老两口的面容到最后只剩下粉红色的小点,层层叠叠的松树吞没了车站的小房子。
佩卡拉直视着警察的眼睛。
好一阵子,警察迟疑着要不要发作,他很纳闷竟然有犯人胆敢与他对着干。警察的嘴角紧咬着。“看来应该给你吃点苦头,免得这样放肆。”他低声说。
“这个人受特别行动局的保护。”基洛夫说。
“保护他?”警察大笑起来,“就这个流浪汉?他叫什么?”
“佩卡拉。”基洛夫回答。
“佩卡拉?”警察松开拽着佩卡拉的手,好像扔掉一块滚烫的烙铁,“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佩卡拉?”
台阶下面,老人还跪在地上,注视着警局门口台阶上戏剧性的场面。
“你倒是说呀!”警察吼道。
老人仍在原地。“佩卡拉。”他念叨着这个名字,殷红的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来。
“给我滚远点,该死的!”警察咆哮着,他的脸涨红了。
老人终于爬起来,顺着公路朝前走了,每走几步,便回过头来看佩卡拉一眼。
基洛夫和佩卡拉推开警察,走进警局幽暗的长廊,微弱的光线透过焊了铁栅栏的窗户照进来。
基洛夫一边走,一边扭过头来瞅着佩卡拉。“你究竟是谁?”他问。
佩卡拉没有回答,他跟着年轻委员的脚步来到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门半掩着。
基洛夫站在门边。
佩卡拉走进了房间。
一个人坐在房间角落的桌旁,桌子和他坐着的椅子看起来是房间里唯一的家具。从军服上佩戴的肩章,不难看出他是个红军指挥官。一头黑发精心地从脑门朝后梳理,还特意弄了个分头。他双手交叉端坐在桌前,好像等着摄影师来照相。
“安东!”佩卡拉喊道。
“欢迎归来。”安东应了一声。
佩卡拉目瞪口呆地看着哥哥,而安东也慢条斯理地望着他。等到相信眼前的一切不是恶作剧,佩卡拉转身拔腿朝门外走去。
“你要去哪里?”基洛夫说,追上去抓住他。
“随便哪里都行,”佩卡拉说,“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委员的声音有些慌乱。
警察还站在门口,神情紧张地望着门前的马路。
基洛夫把手搭在佩卡拉的肩头:“你还没有跟斯塔克指挥官见面呢。”
“这是他现在的名字吗?”佩卡拉说。
“现在的?”委员的脸上很迷惑。
佩卡拉冲着基洛夫说:“斯塔克不是他的真名,是杜撰出来的,跟我们称呼列宁,还有斯大林一样!人还是那个人,只是新名字听起来比尤里亚诺夫或朱切什维利好听些。”
“听着,”委员打断佩卡拉的话,“我可以因为你这番话就让你吃枪子儿的。”
“你还是找找不枪毙我的理由吧,”佩卡拉说,“那些理由估计更吸引人,或者,让我的哥哥来行刑吧。”
“你的哥哥?”基洛夫惊讶得合不拢嘴,“指挥官斯塔克是你的哥哥?”
安东从房门口探出身子来。
“你也没有告诉我呀,”基洛夫说,“事先就该通知我。”
“现在告诉你也不迟。”安东边说边走到佩卡拉身边。
“那人不是他,对吧?”警察问道,“你是在开玩笑吧?”他尝试挤出一丝微笑,但终于没笑出来,“这个人不会是传说中的翡翠之眼吧?不是都死了很多年了吗?听人说,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仅仅是个传说!”
安东把身子靠过来,在警察的耳根低语了一会儿。
警察咳嗽起来。“我也没做什么呀?”他看着佩卡拉,“没做什么错事吧?”他继续问道。
“要不我们问问那个被你扔到街上去的人。”佩卡拉说。
警察踯躅地走到门口。“这可是我的地盘,”他喃喃自语,“我说了算。”他看着安东,渴求得到他的支持。
安东一脸严肃:“我建议你,趁着还能动弹,闪到一边去。”
警察悻悻地走开了,像一个无人问津的影子。
安东的视线仍旧停留在佩卡拉身上,点头示意他前往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我的弟弟,”他说,“让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
距离两人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十年了。那是在寒冷荒凉的火车站月台,列车满载着犯人开往西伯利亚。
佩卡拉被剃了头,身上还穿着薄薄的米黄色棉睡衣,那是他蹲监狱的时候发的囚服。凛冽的寒风中,佩卡拉与其他犯人挤在一起瑟瑟发抖,等着运囚车ETAP61的到来。大家都沉默不语,越来越多的犯人在月台上集合,围成一个个同心圆,像包裹得紧紧的洋葱头。
太阳已经落山了。车站房子的屋檐下,凝结的冰柱足足有人的胳膊长。狂风在铁轨上肆虐,卷起雪花在空中打着旋儿。月台的两端,背着来复枪的士兵背靠着吐着火苗的油桶。火星不时从桶里飞出来,映红了士兵们的脸庞。
夜深了,列车姗姗来迟。两个守卫分别站在打开的车门的两边,佩卡拉爬上车的时候,碰巧回头看了一眼车站的房子。在油桶燃烧的火焰旁边,一个士兵正伸出冻得通红的双手,放在火上取暖。
他们四目相对。
佩卡拉恍惚中觉得那是安东,但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身后的守卫一把推进了冰冷潮湿的车厢。
佩卡拉握着锋利的刮胡刀,把刀口贴在长满胡须的脸颊上,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以前,他一般一个月刮一次胡子,但是有一天,当他把刀口在皮带内侧剐蹭,想让刀口更锋利的时候,陈旧的刀片终于不堪重负,断成了两截。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从那之后,他有时候****着身子坐在木屋旁边冰冷的溪水里,用小刀把头发一撮撮地割下来。可是现在,他站在警察局肮脏的浴室里,一手拿着剪刀,另一手拿着刮胡刀,反而有些手足无措。
整整一小时的时间里,他打理着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在痛楚中紧咬牙关,用一块洗衣皂狠命地在脸上磨着,期待弄出些泡沫来。他尽可能不去理会房间里刺鼻的小便的气味,呛人的烟味和散落在四周的厕纸。
慢慢地,一个连佩卡拉本人都难以辨认的面孔出现在镜子里。胡须剃干净了,露出一张光滑干净的脸,下巴、上嘴唇和耳根部位也许用力太重,刮出的伤口渗出血来。为了止血,他从布满灰尘的角落捡了些玉米穗,胡乱地敷在伤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