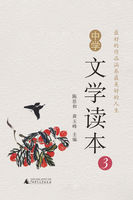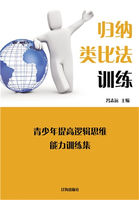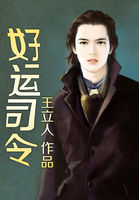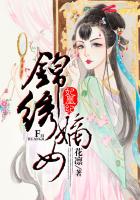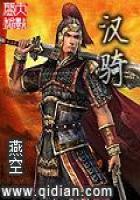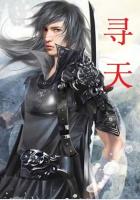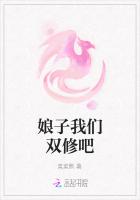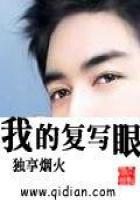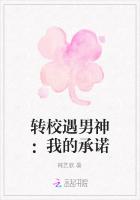(4)小黄脸突然把头一昂……叫了一句:“男子汉们,站起来呀,互相换换座。……”(谭合成《互不知名的旅伴》)
再看两个例子:
(1)他与张三相处得很好。
(2)老王是小李的邻居。
(1)主语是单数,只是一个个体事物,因此用介词结构作状语,介词引进对象,这样句中就不只一个个体事物了。(2)主语也是单数,只是关系存在的一方,因而用定语“小李”显示关系的另一方,从而句子能够成立。
总之,运用关系词时一般要出现与关系词有关联的若干个体来满足关系词的要求。这种出现与关系词有关联的若干个体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我们上举的主宾同现的方法、用复数主语的办法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用由若干个体构成的联合词组作主语的办法(“张三和李四是同伙”)等。
在本文的开头部分我们说,“他是朋友”不能成立。这是因为“朋友”是个关系词,而句中只出现一个个体“他”,不能满足关系词的要求,所以句子站不住。假如我们说“他们是朋友”、“他和小汪是朋友”、“他是小钱的朋友”等,句子则能成立,因为这几句中出现了不只一个个体事物,前一句“他们”是复数,当然不只一个个体,后两句分别出现了两个个体,总之它们都能满足关系词“朋友”的要求。
区分关系词时要注意,有些词在此种语境中反映事物间的关系,是关系词,而在彼种语境中却不是反映事物间的关系,不是关系词。比如:
(1)这位同学,请问到中文系办公室怎么走?
这里的“同学”是“学生”的意思,是非关系词,它只有在表示“在同一学校学习的人”的意思时,才是关系词。
(2)他笑了。
(3)你别笑他,好吗?
(2)“笑”是露出愉快的表情,发出喜欢的声音的意思,是非关系词。(2)“笑”是讥笑的意思,既是讥笑,就有个谁讥笑谁的问题,就是说“讥笑”必须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事物之间,因此它是关系词。
(原载《逻辑与语言学》1989年第3期)
试说“定中重复”的判别
语言表达经常受到经济原则的制约,汉语表达更是如此。汉民族历来崇尚简约,表现在语言风格上便为孜孜追求简约美。古人云“文贵简,言尚省”、“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槐《论文偶记》),“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陈骙《文则》),“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严羽《沧浪诗话》),“意则期多,字唯求少”(李渔《笠翁一家言》),这些论述都显示了汉人对语言风格上简约的美学追求。而“语义重复”则背离了语言的经济原则和我们汉民族特别推崇简约的审美意向,因此成为我们汉语表达中一种力戒的语病。
语义重复从语言的形义关系来说有字面相同的语义重复和字面不同的语义重复。前者字面相同很容易判别,如“我觉得这是想得不对的想法”,而后者则稍显隐蔽,如“这位老向导我不十分清楚他过去的身世,但是从他密密的纹路里,猜得出是个久经风霜的人”。“身世”即一个人的经历、遭遇,当然是“过去”的。因而用“过去”修饰“身世”,便显得多余。
语义重复从语言的结构关系来说有并列式重复、主谓式重复、定中式重复等等。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语义重复问题。
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关系从语法角度而言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定语为中心语的修饰成分。从逻辑学角度而言,定语或是对中心语所表概念的限制,或是揭示中心语表达的概念所反映事物的属性,前者常称作限制性定语,后者常称作修饰性定语或描写性定语。语法学家们通常认为:“限制性定语的作用主要是给事物分类或划定范围,使语言更加准确严密”,“描写性定语的作用主要是描绘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突出其中本来就有的某一特性,使语言更加形象生动”。一般说来限制性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无语义重复的问题,因为限制性定语通常表示中心语的领属、数量、时间、范围、处所等,不直接涉及中心语所反映的事物的某一或某些属性。而描写性定语则不然,它的特征就在于揭示中心语所反映的事物的某一或某些属性,而当中心语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包含有定语所反映的事物属性时,便可能形成语义重复。当然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因为:第一,有些描写性定语也有限制的作用,有些限制性定语也描写的作用,描写和限制有时难以截然分开;第二,人对事物属性的反映情形往往异常复杂;第三,人们判别重复与否的原则和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定中语义重复的判别需要注意区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区分词法层面和句法层面
语法层面有词法层面与句法层面之别。我们觉得语义重复的确认应严格限定在句法层面。那种在词法层面判别语义重复问题的做法应该反对。翻译小说《美国悲剧》(德莱塞原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版)中有这么一句:“那时,一辆辆漂亮的小轿车打从他身边疾驶而去……”杨林成先生认为“打”和“从”作用相当,都是介词,应删去一个,否则冗余累赘,不合语言规范化的要求。杨林成先生在此是将“打从”的使用归入了语义重复的范围。其实“打从”在此为并列式合成词(《现代汉语词典》收有该词,解释为:①自从(某时以后);②介词,表示经过,用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前面),判别为语义重复实在不妥,因为在词法层面寻找语义重复会忽视语言的节律要求,会无限制地扩大语义重复的范围,更严重的是背离了语言的发展规律。如果将“打从”判别为语义重复,则所有的同义词素并列的合成词都得判别为语义重复。推而广之,包含有同义组合的固定短语、准固定短语等语言形式恐怕都得判别为语义重复,而这显然不符合语言运用的事实和语言的发展规律。同样的道理,定中式语义重复也应严格限定在句法层,撇开词法层。例如:“我们期待着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新的征途上英勇善战,以胜利的捷报,为祖国女子排球运动谱写新的胜利篇章。”(《体育报》1982年9月3日)“胜利的捷报”为自由短语,属句法层面的语言形式,“捷报”即胜利的消息,用“胜利”来修饰“捷报”应判别为语义重复。然而“白银”这一定中形式应作不同的处理,虽然“银”就是白色的,“白”修饰“银”却不应看作语义重复,因为“白银”是词,属词法层面的形式。另外,固定短语凝固性强,且具有使用的现成性,类似于词,虽属句法层面,但可与词同等看待,这个层次也无语义重复问题(即使某些固定短语从理论上说是叠架,也不应该认为是语义重复)。
二、区分方言层面和普通话层面
汉语言的使用包含有方言层面和普通话层面的不同,因此汉语言规范化应区分方言层面和普通话层面。在语文实践过程中,如果我们对二者不加区别,混为一谈,就会使得语言规范化的有关论述脱离言语实际,变得空洞教条。朱炳昌先生编著的《异形词汇编》(语文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认为“角落”和“旮旯”是异形词,并且认为前者为标准词形,应该选用,后者为非标准词形,应该摒弃。其实“角落”和“旮旯”并非异形词,它们不属于同一层面,“角落”属普通话层面,“旮旯”属方言层面,二者的使用环境并不相同,将“旮旯”作为规范的对象是不切实际的。而且言语生活中义同“角落”的方言词并不止“旮旯”一个,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方言词“犄角”也有“角落”意,是否也要规范掉呢?
就语义重复的判定来说也应该区分方言层面和普通话层面。凡方言区流行的语言表达形式,从普通话角度看属语义重复的,可从宽处理,不作为语义重复的毛病看待,以区别于一般的语病。杭海路、管锡华主编的《实用语文正误辞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咸盐”词条下有这么一段文字:
语言表达贵在精炼。犯有“重复”语病的句子,往往是出现了多余的说明或修饰。如:“据说,他在审讯负伤被俘的抗联战士时,狠毒地往伤口上抹成盐,让你活受罪……”(《人民文学》1984年第4期)上例中“咸”字属多余的修饰。正如“糖”总是甜的,我们一般不说“甜糖”一样,一般也不说“咸盐”。中心语中已经包含了修饰语的意思,再出现这个修饰语便显得毫无必要,病例中“咸”字应删去。
我们认为定中形式的“咸盐”流行于江淮方言区,不宜判定为语义重复。文中用“咸盐”而不用“盐”的说法,至多只能说作者选择了方言词,而且“咸盐”是一个词(《现代汉语词典》收有该词),属词法层面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也不宜看作语义重复的语病。
三、区分有无渲染、强调的必要
在言语活动中,人们常常运用修饰性成分(定语)来揭示中心成分所反映的事物的某一或某些属性,如“美丽的黄山”、“凶猛的老虎”。这些定语都属描写性定语,它所揭示的是中心成分所反映事物的固有属性,语义重复的毛病在此就可能产生。应该说中心语表示单独概念的定中结构其定语揭示中心语所指对象的固有属性并不形成语义重复。在接受者的心中_,中心语表示单独概念,它的定语就不会是对其限制,不会是通过定语的使用对之进行隐性分类,因而此时接受者就不会产生因限制而造成的对中心语的分类的语义联想,这种定语只起强调、渲染的作用,也就不可能造成语义重复。如“美丽的黄山”人们只接受黄山美丽的信息,不会产生还存在“不美丽的黄山”的语义联想,所以虽然“黄山”包含有“美丽”的属性,但用“美丽”作定语来修饰它,并未造成语义重复,相反用“美丽”来修饰之,更好地突出、强调了“黄山”的“美丽”属性。然而中心语表示普遍概念的定中结构则不同,其修饰性定语揭示中心语所反映事物的属性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语义重复的毛病。此时语义重复与否的判定标准有二:第一、用这种修饰性定语来强调有其必要性;第二、这种修饰性定语的使用并未使人产生有碍于思想表达的对比式的语义联想。例如:
(1)凶猛的老虎让人胆战心惊。
(2)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与德茜蕾的姐姐朱丽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爱了,而此时的年轻少女德茜蕾也偷偷地爱上了拿破仑。(《演讲与口才》1997年第11期)
(1)“老虎”这一概念本身虽然包含“凶猛”的属性,但用“凶猛”来修饰,可以很好地将老虎的这种属性强调出来,因此“凶猛的老虎”不属语义重复。(2)“年轻少女”则不然,“少女”指“年轻未婚的女子”,它已经包含了“年轻”的属性,而且“少”字已明确地显现了“年轻”的属性,因此用“年轻”来揭示“少女”的年轻属性毫无必要。用“年轻”来强调“少女”的年轻属性纯熟多余,而且用“年轻”来修饰“少女”还容易使人产生还有“不年轻的少女”这类有碍思想表达的对比式的语义联想,所以“年轻少女”应判别为语义重复。
(原载台湾《国文天地》2003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吕冀平,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江显芸,概念限制与语词修饰[A],逻辑与语言论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
[3]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汉语言运用的审美追求与汉语的特点
语言是民族的。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与别的民族语言都存在着共同的东西,但也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的东西,亦即特点。民族语言特点的形成,受到很多因素制约,如该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该民族所浸润的文化特质、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审美观念等等。我们认为一个民族语言的特点与该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意识以及表现于语言运用(言语行为)中的审美追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汉语而言,汉民族在运用汉语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同时,汉民族的审美观念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注入其中。当汉语运用过程中种种有意或无意(特别是有意)的审美追求,形成种种集体审美趋向、集体审美无意识,并经过代代相传,就会逐渐形成汉语某些美学特征鲜明的特点。我们认为汉语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汉人语言运用的审美追求。比如汉民族崇尚简约、含蓄,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孜孜追求简约美与含蓄美。“文贵简,言尚省”、“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槐《论文偶记》),“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陈骙《文则》),“语贵含蓄”(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文贵远,远必含蓄”(《论文偶记》),“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严羽《沧浪诗话》),这许许多多的论述都显示了汉人对语言风格上简约与含蓄的美学追求。汉语句法成分的省略极多(有别于西方语言)与这种审美追求极有关联。
汉语言运用的审美追求有众多表现,因而汉语言运用的审美追求与汉语特点的关系也就错综复杂。本文只讨论汉语言运用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来的一种鲜明的审美意向:追求对称与均衡和汉语某些特点之间的关系。
前人与时贤在论述汉文化的特质时都特别强调汉文化尤其注意和谐、有序,讲求对称与均衡的特征。这种对对称、均衡的特别追求与崇尚表现在汉人的哲学观念、建筑意识、文学与艺术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有关论述很多,本文从略)。表现在美学意向上,汉民族特别崇尚对称与均衡之美。这种对称、均衡的审美意向孕育了汉语言运用上强烈的对称、均衡的审美追求。比如汉人偏爱对偶句,汉语言运用中对偶句丰富多彩。对偶句作为汉民族喜闻乐见的一种语言形式,无论是文人拈须还是平民言实;无论是亭客楹联,还是书报标题;从文学艺术到生活用语,可以说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有。汉民族对对偶的偏爱正显示了汉民族语言运用上的上述审美追求。再如,汉语言运用中常见的顶真、回环、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的使用都是对对称、均衡等审美意识的认同与强化。
再从汉人的语感来说,下面这两段文字,虽然语义、语法上并无毛病,但读起来拗口,听起来别扭,原因就在于它们背离了汉语言运用讲求对称、均衡的审美意识。
(1)“反串”的必须是自己行当以外的角色,“扮演”无这个限制。(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影片《泪痕》,歌颂两位********:一位是活着的金县新来的********朱克实,一位死去的是金县原********曹毅。(《光明日报》1980.2.16)
例(1)中“无”与“这个”配合,显得不平衡,“无”是一个音节,“这个”为两个音节,音节搭配不协调。另外,从语体色彩上看,“无”书面语色彩重,“这个”口语色彩重,语体色彩配合也不协调。如果将“无这个”改为“无此”或“没有这个”就均衡、和谐了。例(2)中“一位是活着……”和“一位死去的是……”语序不对称,读起来别扭,产生不了美感。此处“一位死去的是……”宜改为“一位是已经去世的……”,这样语序对称,也就谐和畅达了。
语感是对已往以及当今使用语言的群体对该语言的某种或某些认识的感性体验。“语言的运用,可以整齐的地方就尽量让它整齐,这是汉语古往今来的一贯趋势。”正因为这种对对称、均衡的审美追求,才养育了汉人以对称、均衡为美而以破坏对称、均衡为丑(有特殊表达效果的,有意识的破坏除外)的审美语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