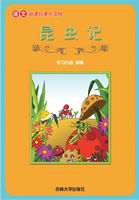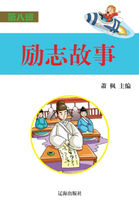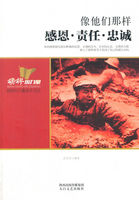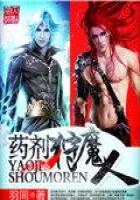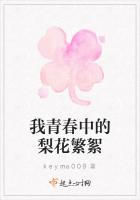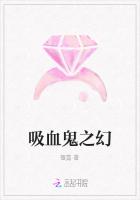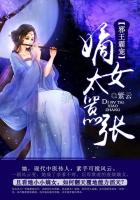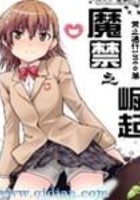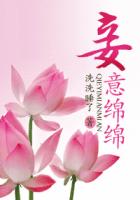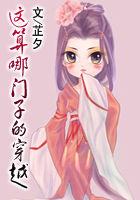对于消极修辞存在于什么样的修辞单位,或者说消极修辞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陈望道先生并未作具体阐述,从《修辞学发凡》的有关内容看主要是词句,但也涉及篇章。邸巨先生在《试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及其关系》一文中认为:“消极修辞的对象只是限于用词、造句、语段,范围太小,应该包括篇章、语体和风格。”林文金先生在《关于修辞的几个问题——兼谈修辞学的范围》一文中甚至认为应将积极修辞中的辞趣归到消极修辞里去,他说:“事实上,从表达功能来看,辞趣和修辞格并不相同,而辞趣和消极修辞的差异不大。正因为这样,解放以后采用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两大分野说的修辞著作,大多数都没有在积极修辞项下立辞趣这个名目,有些则干脆把积极修辞和修辞格等同起来。”
王希杰先生在区分零度、正偏离和负偏离的基础上,把修辞学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零度修辞学——中性修辞学;第二,正偏离修辞学——正修辞学——积极修辞学;第三,负偏离修辞学——负修辞学——消极修辞学。他说“所谓中性修辞学,研究常规修辞现象,一切只求符合语言的和语用的规范,建立修辞的规范标准模式。所谓正修辞学,研究向着积极方向偏离的现象,即研究艺术化的修辞现象,也就是艺术修辞学。所谓负修辞学,就是研究如何克服解决交际活动中的各种各样的负偏离现象,避免降低话语的表达效果的问题。”可见王先生所说的正修辞学相当于陈望道先生的积极修辞,王先生所说的中性修辞学和负修辞学相当于陈望道先生的消极修辞。
从辞规理论来看消极修辞的研究对象为常规的语言表达,其内容包括辞规和辞风两个方面。照吴士文先生的解释,辞规指具有一般功能、一般结构、一般方法,符合一般类聚系统的模式,如列举分承、正面释言等。辞风,指与辞趣相应的,纯属辞的外形的消极修辞,如音节对称、字形清楚、标点正确等。
音节对称。汉语言运用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审美意向:追求对称与均衡,就音节组合来说一般是对称结合。例如不说“这个时”,而说“这个时候”或“这时”,不说“事实胜于雄辩,水落石出”,而说“事实胜于雄辩,水落自然石出”。
字形清楚。书面表达,字形清楚才能准确达意传情,如果字迹潦草,字形难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表达效果。日常生活当中因字迹不清而影响信息传递的事例时有所见,这从反面提供了“字清楚”作为消极修辞一员的重要证据。
标点正确。吕叔湘、朱德熙先生说:“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认识:标点符号是文字里面的有机的部分,不是外加上去的。它跟旧式的句读号不同,不仅仅是怕读者读不断,给它指点指点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有一个独特的作用,说它们是另一形式的虚字,也不为过分。应该把它们和‘和’‘的’‘呢’‘吗’同样看待,用与不用,用在哪里,都值得斟酌一番。”张拱贵先生说:“对于白话文,我们甚至可以说‘标点重于文字’。一个句子里,掉了或错了一两个字,有时还不至于影响整个的句子;可是缺了或错了一个标点,往往使整句成为不可理解,或理解错误。注意文法是包括标点说的。”毫无疑问,标点符号在书面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标点符号使用得正确与否直接涉及语意表达的准确与否、清晰与否,因此标点正确应属消极修辞的辞风家族。例如:
(1)我在武汉听了毛委员演说三个月之后,又在郑州听到了谭延阉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恶毒攻击,什么“糟得很”、“痞子运动”等等。
(2)豫剧演员常香玉同志曾尖锐地指出:现在,年轻演员离开了麦克风,即使在几百个座位的小剧场演出,后面的也听不见声音,这是多么需要加强声音的基本功训练啊!
这两例引自苏培成先生的《标点符号实用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例(1)第一个逗号本应该点在“演说”之后,因为表达者要表达的意思是在武汉听了毛委员演说,过了三个月又在郑州听到了谭延闽的攻击之辞。现在逗号点在了“三个月之后”的后面,很容易使人理解成毛委员“演说三个月”了(其实并未演说三个月)。例(2)最后一个逗号本应为句号,因为“这是多么需要加强声音的基本功训练啊”,不是常香玉的话,是文章作者的评论。原文这样标点会让人误以为此句也是常香玉的话了。
我们认为消极修辞的研究对象为常规的语言表达,或者说常规的修辞现象,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辞规和辞风两个方面(我们所说的“辞风”与吴士文先生所说稍有不同,详见拙著《辞规的理论与实践》中的有关论述)。辞规是消极修辞的各种格式、模式,辞风是常规的修辞现象中还未形成固定格式、模式的现象。至于病例不宜作为消极修辞的主要内容,因为:第一,消极修辞如管病句修改,那么它与词汇、语法、逻辑的界限就不易划清,这样消极修辞的修辞属性难以突显;第二,病例虽然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说关乎修辞,但不一定都是关乎消极修辞,有的病句之所以是病句是因为积极修辞手法运用不当,也就是说有的病例是关乎积极修辞,让消极修辞来管显然不妥。如:
(1)由于多年听不到李老怪“云诗”而深深感觉着文苑之荒芜的庄稼,都在欢腾雀跃、奔走相告了。(《花城》1981年第3期)
(2)红日跃上山巅,霞光万道,晴空万里,烟消雾散,山林金光闪烁;舟来船往,小溪人声鼎沸。时间过得真快,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问:“汽车怎么还不来呢?”(转引自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这两例都是因积极修辞手法运用不当而产生的病例。(1)属比拟不当:把庄稼拟作人,但庄稼并没有“欢腾雀跃、奔走相告”的特征;(2)属映衬不当:陪衬事物与被陪衬事物不合,从容不迫地描写山水景色,又怎能烘托出“焦急的心情”?像这两例之类的病例让积极修辞来管更合适。
我们觉得消极修辞应从正面来研究常规修辞现象,或者说消极修辞重点应是研究零度修辞现象,也就是王希杰先生所说的“中性修辞现象”,至于病句修辞可由修辞学的另一分支——病句修辞学来研究。
从修辞单位来说,消极修辞的范围应涉及音节(字)、词语、句子、句群、段落和篇章。标点符号虽不属语言本身,但它和语言运用紧密相联,消极修辞也应涉及。语体和风格实际上是各种修辞现象共同组成的综合体,不是修辞单位,消极修辞可不研究。语体和风格比较适宜于让两门独立的学科——语体学和风格学来研究。
三、怎样研究消极修辞
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人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剩下来的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研究消极修辞。
以往的消极修辞研究遵循的是《修辞学发凡》论述消极修辞的效果统领方法的体例,也就是以功能为纲,探讨消极修辞手法。《修辞学发凡》从表达效果着眼,把“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匀”、“安排稳密”作为“消极修辞最低的限度,也是消极修辞所当遵守的最高标准”。然而《修辞学发凡》对每种标准只是作了概括论述,或者说只是从“要求”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没有像积极修辞那样归纳出具体的修辞方法,亦即没有从“方法”的角度对消极修辞作进一步的探讨,留下了修辞方式研究不平衡的遗憾。
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消极修辞的研究较已往有所重视,研究视野也有所拓宽,有的研究正例,有的研究反例,有的正反结合;从修辞单位来说有对句子消极修辞的探讨,也有对句群、段落、篇章消极修辞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的消极修辞研究无论在丰富性还是在深入性方面都远远超出了《修辞学发凡》及其以后四五十年的消极修辞研究。但研究消极修辞的方法多数仍沿袭《修辞学发凡》以效果统领方法的体例,也就是以功能为纲的体例。用这种方法研究消极修辞,存在一些弊端:“1.它与积极修辞的表达手法为纲的体例不在一个平面上。2.不同表达效果有时可由几种修辞手法达到,探讨时难免造成手法的重复。3.认定某修辞手段达到了某种修辞效果是凭直觉的感受,科学性不强,探讨时难免造成手法的交叉混乱现象。”
以功能为纲探讨消极修辞,其切入角度往往是“要求”或“改错”,这样研究消极修辞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弊端较多,难以使修辞方式系列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辞规理论,是对以往消极修辞研究理论的完善。它从系统观出发,认为应从“方法”的角度切入,用“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基本上避免了以功能为纲研究方法的弊端,不仅可以完善修辞方式的系统,而且可以使所有的语言片断在修辞方法上都做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
辞规理论所提出的用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其实质就是在《修辞学发凡》的修辞体系中,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进行对比研究,利用积极修辞的研究成果来建立与积极修辞的体系相反相成的消极修辞的体系。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消极修辞有长处也有短处,正如潘庆云先生所说的:“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可以在积极修辞研究的成果上,比较快地建立起一般性修辞的体系,缺点是比较容易受到修辞学中某些传统观念的限制与束缚。”
消极修辞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途径,潘庆云先生曾有一个全新的设想,即结合语体学方法进行,也就是摆脱传统修辞学的桎梏,根据运用语辞题旨情境的不同,把消极修辞分为若干领域,并逐一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消极修辞的整体结构和一般规律。他曾对消极修辞中的法律、诉讼语体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内容包括法律语言的各层次结构分析、法律语体风格分析、法律语言表述规律及法律语言各下属范畴的逐一研究,这些次范畴包括立法修辞、法律文书、法庭论辩、讯问言语、刑事侦查言语等等。但我们认为这种方法难以操作,也难以对所有的言语片断进行全面而科学的修辞分析。
两大分野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但两大分野的术语“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之“消极”与“积极”容易使人望文生义而导致误解,特别是对属于修辞学圈子之外的人更是如此。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赞同两大分野理论的修辞学者在术语的革新上做了种种努力,提出了不少成对的术语,可以说是各有短长吧。如:规范修辞和艺术修辞,平实修辞和艺术修辞,论理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基本修辞和提高性修辞,一般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一般性修辞和特定性修辞,等等。其中“一般性修辞和特定性修辞”是吴士文先生的说法,他在《修辞讲话》(1982年)一书中改“消极修辞”为“一般性修辞”,改“积极修辞”为“特殊性修辞”;在’《修辞格论析》(1986年)一书中,他将“特殊性修辞”改为“特定性修辞”。吴士文先生的“一般性修辞和特定性修辞”之“一般”与“特定”是从语体和语言运用角度或者说是从使用范围和加工方式而言的。
我们认为,在修辞学研究者的小圈子里用陈望道先生的“消极”、“积极”之名,不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两个术语早已有了约定俗成的含义,但如果是在修辞学研究者圈子之外,是面向大众的,那就很有改名的必要了。比较而言,上面几对术语我们更倾向于潘庆云先生提议的“一般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的说法,因为这两个术语能较好地表达出两大分野的“抽象的、概念的”与“具体的、体验的”之间的本质对立。
(原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修辞学与修辞学史论集》,澳门语言学会2005)
20世纪的汉语消极修辞研究
修辞现象“消极”、“积极”名称的使用,最早见于清末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上海广智书局1905)。在“修词现象”一章,龙伯纯引进日本学者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中的观点,把“词藻”称为“修词现象”,并将它分为语彩和想彩两大类。所谓“语彩”,即“言语上之彩色,属于外形的词藻”。所谓“想彩”,即“思想的彩色”,属于内容上的词藻。语彩和想彩又各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所谓消极者,乃“修辞最低之标准,准备上必要者也”。所谓积极者,“乃修辞最高之准备也”。
在龙伯纯之后,王易在《修辞学》(商务印书馆,1926年)和《修辞学通诠》(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两书中对修辞现象也作了类似于龙氏的分类。王易把修辞现象分为消极、积极两部分。前者“思想止求于事理明晰,不求深刻,言语止求与思想切合,不求工丽”,后者“内容为理想之发展,外形为表情之利用”。二者的关系为:“一切文章必先经过消极修辞过程,然后加以积极修辞,方成为美文”;“缺少消极条件之辞并不能成为文章”。王易和龙伯纯一样,也是先将修辞现象分为“内容——想彩”、“外形——语彩”两部分。“内容——想彩”又分为“消极”、“积极”两类。“消极之想彩”包括“命题完备”、“叙次顺序”两种;“积极之想彩”包括“想念增加”(譬喻法)、“想念变形”(化成法,包括拟人、夸张等)、“想念排列”(布置法,包括对偶、复叠等)、“想念态度”(表出法,包括咏叹、反语、警句等),共四种。“外形——语彩”也分为“消极”、“积极”两类,“消极之语彩”包括“行文纯正”、“用语明确”两种;“积极之语彩”包括“语调表情”、“音调表情”两种。
龙伯纯与王易并未将修辞现象两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他们只将消极的和积极的作为外形上和内容上的表现。把修辞现象两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开始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下称《发凡》)所创立的“两大分野”学说。陈望道“两大分野”学说的核心就是将修辞现象大别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并将二者作为修辞的总纲,以此来贯穿区分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的始终。陈望道认为:“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对于语言一则利用语言的概念因素,一则利用语言的体验因素。对于情境也一常利用概念的关系。一常利用经验所及的体验关系。一只怕对方不明白,一还想对方会感动、会感染自己所怀抱的感念。”他同时还认为消极修辞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法,是积极修辞的基础;积极修辞手法是消极修辞手法的形象化,积极修辞必须以消极修辞做底子,它只有在需要把话说得生动形象时才用得上。
《发凡》问世以后,对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学说影响很大,不少著作采用了《发凡》“两大分野”的体系,把修辞现象一分为二,分别总结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规律,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研究,尤其是积极修辞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仅对20世纪汉语消极修辞的研究作一宏观审视,以之为汉语消极修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