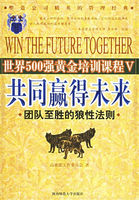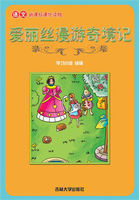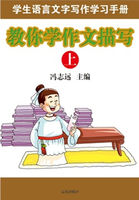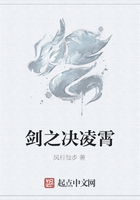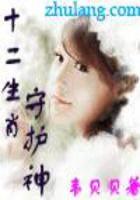一会儿能分析,一会儿又不能分析。十句中,能够分析出来的只有几句。那另外几句呢?不知道是什么修辞方法了。另外几句有三个可能:第一,都是积极修辞,但我们还未研究出来是什么积极修辞;第二,都是消极修辞;第三,其中有的属积极修辞,但我们还未研究,有的属消极修辞。
这说明一个问题:还有很多修辞方式我们还未很好把握,甚至还未研究,特别是消极修辞。如果上面几句都是消极修辞的话,用原有的“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匀”、“安排稳密”来分析,肯定会遭人反对,因为它们与修辞格并列很不协调,而且关系紊乱。如:
第一句(比拟),第二句(意义明确),第三句(比喻),第四句(伦次通顺),第五句(反问),第六句(词句平匀),第七句(安排稳密),第八句(回环),第九句(意义明确),第十句(夸张)。
很明显,一、三、五、八、十句是从“方法”上进行分析的,而二、四、六、七、九句则是从“要求”上进行分析的。它们角度不同,层次不一,难以同列于一个平面。因而就言语事实全面分析来说,修辞方式,特别是消极修辞方式仍需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
总之,无论是修辞方式理论体系的完善,还是言语作品的全面分析,都向修辞研究提出了要求:第一,必须重视消极修辞的研究;第二,消极修辞的研究必须另辟蹊径,“从研究上要来一个转向,要为全面分析而研究,要立足于方法的研究,即把从‘要求’着手的研究转移到从‘方法’上着手的研究”。
有鉴于此,吴士文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辞规”与“辞风”这两个概念作为消极修辞的下位层次与积极修辞的“辞格”和“辞趣”对举。吴士文先生对消极修辞体系的构想,不仅为人们研究消极修辞指明了方向与途径,而且还丰富、充实了整个修辞学体系:
修辞方式:消极(一般性)修辞、积极(特定性)修辞
一般性修辞:辞规、辞风
特定性修辞:辞格、辞趣
“辞规”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但可以强化消极修辞的规律性,而且还可以避免消极修辞研究中所出现的弊端,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说到消极修辞理论体系的完善,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早在吴士文先生之前就有少数学者对此做出可贵的努力了。比如1963年,东北师大中文系在编写教材和语言学名词解释的工具书中,就提出了把消极修辞的规律和手法叫“修辞律”这一术语,以此和积极修辞的手法“修辞格”对应。1979年,宋振华、王今铮两位先生在《语言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中,专门论述了“消极修辞和辞律”、“积极修辞和辞格”的内容。消极修辞的辞律分为同语音有关的辞律、同词汇有关的辞律、同语法有关的辞律三个方面。
1984年宋振华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吉林人民出版社)将一般修辞(即消极修辞)的各种规则简称为“辞律”,并将辞律概括为两种,即词语选用的规律和句式选择的规律。
不过,提出“辞律”这一术语的学者们仍是从“要求”的角度来研究消极修辞,而不是像研究辞格那样从“方法”角度来研究。比如上述《现代汉语修辞学》就将“词义要确切”、“感情色彩要鲜明”、“语体色彩要谐调”等看做辞律。这种从“要求”的角度来概括消极修辞的规律、模式,角度与积极修辞的规律、模式的概括不同,因此无法做到整个修辞方式的系列化,而且会出现很多弊端。
吴士文先生提出辞规理论的出发点如上所言,一为完善修辞方式理论体系,二为全面分析言语事实。应该说这两个出发点的明确有助于研究更趋科学与严密。但是吴先生特别强调“为全面分析而研究”,强调“使所有的语言片断,在修辞方法上都能做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这就使得辞规研究比较适合阐释式的作品分析,而对说写的指导则退到次要的位置了。这是一个缺陷。当然,这个缺陷不只是辞规理论的缺陷,更是整个修辞学的缺陷。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曾经说过“修辞对写说的缘分最浅”。这句话曾得到叶圣陶先生的称赞。叶先生认为这句话很精当,也很实事求是,不像有些人一味吹嘘自己的东西。1962年11月19日陈望道先生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解答有关修辞学问题时又说:“其实,修辞与阅读欣赏的关系最大,对写说的作用则次之,修辞学家的修辞不一定好,因为写说是要适应题旨情境的,只有适应当时的题旨情境的修辞,才是好的修辞。”1962年12月17日陈望道先生在复旦大学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过类似的话:“我认为修辞对阅读和欣赏的帮助,比对写说的帮助更大一些。因为随机应变的技巧,不能告诉,而原则却是可以告诉的。”陈望道先生的这种修辞学思想得到很多后来者的认同与实践,可以说整个修辞学偏重于静态的分析,而缺少动态的探求,缺少言语生成的揭示。这不能不说是修辞学整个学科功能上的重大缺憾与缺陷。“随机应变的技巧”能不能告诉?修辞与写说能不能密切起来?看看修辞学的近邻口才学,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认为修辞学的两大功用,应调一个个儿,即首先是有助于写说,然后才是有助于阅读与欣赏。本来修辞就是一种言语行为,修辞学理应揭示言语生成的技巧,修辞学就要告诉别人有用的修辞术。如果修辞学永远“与写说的缘分最浅”,修辞学将永远难以得到认同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辞规理论的出发点就不能只是完善修辞方式理论体系,全面分析言语作品,还应增加一个,即:揭示言语生成的技巧。
二、“辞规”理论的修辞观
从修辞学史上看,修辞学者的修辞观并不完全相同。人们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认识多有不一。如果粗略一点考察,大体可以分为严、宽两派,严派认为修辞就是对语言的美化。他们只承认形象生动、有魅力可言的是修辞。这种修辞观可称为“美辞观”。下面这些认识大体可归为“美辞观”:
1.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惟求达者殊科。(杨树达《中国修辞学》,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
2.文法者,言语律也;逻辑者,思想律也;发诸心,出乎口,何如斯为当,文法、逻辑之事也;修辞学则不惟欲其当,必使吾之言说何如斯可以晓人而动人……故示文章之破格或正格,文法之事也,而修辞则在别文章之美恶。(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中华书局,1932年)
3.修辞学的使命在:“美感”或“欣赏”。……修辞学最大最重要的功用在创造优美的言辞。(黄庆萱《修辞学》,台北三民书局,1975年)
4.朱星先生于1957年出版的《语言学概论》关于“修辞学的基本概念”一节,把修辞看作是“讲词句的艺术加工的法则”,“目的是要求词句在语法的基础上合乎艺术的美化与表达的效果”。他认为“修辞研究的对象是艺术性的语言”。
当代著名修辞学家谭永祥先生是美辞观的突出代表。他的美辞观最为直接明了。他认为,“修辞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言语艺术,是言语和美学相互渗透的产物”。详而言之:“修辞,是理性、情感和美感等信息量丰富甚至超载的言语现象,也称修辞现象。把理性、情感和美感等信息最大限度地注入载体,叫修辞活动。研究修辞现象和修辞活动的规律的科学叫修辞学,亦可称为言语美学或修辞美学。”谭永祥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修辞学研究消极修辞,在《汉语修辞美学》一书中态度坚决地认为:“消极修辞正是为了‘求达’,理当属于语法(文法)的范围。”他认为:“修辞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辞格和辞趣,因为只有辞格和辞趣才是属于‘理性、情感和美感等信息丰富甚至超载的言语现象’,是一种言语美学,或日修辞美学。舍此,都不是修辞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是属于别的学科,尽管它们大都是修辞学的左邻右舍。”
宽派的突出代表是陈望道先生。陈先生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修辞现象,即在修辞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具体的语文现象。
言语成品(一篇文章或一席演说)的形成,大致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收集材料;第二,剪裁配置(主要是确定主题和取舍材料);第三,写说发表。第一阶段“是与生活经验及自然社会的知识有关系”,第二阶段“最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等等有关系”,这两个阶段是修辞的前提,也是修辞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它们还不是修辞本身。这第三个阶段才是修辞的所在。第三阶段写说发表的全过程,就是修辞的全过程。《修辞学发凡》对这个过程有一个说明:“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晃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由此可见修辞现象产生于修辞过程之中。修辞过程有长短之别,短的可能“随笔冲口一晃就过”,长的可能“添加涂改穷日累月”。但不论过程长短,只要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语文现象,都是修辞现象。
修辞现象在人们的写说中无处不在,只要人们开口说话,动手写文章,这种现象便会产生。陈望道先生认为:“每一句话都可以看作文法现象,也都可以看作修辞现象。文法是讲语文组织的,一句话的主语、谓语等就是讲语文组织的。修辞是语言文字的运用,一句话里凡是与运用语言文字有关的现象,包括运用语文组织规律的现象,都可当作修辞现象。比如‘我吃饭了’、‘我把饭吃了’、‘饭我吃了’这三个句子,从语文组织规律上看,都是文法现象;从对语文组织规律的运用上看,又都是修辞现象。”“有人认为凡是明白通顺的句子只有文法,没有修辞。其实明白通顺的句子也是对语言文字的一种运用,所以也是修辞现象,不过它不是积极修辞现象,而是一种消极修辞现象。”
“辞规”理论的修辞观属于宽派修辞观。它认为一切语文现象都有修辞,一切言语活动都有修辞。在言语作品中凡能对应题旨情境的都是修辞。吴士文先生在《修辞的敏感》(《语文月刊》1985年第5期)一文中说:“如果我们都能有修辞无所不在的敏感,那么,所有的普普通通的说法就都可以找到规律,说明用法了。”比如,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它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艺术家依照自然景物作画,叫作写生。所谓风景如画,是说美好的风景。拿画来形容风景的好,因为有些画是经过艺术家美化了的风景的写照。
这里有辞格吗?看不出来。但它对应了题旨、情境,你不能说它不是修辞。它有方法可说,但它和词典的解词方法又不一样:它不是就孤立的词解释孤立的词,而是对应题旨、情境的解释,并且有意借着解释安排下文,以便更好地把鉴湖如画的风景写出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其实这里也有修辞方式,不过它不是积极修辞方式,而是消极修辞方式。吴士文先生称之为“正面释言”。再如,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有这么一句:“这个国王被一群反动派包围,一味地骄奢淫逸,轻举妄动,多树敌人,容易受人欺骗,也容易受人挑衅,结果一败再败。”这句话也没有辞格,但你得承认它也有修辞,这其中也包含有修辞规律。吴士文先生认为:“这个规律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复句,当第一分句用的是被动句时,后面与之相应的主语都可以省略。这样的写法不仅显得简洁,而且也显得衔接紧凑,语意连贯。”
“辞规”理论的修辞观认为凡有言语的地方就有修辞。这种广泛的修辞观曾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与责难。你不是说一切言语活动都有修辞吗?那么,请问:“请你坐在椅子上。”这句话有什么修辞?当然,如果认为修辞就是辞格,辞格就是修辞,这里的确不好说有什么修辞。然而如果认为修辞是在一定语言环境中呈现出来的达意传情的语言手段,如果承认修辞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那么应该说这句话有修辞。比如说,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之下,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为什么用了这些词,没有用别的词,等等,这里应该有修辞,只是不同的人解说起来可能有所不同而已,而这又是以往没有研究,现在则需要大力研究的问题。
既然一切语文现象,一切言语活动都有修辞,那么就不能只着眼于积极修辞,也应该着眼于消极修辞,否则在言语事实面前可能会束手无策。但是以往的消极修辞研究缺乏修辞的全面观点,角度与方向产生了偏差,成果微薄,以之分析语言事实也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辞规的提出与建立,正是用系统方法,即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方法来研究修辞现象,研究消极修辞方式,“从另一个方面完善修辞方式的系统”,“使所有的语言片断,在修辞方法上都能做出全面而科学的分析”
三、“辞规”理论的哲学基础
人类思想史上早已存在对立统一的观点。例如,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强调一切事物都是成对偶的,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春秋繁露·基义》)这里的“合”,就是对偶的意思。董仲舒甚至还认为对偶是相互渗透的:“于浊之中,必知其清;于清之中,必知其浊。于曲之中,必见其直;于直之中,必见其曲。”(《春秋繁露·保位权》)清浊曲直,互为包涵。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二而一,一而二。分合、合分”(《东西均·张驰》)的对立统一观点。他认为世界万物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他说:“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交也者,合二而一也。”(《东西均·三征》)“尽天地古今皆二”,事物都是对立的;“两间无不交”而“合二而一。”,对立面又是统一的。这也就是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中觉察到对立面的统一。他说:“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在我的身上,生和死,醒和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则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立统一学说。在他的著作中,从不同角度多次谈到过对立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自然辩证法》“运动的基本形式”一节中他更为完整地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他说:“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