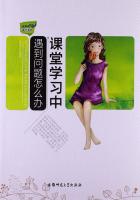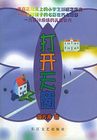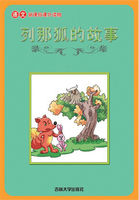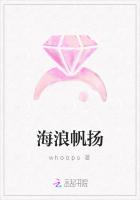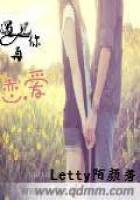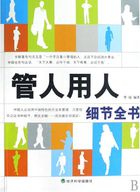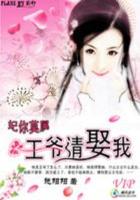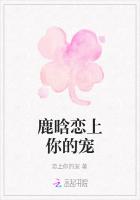尊重还表现为对对方能力、“隐私”的尊重。作为社会的个体,每个人都希望并认为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同时也希望别人承认自己的能力。如果在人际交流中,被对方认为是无用的人,其自尊心必然会受到损害,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进而影响到人际交流的顺利进行。另外,每个人都有内心不宜公开的东西,在人际交流中,一个人对自己的情况,是公开还是保密,公开多少,保密到什么程度,完全是他自己的权利,别人不应过多地干涉,否则就是侵犯了别人的权利,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尊重在人际交流中最直接的表现是礼貌。在人际交流中讲究礼貌,能使对方产生愉快的心理感受和自尊心得到满足的充实感。“礼貌不仅反映了自身高雅的风度和较高的思想境界,而且更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也直接影响着交际双方良好关系的建立。”陈松岑先生在《礼貌语言》中举过一个称呼使用与否的比较用例:
假如有一位青年在北京城里某个小胡同中速了路,他对一位坐在家门口的老头说:“老大爷,请问到西单怎么走啊?”这老头一定会觉得这位青年把两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长幼辈分的关系,而且对自己很尊重,所以就非常乐意为他指点道路。反过来,如果这位青年说:“嗨!到西单怎么走?”这位老人一定会感到这个小伙子太不尊重自己,仿佛是一个大人不经意地在对孩子讲话,所以他可能很生气,装作没听见,不予理睬。
从人际修辞角度来说,称呼老人“老大爷”,突出强调了自己与对方的年龄、辈分差异,很有礼貌,体现了对对方的尊重,从而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达到了目的。而一声“嗨”,虽也能引起对方的注意,但它缺乏教养与礼貌,表现出了对对方的轻视,以之进入人际交流,因违背了尊重的原则而导致交际失败。
礼貌交际主要表现在用词造句上的对社会言行准则、道德规范的适切,也表现于语态的亲切自然、谦恭得体。很难设想,横眉立目、翘着二郎腿、歪脖瞪眼、冷笑着、指着人的鼻尖等身势情态,能够使人感受到说话者语言的礼貌。《荀子·非十二子》云:“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身势情态语作为一种伴随言语交际手段,是构成礼貌语言的一个有机方面,也可成为破坏礼貌语言,使之“有言而无礼”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所以人际修辞也应注意身势情态语的恰当运用。
尊重对方还表现在修辞主体在人际交流过程中能平等地对待对方。人际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活动,在这种双向的交流活动中,以何种态度对待对方,直接反映了人际修辞主体的品德修养。有些人在人际交流过程中,自恃比对方优越,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动辄就命令、训斥对方,不尊重对方的人格,这样的言语行为反映了这种人缺乏平等待人的品德。而有些人则相反,在人际交流中能够考虑对方的需求,尊重对方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尊重对方的人格,这反映了行为者平等待人的美德。其实由于身份、辈份、年龄、职业、财富等的不同,人们的社会地位难免会有高有低,但这种高低差异只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而不是人格尊卑的显现。在人际交流过程中,交际双方的人格是平等的,都具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因而,人际交流中,人际修辞主体不管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平等对待对方,尊重对方的思想、情感,尊重对方的权利,在和谐的氛围中平等交流。
4.情感原则
情感原则指人际交流应该富有亲切感、人情味,不要过于生硬。
人际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有目的的言语行为,而人是理智的动物,更是情感的精灵,因此在人际交流中诉诸情感,才能增进情感的互动。
情感原则要求我们用情感化的语言,去焕发接受对象心理的愉悦反应,但更重要的要求是人际交流应具有人情味。人情味包括的内容相当丰富,如爱、理解、关怀、体贴、帮助、同情、怜悯、安慰等等。人情味是形成人际修辞魅力的重要因素。
爱。爱是人情味中内涵最为丰富的成分,也是理解、关怀等等其他人情因素的滋生母体。人类有了爱,也才有了更好的希望,正如泰戈尔所说的:“爱就是充实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充满爱的人际交流应该是最富魅力的交际,因为爱是人类最美的情感,徜徉其中,我们能感受到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博大、温馨、甜蜜与醇厚,感受到人与自然、社会的融洽与和谐。有爱的人际交流,即使修辞主体的语言表达带有缺陷,人们也会感到其中的暖意,而没有爱的人际交流,不论修辞主体的言语多么动听,也不会有真正的心灵的交流。
理解。指人际交流过程中,修辞主体对交际对象思想、情感、行为等的深入了解和某种认同。人在社会,由于角色身份的不同,心理需求的不同,行为方式的不同,都会形成人际交流中认识对方、了解对方的障碍,造成不解与误解。而不解与误解的存在既影响信息交流,又容易造成人际隔膜。此时交际双方互相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人际交流过程中,修辞主体如果能充分了解对方的需要、情感和行为方式,清楚对方的处境,明了对方的心情,能够立足对方,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那么人际交流因理解的注入,也就有了成功的前提。理解虽然包含较多的理智成分,但仍是一种情感体现。它由爱滋生而来,是爱的又一种表现。因为修辞主体只有爱对方,才会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才能体会到对方的难处和苦衷,才会理解对方,所以也有人说:“理解就是爱。”
关心、体贴。关心、体贴别人是一种美德,也是人情味的一种表现。芸芸众生没有不需要别人关心、体贴的,关心、体贴既是心理的需要,更是情感的交流。卡耐基曾经说过:“如果你要别人喜欢你,或是培养真正的友情……就把这条原则记在心里:对别人表现出诚挚的关心。”人际交流中关心、体贴对方,反映了对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这样容易引起对方的好感,产生出人际修辞魅力,而且关心、体贴对方也才能引起对方对你的关心、体贴。有了修辞主体之间的相互关心、体贴,人际修辞的人情美也才更加浓烈。而有了浓烈的人情美,人际修辞也才会更加成功。人际交流中关心、体贴对方,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关心对方的冷暖、安危、健康、生活、工作、学习,等等。有时可能需要较多的话语,有时三言两语,甚至更少的言词即可表示出对对方的关心、体贴。人际修辞中关心、体贴人情美的创造主要不在于话语的多少、文采的有无,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挚的感情,要有对对方的爱。
5.谐和原则
谐和原则指人际交流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要协调统一。
人际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信息交流活动,它关涉到多种因素,是多种因素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
在进行特定的人际交流之前或者过程中,修辞主体应该分析、把握对方的各种特定因素,如年龄、性别、职业、身份、知识水平、兴趣爱好等,以及双方所处的交际环境,在此基础上,努力使自己的外在形象(仪表、举止等),交际的内容、方式、语言形式等切合对方的心理需求和交际环境,与对方的各种特定因素及交际环境构成统一的整体,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创造出一种和谐的美。这样的人际交流方能产生出极大的魅力,拨动交际双方的心弦。
人际交流要创造出和谐美,必须注意各种交际因素的统一,如注意外在形象与话语内容的统一,话语形式与话语内容的统一,外在形象、话语和交际环境的统一,交际主体之间的协调、统一,因为和谐就是多样的统一、不同因素的协调,正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学者所言“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和谐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这里以“交际主体之间的协调、统一”为例对谐和原则作一说明。
人际交流,其交际主体都是充满个性色彩的独特的“这一个”。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必须注意对方自身的各种因素,有意识地适切对方的各种因素,与对方相协调,相统一,从而创造出人际交流的和谐美。比如,面对一个小孩,要与之交际,修辞主体就应遵循对象律,使用浅显、形象的语言和他交谈,这样容易与对方的知识水平相适应,容易产生和谐的交流。相反,如果不遵循对象律,使用深奥、抽象的语言和他交谈,就破坏了与对方知识水平等的适应,也就破坏了交际的和谐。
一般说来,交际主体之间性格、志趣、思想、观点、立场、态度相同或相近最容易造成交际的和谐。俗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日常生活中趣味相投的人,他们的人际交流往往十分融洽,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相同或相近的趣味。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性格、志趣、思想、观点、立场、态度不同的交际主体之间就不可以有和谐的人际交流。假如性格、志趣、态度等等不同的交际主体在人际交流过程中能够理解对方、尊重对方、欣赏对方,多一份宽容大度,也可以产生和谐的交流,创造出人际交流的和谐美,而这关键就在于交际主体要有一种良好的品质与心态。
(本文曾在中国修辞学会2005年夏季学术研讨会(2005年6月16日一18日),厦门)上宣读)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修辞探微
在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一个转变期的开始。作为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默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它叙俗事,画俗境,因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名留于中国小说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彭城(今江苏徐州)张竹坡(名道深)以超人的艺术才华与高拔的艺术视角,完成了对《金瓶梅》的评点,为这部经典小说的传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评点丰富了我国文学理论宝库,并给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艺术经验。
张竹坡为《金瓶梅》撰写了十几万字的评点文字,其中包括一百则回前总评,大量的眉批、夹批,以及《杂录小引》、《竹坡闲话》、《冷热金针》、《<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论》、《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等专论。其中最有价值的要数108条“读法”和一百则回前总评,以及大量的眉批、夹批。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主要侧重于文学批评和小说美学,但也有不少内容是隶属于修辞学的,这就是修辞史家所说的“评点修辞”。本文拟对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中的修辞思想作一概括的论述,以期为张竹坡评点研究提供另外一种参照系。
一、接受修辞观
文学作品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获得价值,阅读是文本价值实现的中介。从接受修辞学的角度来说“表达主体(作家)一文本(作品)一接受主体(读者)”形成互动关系。小说评点作为中国古典叙事批评中的一种独特的形式,评点者通过评点引导读者正确地理解作品,把握作品的创作主旨、形象内涵等意义体系,填补、丰富作品的审美空白,影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遥感于作家内在的情感脉搏所唤起的自身的情感运动。
台湾学者单德兴先生指出,中国古代评点式批评大都不是以正常字体出现在全书及章回的始末,就是以小字体出现在正文中,或以眉批方式出现,这种评点本使读者能同时处理正文和评点,透过这种印刷上的特别安排,批评家便在读者阅读行为“之前”或“之中”影响读者,而不像一般批评是阅读行为之后。所以读评点本的读者在处理叙事文本的同时,也被批评家的评语所指引来决定文本的意义。因此他们的阅读过程结合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以及读者与评语的互动。评语则具体呈现了批评家(具有文学能力或有知识的读者)的见解和“后见之明”。也就是说,他们对文本的观念经历过程,同时发生于他们处理批评家“确定的”与“正在确定中”的评语过程之中。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也正是通过自己的评语来影响读者,指引读者“来决定文本的意义”,并影响其情感导向。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所包含的接受修辞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整体解读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既有宏观论述,高度概括,又有具体分析,擘肌入理,涉及创作主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艺术手法等各方面。其评点特色在于从大处着眼、总体立论,并以此为前提,再对小说细部寻绎审察。张竹坡这种整体解读的修辞接受思想贯穿于全书的评点,而且表现得非常明显。
《金瓶梅》以西门庆一家丑恶生活为主线,涉及清河县多家及远外多家,以西门一人为中心旁及家中妻妾仆婢及社会诸色人等,形成其“千曲万折”而又“血脉贯通”的结构特点。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共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因而张竹坡认为读《金瓶梅》要认识到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五十一回又是后半部的关键,要总体把握住小说的“大关键处”、“大照应处”、“大肩架处”,才能对全书的题旨、结构、情节、人物的关系及命运变迁明若指掌。
张竹坡评点修辞的整体接受思想还表现在对篇章修辞的论述上。他关于篇章修辞的论述很多,分散在评点《金瓶梅》的各个章节之中。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他指出:“《金瓶》有板定大章法。……”“《金瓶》一百回,到底俱是两对章法,合其目为二百件事。……总之,以目中二事为条干,逐回细玩即知。”“《金瓶》一回,两事作对固矣,却又有两回作遥对者。如金莲琵琶、瓶儿象棋作一对,偷壶、偷金作一对等,又不可枚举。”这些其实是在提示读者要注意分析章法。
张竹坡强调整体解读《金瓶梅》,他主张读《金瓶梅》“一百回是一回,必须放开眼光作一回读,乃知其起尽处”(《读法》38),“《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读法》52)。
2.逆向同构接受
文本建构与文本解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逆向的对应行为。作者建构文本之时,在“脱卸处”、“穿插处”、“用意处”、“结穴发脉、关锁照应处”等关键之地常常加以遮掩,以营造文本曲折多变的艺术魅力。读者在解构文本之时则需要逆向同构,沿波讨源,解开作者的掩映,变“幽”为“显”。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二回回评中明确地展现了自己的同构逆向修辞接受思想。他由《金瓶梅》作者“每于伏一线时,每恐为人看出,必用一笔遮盖之”而告戒读者“于此等处,须要看他学他”。然后由此上升到理论高度:“做文如盖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别出心裁的比喻很好地道出了文本解构与文本建构是逆向同构的关系,从而昭示了从作者意图、文本意义等方面同构逆向解读的修辞接受思想。
3.读者参与小说创作:修辞接受具有双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