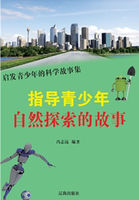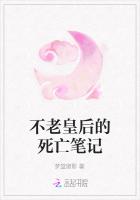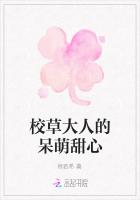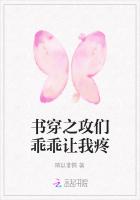西方文学接受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伊泽尔说过:“文学作品有艺术和审美两极:艺术一极是作者的文本,审美一极则通过读者的阅读而实现。”可以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接受修辞学认为“表达”与“接受”呈互动模式,“相对于修辞表达而言,修辞接受具有受动性和施动性两重属性,前者承受某种作用力,后者产生某种反作用力,正是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矛盾运动中,接受修辞具有了受制于表达、又驱动了表达的动力学价值。”应该说三百年前的张竹坡已经意识到了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虚构性的小说创作,接受与表达互动。这种看法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
看《金瓶》,将来当他的文章看。犹须被他瞒过;必把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方不被他瞒过。
将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是矣。然又不如将他当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我先将心与之曲折算出,夫而后谓之不能瞒我,方是不能瞒我也。
这三段文字其实涉及了小说阅读时要注意的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小说作品有虚构性,并非事实;第二,读者在阅读小说作品时,要将其当作自己的作品来读;第三,仅当自己的作品来读还不够,更进一步,将其“当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用“心”来读。联系这三层意思,可知张竹坡已经领会到了小说创作和阅读之间的内在联系,领会到了修辞接受具有受动性和施动性这两种属性。
4.对比接受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一直贯穿着整体解读和读者参与创作:修辞接受具有双重属性的思想。由此又派生出对比接受的观念。在评点中他特别强调前后章节的对比阅读,以准确领悟小说的表现艺术。比如在第四回回评中,他指出:“写二人勾情处,须将后文陈敬济几回勾挑处合看,方知此回文字之妙,方知后几回文字之妙,绝不雷同也。”在第五回回评中,他又指出:“上文勾情处,要与‘花园调婿’一回对读,见文不犯手。此文要与‘贪欲丧命’一回对读,见报总一般。”
除了强调前后章节对比阅读之外,张竹坡还强调与作者对比,引导接受者参与小说创作,感受作者的语言运用的功力。第二回回评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愿看官看金莲、武二的文字时,将身即做金莲,想至等武二来,如何用言语去勾引他,方得上道儿也。思之不得,用笔描之亦不得,然后看《金瓶梅》如何写金莲处,方知作者无一语不神妙难言。至看武大、武二文字,与王婆、西门庆文字,皆当作如是观。然后作者之心血乃出,然后乃不负作者的心血。
这里张竹坡希望读者用“心”去体察《金瓶梅》语言运用的神妙,置换角色去感受作者个性化的人物塑造,在与作者的对比中完成对文本的接受。
二、推崇简约与白描
语言表达经常受到经济原则的制约,汉语表达更是如此。汉民族历来崇尚简约,表现在言语风格上便为孜孜追求简约美。古人云“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槐《论文偶记》)、“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陈骙《文则》)、“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严羽《沧浪诗话》)、“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刘勰《文心雕龙》)、“意则期多,字唯求少”(李渔《笠翁一家言》),这些论述都显示了汉人对言语风格简约的美学追求。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也特别推崇简约,大量的夹批中包含了很多对《金瓶梅》叙述文字言简而意丰的肯定。如:
(1)看他叙出十弟兄,虽一篇小小文章,却参差错落,而与西门庆亲疏厚薄,以及后文各人的行事、终身,皆不烦言而毕现,真化工之笔也,惟古史迁可以似之。(第一回夹批)
(2)又省一笔。……细。又省一笔,行文便如云散水流匆匆,明简之甚。(第七十一回夹批)
例(1)事涉“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短短一段文章将九个结拜兄弟与西门庆的亲疏厚薄,以及后文每个人的“行事、终身”都很好地反映出来了。张竹坡赞赏其“不烦言而毕现”,认为是“化工之笔”。例(2)事涉西门庆与何干户进朝而返的几件事,事多而言少,几个简短的承接句式容纳了较多的内容,张竹坡称之“明简之甚”。再如,第一回应伯爵对西门庆叙述武松打虎的一段文字:
(伯爵)于是手舞足蹈说道:“这个人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难在柴大官人庄上,后来怎的害起病来,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寻他哥哥,过这景阳岗来,怎的遇了这虎,怎的怎的被他一顿拳脚打死了。一五一十说来,就象是亲见的一般,又象这只猛虎是他打的一般。
对此张竹坡夹批:“一段文字,武二出来,武大亦出来,而虚拟打虎、传闻打虎者,色色皆到,却只是八个‘怎的’,两个‘象是’便觉奇绝,妙绝。”在第一回回评中,张竹坡认为:“《水浒》上打虎,是写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扑;《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几个‘怎的’‘怎的’,一个‘就象是’,一个‘又象’,便使《水浒》中费如许力量方写出来者,他却一毫不费力便了也。是何等灵滑手腕!”这里张竹坡推崇的是《金瓶梅》叙述的简约,因为《金瓶梅》与《水浒》创作主旨有别,打虎详略繁简亦有别,用张竹坡自己的话来说:“《水浒》本意在武松,故写金莲是宾,写武松是主。《金瓶梅》本写金莲,故写金莲是主,写武松是宾。文章有宾主之法,故立言体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一节,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说出。”
张竹坡推崇简约,并不单单是指一味地简字省文,主要是指简而有当、言简意赅,可以说“文约而事丰”是他最理想的标准。这从三十三回回评中的一段文字可见其端倪:
一路写金莲强敬济吃酒索唱,总是从骨髓中描出,溶成一片,不能为之字分句解,知者当心领其用笔之妙。然而他偏又夹写瓶儿、春梅、潘姥姥、吴月娘、如意儿、官哥,总是史笔之简净灵活处。
张竹坡在评点中经常拿《金瓶梅》与司马迁或一般历史作品写法相比,推崇其简约的特色。晋代张辅在《班马优劣论》中认为马优班劣,其理由是:“迁之著作,辞约而事丰,彼三千年事,仅五十万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用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张辅以字数多寡论烦省、评优劣不免失之偏颇。但说司马迁的作品辞约而事丰是符合事实的。本来写历史在语言运用上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简约,因此张竹坡常常称赞《金瓶梅》的叙事“惟古史迁可以似之”、“总是史笔之简净灵活”等等。
《金瓶梅》主要写的是家庭之中、市井之间的事,它描写市井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包括奸夫****、贪官恶仆、帮闲娼妓、尼姑道士等等,整部小说浸透着“俗”的色彩,形成“一篇市井文字”。张竹坡评点特别重视其与市井文字美学风貌相适应的白描手法:
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64)
所谓“白描”,“从修辞的角度分析,就是用朴实的、平白的、极为精炼的语言,把人物的动作、神态甚至性格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往往是淡淡数笔,却能以少胜多,形神毕现”。《金瓶梅》中有大量精彩的白描,张竹坡对此反复评点、赞不绝口。如,第一回描写伯爵向谢希大说:“何如?我说哥要说哩!”张竹坡评点道:“妙。纯是白描,却是放重笔拿轻笔法,切须学之也。”六十七回应伯爵寒冬岁月添了个儿子想向西门庆借钱,张竹坡对这段文字的夹批是:“一路白描,曲尽借债人心事。”二十六回西门庆设计陷害来旺,宋蕙莲跪对西门庆说了一番话,张竹坡批日:“直讲人情,妙。白描中化工手也。”
有时,在张竹坡的评点文字中并未出现“白描”一词,而是用“如画”、“逼真”、“化工”、“写生”、“摹神”、“描神”、“画”、“追魂取影”、“毛发皆动”等词语。这些词语与“白描”实际含义相同,只不过它们是用来形容白描手法成功运用之后的修辞效果而已。例如,六十一回李瓶儿病重,西门庆一家病急乱投医,请了好几个医生,其中那个赵太医是个不懂医术的“捣鬼”,对此张竹坡批道:“若止讲病人,便令笔墨皆秽;止讲医人,却又笔墨枯涩。看他用一捣鬼杂于其间,便令病家真是忙乱,医人真是嘈杂,一时情景如画,非借此骂岐黄流也。”七十五回,春梅大骂申二姐,要她“趁早儿与我走,不要来了”,申二姐说:“我没的赖在你家!”张竹坡批日:“逼真,如闻其声口。”七十二回潘金莲不满如意儿和西门庆的关系同孟玉楼讲了一番“有权属”的话,张竹坡批道:“又结到此,总是点水归源。一腔心事如画,方是描神之笔。”
再如,七十五回写潘金莲与吴月娘大吵了一场后,吴月娘对大妗子说:“你看这回气的我,两只胳膊都软了,手冰冷的……”张竹坡在此批道:“看他此等笔法,纯是追魂取魄,最耐人学也。”第一回写武松和潘金莲初次见面,张竹坡有一段批语:“写妇人,写武松,毛发皆动。”更有甚者,第三十回写李瓶儿即将生子,西门庆家里上上下下忙成一团,各色人等均有自己真实而妙不可言的表演,张竹坡在此竟一连批下了五个“如画”、两个“白描”,由此亦可见张竹坡对白描手法的极度推崇。
张竹坡赞扬《金瓶梅》的白描手法具有“摹神肖影,追魂取魄”的高超艺术表现力,是“笔蓄锋芒而不露”,后被鲁迅赞之为“幽伏而含讥”。应该说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的过程中对白描这种由金圣叹从绘画而引入小说批评的语言艺术方法的评价和分析,推动了其发展,也给后世以较大影响。
三、探索小说语言运用的方法、技巧、规律
小说评点肇始于金圣叹。“他评点《水浒》体例完备,穷幽晰微,总结出了小说修辞的许多规律,开一代风气之先。”后来众多的小说评点在理论和方法上无不继承了金圣叹。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也是如此。金圣叹:“最很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书了。”(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金圣叹《水浒传(楔子总评》)这些话语表明了他对小说语言运用的方法、技巧和规律的重视,受金圣叹的影响,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也十分重视《金瓶梅》语言运用的方法、技巧与规律。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幼时在馆中读文,见窗友为先生夏楚云:‘我教你字字想来,不曾教你囫囵吞。’予时尚幼,旁听此言,即深自儆省。……今本不通,然思读书之法,断不可成片念过去。岂但读文,即如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去,便味如嚼蜡,止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夫不看其妙文,然则止要看其妙事乎?”(《读法》71)
张竹坡评点对小说语言运用的方法、技巧和规律的探索体现在很多方面,此处我们只就词语修辞、辞格及章法的点评略作说明。
1.词语修辞
《金瓶梅》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运用白描手法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白描的特征在于不用或少用夸张、渲染、排比等手法,甚至连形容词都不多用,只是用简洁、朴实、平易的语言把人物的动作、神态等生动如画地表现出来,从而达到一种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审美效果。而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经常会涉及动词的选择与锤炼。张竹坡评点中有不少对动词运用之精当的赞美和推崇。如三十一回有吴典恩向西门庆借钱的描写:
正打发出门去了,只见陈敬济拿着一百两银子出来,叫与吴主管,说:“吴二哥,你明日只还我本钱便了。”
张竹坡在此眉批:“一‘叫’一‘说’字,将西门骄盈之色活画出来。”九十四回写春梅使悍责骂海棠、雪娥等,作者用几个动词便简洁生动地将其性格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出来。张竹坡在此回回评中指出:“内只用几个‘一推’‘一泼’,写春梅悍妒性急如画。”再如,三十七回西门庆看上了王六儿,要冯婆子去说合,冯对王说:“……你若与他凹上了,愁没吃的,穿的,使的,用的?……”张竹坡在此旁批道:“凹字绝妙,六节所为象形也。”七十九回应伯爵闻知西门庆死了,便去吊孝,吴大舅告诉他吴月娘同时添了个娃儿,小说写道:“伯爵愕然……”张竹坡夹批日:“二字描尽。”在此回回评中他更是作了详尽的修辞分析:“写伯爵,止用‘愕然’二字,写尽小人之心,已写尽后文趋承张三官之意,真是一笔当千万笔用也。”
张竹坡词语评点修辞不仅涉及动词的运用,还涉及很多其他语法功能的词语的运用。如三十回写李瓶儿生子“良久,只听房里‘呱’的一声养下来了”。此处用一拟声词“呱”既描摹了婴儿的哭声,又形象地显现出生产的顺利。因此张竹坡夹批道:“文字垛花之妙如此。”再如:
(1)婆子便道:“啊呀!……”(第四回)
用叹词“啊呀”便将王婆说话时的情态、语气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张竹坡批道:“如闻其声。”
(2)因说道:“昊二哥你拿出那符儿来,与你大官人瞧。”(第三十一回)
吴典恩央求应伯爵为自己向西门庆借钱说话,应伯爵用话语作了一番铺垫之后,指向修辞目的:拿出借款字据让西门庆答应。这里应伯爵用一代词“你”修饰“大官人”以此拉近吴与西门庆的距离,“你”的运用巧妙之至,张竹坡旁批:“一‘你’字,妙也。”
(3)(金莲)带笑带骂道:“好个贼短命的油嘴……你又跟了我来做甚么,也不怕人看着。”(第五十二回)
“又”是表示一定关系的副词,用此就隐含了具有依存关系的条件的存在。此处一个“又”字包含了众多复杂的内容,张竹坡用旁批指出了这一点:“‘又’字妙,将上文无数涎脸眉眼一齐描出。”张竹坡对词语所包含的隐含关系特别注意揭示之,这和他极力推崇简约的修辞观是一致的。
称谓(称呼)反映出入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反映出称谓者与被称谓者之间的思想、情感与态度。《金瓶梅》中称谓词语的使用极具修辞色彩,张竹坡对此一一作了评点,分析其显著的修辞效果。如:
却说武松一日在街上闲行,只见背后一个人叫道:“兄弟,本县相公抬举你做了巡捕都头,怎不看顾我!”(第一回)
武大的一声“兄弟”饱含着浓烈的亲情,所以张竹坡夹批:“二字刺人心肺。”当武松随武大到家中,潘金莲见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欢喜之情集于无数声“叔叔”的称呼上。(在第一回回评中,张竹坡指出“篇内金莲凡十二声‘叔叔’,于十一声下,作者却自人一句,将上文十一声‘叔叔’一总,下又拖一句‘叔叔’,便见金莲心头眼底口中,一时便有无数‘叔叔’也。益悟文章生动处,不在用笔写到之处”)后来挑逗武松不成,潘金莲在怨恨、恼怒之中变换了几个情感色彩强烈的称谓。作者用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了人物复杂的思想情感。对潘金莲对武松称谓的几经变化,张竹坡批道:“忽下你字,换去叔叔二字,妙”,“忽将外人换去叔叔,妙”,“忽将那厮换外人,妙”。几个称谓的逐步转换,层次清晰地把潘金莲内心深处对武松由敬畏到误解,由误解到怨恨,由怨恨到恼怒的感情变化,真实而细致地刻画出来了,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潘金莲****狂浪的个性特征,所以张竹坡连声称“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