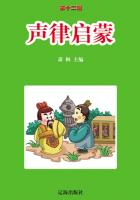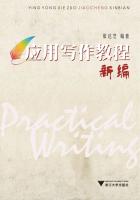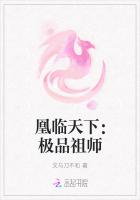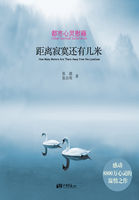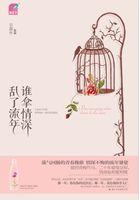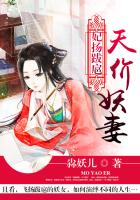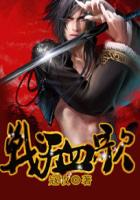称谓的变化还能反映出称谓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称谓者对被称谓者的价值评判。潘金莲对王婆称谓的几次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张竹坡在评点中也意识到此。潘金莲在未进西门庆家门之前称王婆为“王干娘”,等到成为西门庆的宠妾,她称王婆为“老王”。第七十六回王婆进西门庆家为人说情,临走,潘金莲对她说:“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张竹坡在此夹注日:“二人称谓间写尽人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反映出随着地位的变化潘金莲对王婆由尊敬到轻慢了。后来西门庆死了,吴月娘让王婆将潘金莲领出,“或聘嫁,或打发”,此时潘金莲又称王婆“王干娘”了。张竹坡以玩笑的口吻指出了称谓的变化:“又不是老王了。”张竹坡对称谓的批语屡屡可见,再如:
称谓奇极,强如割子由之头。(二十回夹批)
不称姐姐,妙。(七十六回夹批)
绝妙称呼。一家眷属,皆受度脱。(八十四回夹批)
2.修辞格
“修辞格是一种语言中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而有意识地偏离语言的和语用的常规并逐渐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修辞格的恰当运用能增添作品的生动形象性。《金瓶梅》运用了不少修辞格,为文本的艺术魅力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张竹坡在评点中对此作了较多的涉猎。如:
(1)比喻
这婆娘便道……他酒便吃两钟,敢恁七个头八个胆,背地里骂爹?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二十五回)
张竹坡夹批:“以纣王喻之。妙绝。”在其他地方,他对比喻的妙用也作了点评,如:“妙绝譬喻”(二十七回)、“妙喻”(八十五回)、“又是天生妙喻”(八十六回)。
(2)错综
《金瓶梅》错综手法的使用相当普遍,对此张竹坡在回评、冒批、旁批、夹批中作了很多点评。如:“内有十一‘他若’,四‘若是他’,错落尽致,不细注。”(第三回眉批)“一路将众人睡去,叙得错落之甚。”(三十九回眉批)
(3)双关
那老婆原来****出身,与贲四私通被拐出来,占为妻子。(七十八回)
张竹坡夹批:“私通二字,双关名意。”
(4)反复
第三回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时说的一番话运用了反复的手法:出现了九个“此事便休了”。张竹坡注意到了这种用法,在九个“此事便休了”后都加了夹批。比如在第三个后他批道“上文两个‘此事便休了’。此处又添一句,生动之极。三个‘便休’”。
(5)跳脱
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泼脚子货,别人一句儿还没说出来……你看他嘴头子就相淮洪一般。”(七十五回)
这段引文属现代所说的跳脱修辞格,张竹坡在评点中注意到了它的语形残缺、上下不接的特征。因为是争吵,潘金莲的语速比吴月娘快,这就造成吴月娘话语的不完整。张竹坡在此段文字的不连贯处加了几个夹批,既指出了这种言语现象的形式特征,又概括了这种方法使用时的修辞效果:
(1)句。与上句不连。(2)又与上句不连,一连三句,皆不成句。即下自云“没说出来”。(3)又与上句不连,自己没说出来,正是气急语。(4)月娘正云一句没说出来,金莲一面又说。月娘依旧没说出,所以又说“你看”,又说其嘴也,气急如画。
(6)镶嵌
郑爱香儿道:“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山虎儿、汗东山、斜纹布。”(三十二回)
“望江南、巴山虎儿、汗东山、斜纹布”取每个词语的第一个字,再运用谐音生义。张竹坡眉批:“‘望’作‘王’,‘巴’作‘八’,‘汗’同‘汗’,‘斜’作‘邪’,合成‘王八汗邪’四字,盖****行市语也。”
3.篇章修辞
篇章结构的巧妙安排体现了作者的独运匠心。因此张竹坡特别重视《金瓶梅》的篇章修辞。可以说对篇章修辞的探讨是他评点的最重要的方面。如,他认为二十九回是一部之“关键”,所以在此回回评的开头即指出:“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
诸如此类的论述有很多,这些充分说明了张竹坡对《金瓶梅》的篇章布置是十分重视的。张竹坡从多方面总结了《金瓶梅》的篇章修辞艺术,此处我们只简述穿插、伏笔与照应。
张竹坡对《金瓶梅》的穿插技巧大加赞赏:“未出金莲,先出瓶儿,既娶金莲,方出春梅;未娶金莲,却先娶玉楼;未娶瓶儿,又先出敬济。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夹写蕙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诸人,又极尽天工之巧矣。”(《读法》第五)他认为:“读《金瓶》,须看其入笋处。如玉皇庙讲笑话,插入打虎;请子虚,即插入后院紧邻……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盖其用笔不露痕迹处也。”(《读法》第十三)
《金瓶梅》善用穿插之法,其巧妙之处在于“不露痕迹”,张竹坡认为这要归结于“善用曲笔、逆笔,不肯另起头绪用直笔、顺笔也”(《读法》十三)。穿插得天衣无缝当然还要借助于过渡用语的成功运用,对此张竹坡在点评中作了不少评析。例如,第一回中插叙武大与潘金莲夫妇文字完结,用“不想这日,撞见自己嫡亲兄弟”作过渡承接上文,张竹坡夹批:“此一篇清晰文字,下文用‘不想这日’四字,便瞒过插入的这一篇文字去。妙妙!”他的这几句评语很好地道出了“不想这日”这个过渡用语的语篇衔接功能。
善用伏笔与照应是《金瓶梅》篇章组织上的一大特色,张竹坡对此特别重视,多有评论。在第六回、三十六回回评中他还对之作了较详细的阐释:
文有写他处,却照此处者,为顾盼照应伏线法。文有写此处,却写下文者,为脱卸影喻引入法。(六回回评)
盖此书每传一人,必伏线于千里之前,又流波于千里之后,如宋蕙莲既死,犹余山洞之鞋等是也。(三十六回回评)
在读法、回评、眉批、夹批中,张竹坡对《金瓶梅》的伏笔与照应作了大量的点评,为读者理解全书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如:
以上方将十兄弟身份用力一描,为热结作照应也。(十二回夹批)
写雪娥处却是衬蕙莲,又为向来旺学舌伏线。(二十三回眉批)
百忙出下回之笋。(二十七回夹批)
伏。……总照后文泄机。(六十六回夹批)
另外,张竹坡还经常用“金针奇绝”(八十二回夹批)、“藏针伏线”(二十二回夹批)、“千里结穴”(五十八回回评)、“照后作结的文字”(七十三回回评)、“云外神龙忽露一爪”(七十一回回评)等词语来描述《金瓶梅》中的伏笔与照应,由此亦可见张竹坡对《金瓶梅》这种篇章组织上的特色极为重视,且深有感受。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
略论《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的
修辞理论贡献
王希杰教授在中国语言学界以理性思辨、理论创新见长。他在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学理论、语义学理论、修辞学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树,成就斐然,而这其中尤以修辞学理论建树最为突出,被认为是新时期中修辞理论上成就最高的一位。1983年1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王希杰先生的第一部修辞学著作《汉语修辞学》就以理论创新而特别引人注目,袁晖先生认为:“这本书是我国80年代出现的最好的一部修辞学著作,代表了我国80年代的修辞学的水平。”(p.381)该书出版至今,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成为我国众多高校中文系教学和研究的必读参考书。200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修订本对原版作了大量的改动,吸收了王先生最近十来年的最新成果与成熟理论,构建了更加缜密独到的修辞学新体系,而且修订本在每章之后增加了大量饶有趣味且启人心智、极富研究性的“思考与练习”,这就使得本书又很适合作修辞学课程的教材。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就其修辞理论上的贡献略作论述,以之就教于王希杰教授及学界同仁。
1.辩证修辞观
王希杰先生对修辞、对修辞学的认识充满着辩证法。《汉语修辞学》对汉语修辞现象的研究与论述无论是宏观的审视,还是微观的探求都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芒。王先生认为“修辞活动是有效地运用语言的活动,其目的是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其途径是妥善处理好交际活动中的各种矛盾,保持矛盾和矛盾诸方面的相对的动态的平衡。语言材料、修辞方式本身,孤立地看,很难说什么好和坏的。适当的场合,运用适当就是好,运用在不能运用的地方就是不好”,“修辞是保守和创新统一的学问。一方面,修辞学推崇规范的纯正的语言表达,推荐典雅的优秀的风格;另一方面,修辞又鼓励创新和突破,鼓励打破规则教条的束缚。进一步认识语言,把握语言辩证法,这是学习和研究修辞学的关键”。(p.494—495)
《汉语修辞学》的辩证修辞观集中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整体观念;第二,联系观念。整体观念就是全局观念,即时时处处从全局把握问题。整体观念,要求全面、辩证地把握交际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如表达主体的特点、接受主体的特点、交际环境的特点、交际内容的特点、语言媒介的特点等等,只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忽视了其他的因素,是难以收到好的表达效果的。整体观念,要求表达主体从全局出发考虑到语言表达的具体的、局部的问题。对具体词句的选择,具体修辞方式的选择,应当服从交际的战略原则。整体观念还要求照顾上下文的协调,比如,同一词语在上下文中多次重复,会显得单调、呆板,就必须加以变化。联系观念就是依存与对立统一观念。修辞现象,修辞要素常常互依互存,常常对立而又统一,因此修辞研究必须从事物多方面联系之中来观察各种修辞现象,从而抽象出符合事实的修辞规律,并指出各种修辞规律的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修辞活动中的句子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上下文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句子必须和其他句子联系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语篇。如果忽视了句子之间的联系,就可能会妨碍表达效果,反之,如果注意句际关系可能为表达增色。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有云:“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汉语修辞学》分析道:“青山看我应如是,是荒谬的,青山没有眼睛。但是同‘我看青山多妩媚’相配搭,作动词‘料’的宾语,表现的是诗人的心理活动,不仅不荒谬,还是绝妙的诗句。”显然这是用依存观念来阐释修辞现象。像这样的阐释在《汉语修辞学》中时有所见。
通常人们推崇《汉语修辞学》原版的辩证法思想主要着眼于原版很多内容所表现的对立统一认识。应该承认对立统一认识,最为典型地表现了《汉语修辞学》的辩证修辞观。和原版相比,修订版的修辞的对立统一的观念更强,认识更为全面、深刻。比如在论述语言的侧重美等时说:“侧重,同均衡和变化及联系是对立统一的。均衡,必须有一个中心。没有中心,就没有均衡。变化必须有一个中心。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中心。变化必须立足于中心。联系是为中心服务的口离开了中心的联系,是杂乱无章,侧重是对中心的维护和强调。”(p.342)再如修订版第三章中增补的“语言的同义手段和言语的同义手段”,“显性同义手段和潜性同义手段”,第四章中增补的“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语流义和语流义变”,“情景义和情景义变”,“模糊义和模糊义变”,第六章增补的“插入语和反衔接”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作者自觉的对立统一的辩证修辞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版特别强调修辞学是转化之学,它认为:“修辞学其实是转化之学,利用一定的条件,把坏的转化为好的,化腐朽为神奇。同时,也要避免把神奇变作腐朽——在失去了必要和充分条件的时候。”(p.496)修辞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的转化的认识是王希杰先生辩证修辞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由此我们也可认为修辞学其实就是揭示这个“转化条件”的学科。
辩证地认识修辞现象与规律、辩证地认识修辞学,这是《汉语修辞学》在修辞理论上的第一个贡献。
2.修辞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