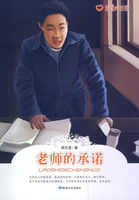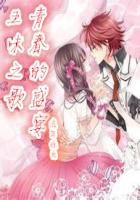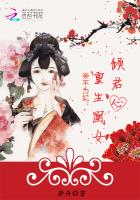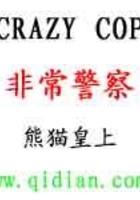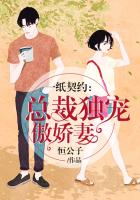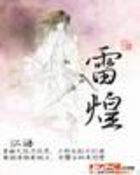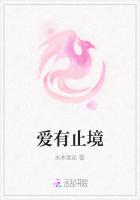一个打着三角小红旗的老倌子被挤得偏偏欲倒,但他没有放弃维护秩序的职责:喂!那个剃光头的!不准拿两份!(韩少功《火宅》)
此处以对方剃光头这个特征构造称呼语。
2.绰号代本体
用被称呼对象的外号代替被称呼对象而构造的称呼语。如:
“嘿!坦克!你可把人急坏了!”剑波上前用力握着刘勋苍的手。(曲波《林海雪原》)
3.工具代本体
借与被称呼对象有关的工具代替被称呼对象而构造的称呼语。如:
“三轮,过来!”(李民玉《都市》)
4.地点代本体
借与被称呼对象有关的地点代替被称呼对象而构造的称呼语。如:
正当小铁匠掩住炉火,准备歇息的时候,铁匠棚外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唤:
“嗳,张庄的!”(张一弓《张铁匠的罗曼史》)
5.行为代本体
以被称呼对象所从事的工作、活动,正在进行的动作行为来代替被称呼对象而构造的称呼语。如:
“担粪的!你把人臭死了!……”(路遥《人生》)
6.夫名代妻名
这种借代式称呼语其格式为:夫名十家的。如:
锁爷麻脸立即通红了,道:“锅三家的,你找到叔的名下,叔就是再戴一顶富农帽儿也得管你的事……”(张石山《村宴》)
漫长的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尊男卑女、女子为男子依附的观念,“夫名十家的”这种对女性的称呼正是这种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沉淀物。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称呼已逐渐被淘汰,只流行于某些较偏远、闭塞地区。
借代式称呼语使用起来较为方便,尤其是对不熟悉的人,比如根据对方的特征、标志、所从事的活动等,在有关词语之后加一个“的”字就可构造出一个个借代式称呼语来,如“卖樱桃的,你过来一下!”“穿红衣服的,你挡住我啦!”
借代式称呼语的使用方便是方便,但有时交际效果不佳。请看实例:
一位解放军战士上了公共汽车,他先在前门乘务员那里买了票,之后移到了车厢中部。不一会儿,他听得后面传来一声女高音:“喂,那戴黄帽子的,卖票啦!”战士回头一看,见后门乘务员位置上坐着一位花枝招展的摩登女郎,正不屑一顾地睨着自己。他的脸泛了一点红,略微沉了沉,突然出人意外地亮开了他雄浑的男低音,答道:“噢,这涂红嘴唇的,买过咧!”说着,亮出车票。满座哗然。(《演讲与口才》》1986.12)
这里女乘务员用了个借代式称呼语——“那戴黄帽子的”,但这种称呼语带有轻视、不尊重的情感色彩(参拙文《不受欢迎的“的”字结构式称呼语》,《演讲与口才》1988.11),刺伤了战士的自尊心。
借代式称呼语在日常交往中使用较为普遍,但其色彩有褒有贬。为了使自己的言语更礼貌、更得体,我们认为运用借代式称呼语需要注意以下四个准则:
1.情感准则
称呼语一般既有指称功能(指示听者,表示向谁说,传递理性信息),又有情感功能(显示说者对听者的褒贬态度,传递情感信息)。借代式称呼语也有这种双重表达功能。我们认为借代式称呼语有较强的描绘性或指别性,对不认识或不太熟悉的人采用之有其方便性,但是现代汉语中借代式称呼语多数带有轻视、不尊重对方的情感色彩,因此为了体现对他人自尊与情感的尊重,我们应该谨慎地有选择地使用借代式称呼语。比如“的”字结构式称呼语带有贬义(“当家的”、“掌柜的”除外),用人的生理缺陷为特征代人的称呼语(如“结巴,走吧!”“麻子,你有打火机吗?”)通常也有贬义,这些都应谨慎使用。
2.关系准则
借代式称呼语的使用有时需注意双方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有长幼之别,有熟悉与生疏的不同,等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也会影响到借代式称呼语的使用。如有的借代式称呼语用于熟人可以,用于生人则不行;有的借代式称呼语只能用于长对幼,用于幼对长则显得说话人没大没小,缺少教养。譬如同是特征代人,“胖子”用于熟人间,用于长对幼有时可以;用于生人,用于幼对长则显然糟糕,请比较:
①胖子,你在等谁?(用于熟人、关系较亲密者)
②胖子,到文峰新村怎么走?(用于向生人问路)
③胖子,你老头在家吗?(长对幼)
④胖子,青青姐在家吗?(幼对长)
①③这种特征代本体的称呼语“胖子”,通常对方能够接受,但②④这种特征代本体的称呼语“胖子”,对方肯定不能接受。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有一种关系准则的约束。
3.时境准则
有的借代称呼语在这种时境下能够使用,换一种时境可能就不恰当了。如“胖子”用于日常谈话,用于非正式场合,有时反而能体现双方关系的融洽与亲密,但是用于正式场合,就显得不严肃,近乎放肆了,对别人缺少了应有的尊重。
4.心理准则
即考虑到对方的心理,考虑对方能否接受。如,有的人忌讳绰号,即使在很熟悉的人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对这类人,你若用借代式称呼语大呼小叫的“大头,外面有人找!”、“大耳朵,下班啦!”等等,这就不识相了,肯定令对方产生不快,说不定还会恶化人际关系。而有的人则不以为然,你叫他绰号他会爽快应答。据说陈赓将军早年就喜欢别人称他为“小调皮”。再如,叫“三轮,过来!”、“出租,过来!”对方可以接受,但叫“粪车!过来!”恐怕对方难以接受了。因此借代式称呼语的使用需要遵循心理准则。
(原载《阅读与写作》1997年第11期)
谚语与汉民族传统文化心态简说
谚语是使用语言的群体在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言简意赅的习用的固定短句。谚语虽然通俗易解,但是含义深刻。在它通俗精炼的语言表层之后往往蕴涵有丰富深广的内容:有对自然奥秘的探究,也有对社会人生的剖析;有的总结了生产经验,有的表明了人生哲理,有的概括了风土人情,有的展示了社会取向……。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心态等等在一个民族的谚语中都有所积淀。正如教育学家马申斯所说:“人类一代一代地把深刻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各种历史事件、信仰、观念,已经成为陈迹的悲哀与欢乐,都收入语言的宝库中……”因此,从汉民族流传甚广、数量众多的谚语中,我们必然可以窥视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来。当然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从谚语中将其全部显现,更不可能在一篇短文里面面俱到。本文只打算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勾勒出谚语所显现的几种汉民族传统文化心态。
1.谚语和“群体规范”心态
比较文化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西传统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如,在西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进取精神,从而形成一种注重个体意识而忽视群体意识的文化心理。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道”与“人道”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主张天称父,地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宇宙天地,为人之父母;世间万物皆吾同伴。人只要忘却私我,保存本心,便可达至“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构成中,始终注重的是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体现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民族观念,不强调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从而形成一种注重群体意识而忽视个体意识的文化心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更是侧重于群体意识对社会个体意识的规范与抑制,强调个性服从并统一于共性。这一点在谚语中有充分的反映。谚语日:
出头的椽子先烂。
风吹连檐瓦,雨打出头椽。
枪打出头鸟。
出林笋子先折断。
出水船儿先烂底。
树大招风风损地,人为名高名丧身。
树大招风,人大遭歧。
出头的船先漏水。
出头的桶子先遭难。
出头鸽子先遭难。
人怕出名猪怕壮。
这许许多多谚语从多方面设喻,将传统文化的“群体规范”心态深刻而鲜明地展示了出来。作为喻体的“椽”、“鸟”、“树”、“船”等等自然之物实是人格的象征,积淀于这些谚语其中的实是:个体以群体为规范,作为个体不能超出于群体,不能有冒尖、开拓等进取之心,否则就会有“枪打”、“刀砍”的危险!既然如此,很多人只好“真人不露相”(谚语)了。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这种“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的文化势力比较适合于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心理格局,因而得到社会的默认,并且绵延千年,构成一种传统的文化心态——“群体规范”,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倾向。
由于存在着“群体规范”、“枪打出头鸟”,整个社会抑制个体独立意识,只能认同群体,因而传统文化中又有了与之相辅相成的求稳妥、“执两用中”、不偏不依的中庸观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比人气死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谚语就是折射了这种不求进取,不求冒尖,甘居中间的中庸心态。
2.谚语与宗教鬼神观上的追功逐利心态
汉民族这个中国的主体聚居于湿润地区。九曲黄河与万里长江滋润哺育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为文化的创造者们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主干是农业经济。这种农业经济派生出一系列的传统文化特征。比如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就是农业社会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章太炎曾刻画过传统文化“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他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也正是这种“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心态,使得中国自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虽有种种土生的或外来的宗教(如道教、佛教、基督教等)流传,但基本上没有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世俗的人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
传统文化整体上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伦理观念是一种世俗的人世的道德学说,这种道德学说一直左右着它,因而传统文化的宗教色彩较为淡泊,与欧洲、印度等的文化风格迥然有别。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产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除了拜祖宗之外(这其实不是宗教,只是纪念去世的先辈的一种方式),他们只有非常微弱的一点宗教感情。这种淡漠的宗教感情可以解释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宽容态度。”
传统文化这种重实际而轻玄想,对人世伦理和政治的思考压倒对其他一切问题的关注的性格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在宗教鬼神观上,传统文化也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功利色彩极其浓厚。这种宗教鬼神观上的功利心态,在谚语中留有深深的文化积淀。一句著名的经常为人们所使用的谚语“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就深深地透视出这种特征。对神佛可利用时(有求于时)供奉之,不需要时则弃置一边,就是这句谚语的深层内核。我们再看一些谚语:
用菩萨挂菩萨,不用菩萨卷菩萨。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什么菩萨烧什么香。
敬神如神在,不敬如泥块(泥土)。
敬神如神在,不敬妨何碍。
不见真佛不烧香。不见圣像不烧香。
施佛饭僧,不如奉亲;塑像栖庙,不如济贫。
从这些谚语中我们不难窥视出传统文化宗教鬼神观上的浓厚的实用色彩,见什么菩萨烧什么香,有用于我则敬,无用则置之不理。甚至敬不敬神亦无所谓,因为神亦不过“泥巴一块”,简直表现了对神的大不敬。不仅谚语,在其他熟语中往往也表现了对神的种种不敬的态度:戏谑、亵渎、作弄、糟踏,甚至鞭挞。如歇后语:
泥菩萨洗脸——越洗越难看
弥勒佛偷供献——口善心恶
庙里的泥胎——装的什么神
杭州灵隐寺飞来峰岩壁上的那位“大肚弥勒佛”,对之人们曾留下不少联语,其中一联云:“笑到几时方合口,坐来无日不开怀。”前句就颇含戏谑的意味。
有些谚语语表反映的是鬼神贪图功利,如“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至十万贯,通神矣”。认为鬼神一旦得到供奉便表现殷勤,为我所用,任我驱使。这语里或日深层结构实际反映了信奉鬼神者本身追逐功利的文化心态。现代社会心理学在论述归属过程的主观性时强调,被描述的客体特征方面取决于知觉主体的本身特点,对象的表征是与本人自我认识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崇信鬼神或妄佛学仙,“无非欲得其神通,受人供养,使势成于我,利归于我,虽学仙佛,却是学势利也”。总之,谚语反映了传统文化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宗教鬼神观。它功利色彩浓厚,有别于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超世俗性的宗教观。
3.谚语与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
19世纪,泰纳、勃兰兑斯等文化历史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种因素。这种观点虽然未能真正追溯文化特质的终极原因,但包含着一些可供借鉴的成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与这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繁衍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梁启超认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海洋民族的文化心理较为外向,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动态的和开放的状态,而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所处的地理环境是群山巨岭从北、西、南三面如同屏障和墙垣一样环绕着它,群山巨岭使它处于半封闭状态。这种半封闭的地理环境是一种较为完备的“隔绝机制”,在这种较为完备的“隔绝机制”下,非常有利于从事农业,经营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但却不利于发展开放的商业型经济。因而传统文化心理是内向的,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半封闭或封闭的状态。在这种半封闭或封闭状态下养育了一种执著的大陆民族意识,即特别眷恋国土乡邦。在谚语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汉民族强烈的乡土观念的情怀。比如: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狗窝)。
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在家刨土块。
千条路,万条路,不如回家卖豆腐。
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他乡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这些谚语无疑深深地积淀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封建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型自然经济,人们很自然地产生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谚语)的思想,视背井离乡为畏途,除非社会的动荡,否则宁愿斯守穷庐,也不愿离开乡土去找寻那“金窝”、“银窝”。故土难离啊,“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这种强烈的乡土观念或日安土重迁的文化心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在改革开放的动荡变革的今天,这种文化心态正在逐渐改变,由静向动发展。
(原载《营口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