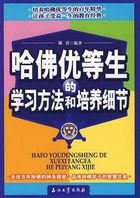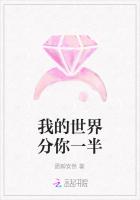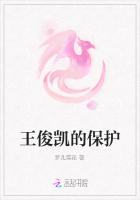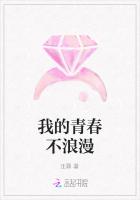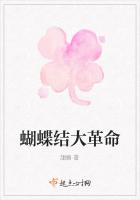现代汉语中还有
“动词+将+趋向动词”格式
“动词+将+趋向动词”格式是近代汉语中较为普遍的格式。它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如何呢?不少学者认为此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完全消失,如邢福义(2002)认为“‘动词+将+趋向动词’,是古白话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到现代,这一格式全部消失……”但我们觉得这一结论不完全正确。
“动词+将+趋向动词”这一语法现象,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据曹广顺(1990)统计,这个时期,这种格式在《古小说钩沉》中出现十例,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二例,《还冤记》中二例。如:
(1)有人呼将去,至一城府。(《古小说钩沉·冥祥记》
(2)若生女者,辄持将去……(《颜氏家训·治家》
(3)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还冤记》)
不过,处于萌芽时期的“动词十将+趋向动词”这一格式中的“趋向动词”都为单音节。而宋元往后,其中的“趋向动词”又增加了双音节的(晚唐五代时期的《祖堂集》中已有一例:“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整个格式的使用也逐渐普遍起来,
如:
(4)师日:“把将果子来。”(普济《五灯会元》卷四)
(5)尽选将来,以充后宫,有何不可?(马致远《汉宫秋》)
(6)都蛙锁豁儿自那山上望见统格黎名字的河边有一丛百姓,顺水行将来。(《元朝秘史》卷一)
(7)只见门外一大黑影,一个人走将进来。(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
(8)那叫花子便和身滚在地下,诈死赖活的闹将起来。(张南庄《何典》卷五)
(9)宋教仁道:“我等只有数人,无拳无勇,倘他们捣将进来,如何对待?”(蔡东藩《民国演义》第八回)
在明清白话小说中,这种句法现象很常见,可谓达到了运用的顶峰。我们统计了《初刻拍案惊奇》、《西游记》和《豆棚闲话》,发现这种句式在《初刻拍案惊奇》中有244例,在《西游记》中有388例,在《豆棚闲话》中有45例。
萌芽时期的“动词+将+趋向动词”这种格式中的“将”还有实在意义,是动词,发展到唐代动词性开始消失,转化为助词(曹广顺1990)。“将”的助词性语法功能的获得使自己成了表示动态或动向的补语标志,而且有时还表现出在表意上可有可无的特质。如:
(10)(周舍云)这等,我步行赶将他去。(小二云)我也赶他去。(关汉卿《救风尘》)
(11)老王……只等三日之后,我轻轻的把着手儿,送将你那满堂娇儿来家,你意下如何?……(王林云)李逵哥哥去了,我也收拾过铺面,专等三日过后,送满堂娇儿来家。(康进之《李逵负荆》)
例(10)中“赶将他去”与“赶他去”二者是同义的,这说明“将”在表意上的可有可无。例(11)也是如此,“送将满堂娇儿来家”用“将”,而“送满堂娇儿来家”不用“将”,但二者同义。
另外,远在南宋时代就已出现了后来逐渐取代“动词+将+趋向动词”格式的“动词+了+趋向动词”格式。大致明初开始这两个格式逐渐混用,最后是后者占据主导地位(陈刚1987、曹广顺1990)。陈刚(1987)认为“还没有发现元代作品里使用‘动了趋’式的可靠证据”。我们在关汉卿《救风尘》中倒是发现了一个“动将趋”式与“动了趋”式并用的例子,但我们也难以绝对肯定关汉卿剧作一点也没有经过后代演员们的改动。这个例子是:
(12)(云)引章妹子,你跟将他去。(外旦怕科,云)姐姐,跟了他去就是死。
应该承认,“将”字在有些场合的可有可无,以及“了”字的兴起、文体的转换(现代白话取代了古代白话),“动词+将+趋向动词”这一近代汉语中使用较为普遍的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大大萎缩了。但我们认为只是萎缩,而不是完全消失。理由有二:
第一,某些方言中至今仍保留有这种格式。
陈刚(1987)认为“动将趋”式现在主要残存于北方方言,在华北、西南、江淮(主要在安徽)、晋语四个区都有发现。陈剐(1988)认为杭州话里有“动将趋”式。
黄伯荣(1996)认为:“从山西晋语所辖的五个方言片看,云中、五台、并州、吕梁、上党都有类似的结构形式。……可以说,‘动+将+来/去’结构是山西晋语语法方面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特点。”
就安徽方言来说皖中江淮官话(如笔者的家乡话无为话)以及皖北中原官话(如沿淮等市县话)中至今仍有这种格式。当然,和近代汉语比较起来,安徽方言这种格式的使用已经大大萎缩了,现在只有少部分单音节动词(如“哭、笑、闹、唱、跳”等)与双音趋向动词“起来”组合构成“动词+将+趋向动词”的句法形式。如:
哭将起来吵将起来打将起来笑将起来下将起来
第二,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动词+将+趋向动词”这种格式的使用频率虽然不高,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陈望道(1981)曾举过鲁迅与郑加真作品中的例子:
(1)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鲁迅《阿长与山海经》)
(2)他站住了……使上全身的劲儿,朝冻土刨将下去。(郑加真《江畔朝阳》)
陈刚(1987)举过茅盾、李健吾作品中的例子:
(3)闪电似的冲将过过来。(茅盾《子夜》)
(4)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李健吾《雨中登泰山》)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在讲“介词的特别用法”时用了一句“动词+将+趋向动词”的表述话语:
(5)就上列的例句,依次看将下来:起初,介宾而不提前;其次……
笔者近来在《人民文学》(2000年第2、3、4、5、7期)和《羊城晚报》(2002年5月10日)上搜集到十余例这种格式的用例:
(6)我从床上跳将起来,顾不上披上衣服,只穿着一个肥大的裤衩,冲到门外。(夏季风《该死的鲸鱼》,《人民文学》2000年7期)
(7)我们跳将起来,跑入浅海,合力把快艇拖上沙滩……(同上)
(8)两人都买了饭菜,一前一后走出食堂,就站在太阳地里吃将起来。(刘富道《民主测评》,《人民文学》2000年3期)
(9)老人看见的是一只王八,很大的一只王八,足足有三斤。而且它还探头伸足,跃跃欲试,企图钻将出来。(凌可新《人气》,《人民文学》2000年5期)
(10)他取了一只脸盆,舀上半盆清水,一倒把王八倒进水里,看它舒筋动骨地游将起来……(同上)
(11)出了村,来来往往给祖坟送灯的人很多,去早的已把鞭炮噼噼啪啪放将起来……(同上)
(12)这样一来,他的满腔怒火腾腾地烧将起来,不可抑制……(陈源斌《你听我说》,《人民文学》2000年4期)
(13)这话刚刚说完,荣小姐她,张开她小巧玲珑的嘴巴,抑制不住地笑将起来。(同上)
(14)它以泰山崩落之势压将下来
我听到一阵轻微的
骨折的声音
([台湾]洛夫《秋来》,《人民文学》2000年4期)
(15)关淑云大喊,房间里的40来人都跪了下来,有的人还虔诚地双手合十拜将起来。(《母亲当众活活掐死九岁女儿》,《羊城晚报》2002年5月13日)
(16)话说我住的那一带——就是广州艺术博物院的附近,最近新开张一间扯面馆——这叫法对老广州来说挺新鲜,但是“扯”字比“拉”字来得传神,那面条的确是从手指缝里扯将出来的。(肖楠《食肆里的买椟还珠》,《羊城晚报》2002年5月29日)
(17)“来啦!”我惊叫一声,一条锄头柄般大小的蛇已蹿将出来了。(汪锡亮《童年趣事》,《羊城晚报》2002年6月13日)
(18)女儿说,她上车后抱着杂志昏昏欲睡,一听到底下三个中年男子“三缺一”的呼唤声,就按捺不住冲动跳将下来加盟。(聂勇军《女儿放单飞》,《羊城晚报》2002年8月21日)
(19)紧接着,杀猪人顺手操刀,对准猪颈部捅将进去,一声嚎叫,鲜血便从伤口流进了接血的铁桶。(谢良福《猪肉里的科技味》,《羊城晚报》2002年11月2日)
(20)虽然只两字之差,但在那样特定的场合,那么严肃认真一本正经地读将出来,实在妙趣横生,越想越忍俊不禁。(晋军《超级幽默》,《羊城晚报》2002年11月25日)
(21)你可以想象,那是一卷天大的红地毯自北向南一路铺将开来。(李中国《解读枫景》,《羊城晚报》2002年12月11日)
(22)然而,席间一老师突然假戏真做哭将起来……(毛尖《残酷的青春》,《羊城晚报》2002年12月13日)
再如,属于皖北中原官话区的阜阳报纸上的用例:
(1)凭借这一“学问”,尽管“五毒”在身,张二江在官场仍然发将起来。(邵道生《贪官有没有“保护伞”》,《阜阳广播电视报》2002年8月16ff)
(2)你不是杀鸡要猴看吗?我也学你那样杀将起来看,情绪上来,还要操刀杀向主人呢!给你来个杀你给鸡看!(米录《“杀鸡儆猴”三疑》,《阜阳广播电视报》2002年9月3日)
(3)不过油的烧饼就简单了……夹上刚出锅的羊杂碎,或者卤牛肉、成鸭蛋、豆瓣酱、“阿香婆”之类,便可吃将起来。(雪涅《马糊烧饼人人爱》,《阜阳广播电视报》2002年10月22日)
又如,沪籍学者曹炜所著《现代汉语词义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
(1)但是,当我们一旦从中跳将出来,将这些代表性成果置于整个现代汉语研究所取得的全部重大成果的大范围中来考察,我们难免会为此感到赧颜……
(2)若再将主要研究普通词汇学的张永言(四川大学)、王德春(上海外国语学院)以及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葛本仪(山东大学)、王勤(湘潭大学)、武占坤(河北大学)等也拉将进来,情形也依然没有改变。
湖南作家古华的名作《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也有动将结构的用例:
(1)三份通报念将下来,马上产生了奇效,一时会场上鸦雀无声……
(2)小巷侧门吱呀一声开了,那黑影闪将出来……
陆扬译,乔纳森卡勒著《论解构·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早在1980年代,德里达的幸运之星据信在它的本土就开始有了悄悄陨落的趋势,但是这颗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非常夺目地升将起来,一时间几乎就使众星的光辉莫不黯然失色。
就以上两点来看,我们认为不能否认“动词+将+趋向动词”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事实。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着“动词+将+趋向动词”这一句法形式,同时认为这种句法形式的存在是汉语表达丰富、细致、生动的表现之一。陈望道(1978)对这种形式持肯定态度,他在论述复合谓语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这些随带成分中间,还可以插入别的成分,变化多端,形式丰富,造成了汉语表达的细致、生动:
(把)船摇出去、摇出船去、摇船出去、摇船出港去、摇出港去、摇将出去
很显然,陈望道先生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动词+将+趋向动词”的句法形式,而且也承认这种句法形式有自身的表达功能。
比较“动词+将+趋向动词”与“动词+了+趋向动词”,我们会发现二者并不完全等同。我们认为前者侧重于表现动作行为的出现,后者侧重于表现动作行为的完成。“动词+将+趋向动词”中的“将”有舒缓节律的作用——黎锦熙(1924)认为“使硬拙的单音动词得着一个字音上的调节”,同时还可以突出强调动作行为的持续。
总之,我们认为“动词+将+趋向动词”这种句法形式仍然存在于现代汉语之中,它的表达功能与“动词+了+趋向动词”以及“动词+趋向动词+了”并不完全相同,有其自身的价值,因而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从而为汉语交际发挥自己的作用。
(原载钟玖英主编《语言学新思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参考文献:
[1]邢福义:《“起去”的普方古检视》,《方言》2002第2期。
[2]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中国语文》1990第2期。
[3]陈刚:《试论“动一了一趋”式和“动一将一趋”式》,《中国语文》1987第4期。
[4]陈刚:《杭州话里有“动一将一趋”式》,《中国语文》1988第3期。
[5]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1996年。
[6]陈望道:《陈望道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7]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
[8]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92年。
动将结构与皖北方言
动将结构指“动词+将+趋向动词”这种格式。它是近代汉语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句法形式。然而发展到现代汉语,这种格式却不常见了。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此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完全消失,如邢福义(2002)认为“‘动词+将+趋向动词’,是古白话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到现代,这一格式全部消失……”我们觉得这一结论不完全正确。因为这一格式只不见于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在一些方言中却还有残存。我们的结论是“动词+将+趋向动词”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只是萎缩,并未完全消失。本文以皖北方言为个案为这个结论提供一种论据。
一
“动词+将+趋向动词”这一语法现象,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据曹广顺(1990)统计,这个时期,这种格式在《古小说钩沉》中出现十例,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二例,《还冤记》中二例。如:
(1)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古小说钩沉·幽明录》)
(2)若生女者,辄持将去……(《颜氏家训·治家》)
(3)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还冤记》)
在《变文》中这种格式有所增加,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功德未知何似许,不教贪处唱将来。”《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利刀截割将来吃,养者凡夫恶业身。”不过,处于萌芽时期的“动词+将+趋向动词”这一格式中的“趋向动词”都为单音节,而宋元往后,其中的“趋向动词”又增加了双音节的(晚唐五代时期的《祖堂集》中已有一例:“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整个格式的使用也逐渐普遍起来,如:
(4)文远便去路旁立曰:“把将公验来。”(普济《五灯会元》卷四)
(5)你实说将出来,我饶你的性命。(纪君祥《赵氏孤儿》)
(6)都蛙锁豁儿自那山上望见统格黎名字的河边有一丛百姓,顺水行将来。(《元朝秘史》卷一)
(7)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一)
(8)那叫花子便和身滚在地下,诈死赖活的闹将起来。(张南庄《何典》卷五)
(9)急得摄政王冷汗直流,几欲跪将下去,求他出力。(蔡东藩《民国演义》第三回)
在明清白话小说中,这种句法现象很常见,可谓达到了运用的顶峰。萌芽时期的“动词+将+趋向动词”这种格式中的“将”还有实在意义,是动词,发展到唐代动词性开始消失,转化为助词(曹广顺1990)。“将”的助词性语法功能的获得使自己成了表示动态或动向的补语标志,而且有时还表现出在表意上可有可无的特质。
另外,远在南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后来逐渐取代“动词+将+趋向动词”格式的“动词+了+趋向动词”格式。大致明初开始这两个格式逐渐混用,最后是后者占据主导地位(陈刚1987、曹广顺1990)。陈刚(1987)认为“还没有发现元代作品里使用动了趋,式的可靠证据”。我们在关汉卿《救风尘》中倒是发现了一个“动将趋”式与“动了趋”式并用的例子,但我们也难以绝对肯定关汉卿剧作一点也没有经过后代演员们的改动。这个例子是:
(10)(云)引章妹子,你跟将他去。(外旦怕科,云)
姐姐,跟了他去就是死。
应该承认,“将”字在有些场合的可有可无,以及“了”字的兴起、文体的转换(现代白话取代了古代白话),“动词+将+趋向动词”这一近代汉语中使用较为普遍的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大大萎缩了。但我们认为只是萎缩,而不是完全消失。
二
陈刚(1987)认为:“动将趋”式现在主要残存于北方方言,在华北、西南、江淮(主要在安徽)、晋语四个区都有发现。陈刚(1988)认为杭州话里有“动将趋”式。
黄伯荣(1996)认为:“从山西晋语所辖的五个方言片看,云中、五台、并州、吕梁、上党都有类似的结构形式。……可以说,‘动+将+来/去’结构是山西晋语语法方面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