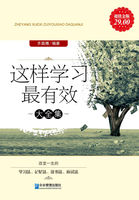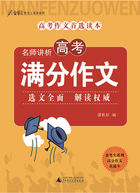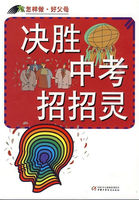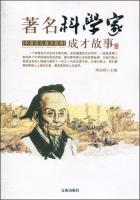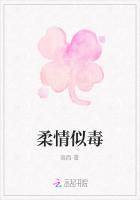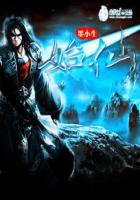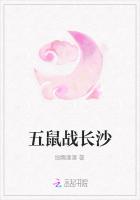让我们来分析(2)。(2)的前一分句是最大限度的有利条件,后一分句即正句是结果。最低限度的不利条件与结果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没有取得极其伟大的成绩,那么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说自明的。在“我们的工作没有取得极其伟大的成绩”的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在“我们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的条件下,“我们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而事实上,我们的工作要么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要么没有取得极其伟大的成绩,总之,都“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这个结论通过“即使A,也B”这种让转关系句式强调了出来。
总之,“即使A,也B”的逻辑基础是简单构成式二难推理。
三、如果A,那么B
“如果A,那么B”这种形式的假设复句,根据A所断定的情况是否确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确定性假设复句,一种是确定性假设复句。如:
(1)如果某一地区正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人口也较多,那么,这一地区的方言就有可能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册)
(2)如果说某一作家,由于思想和艺术方面的个性原因,常常把视觉的焦距对准一类人或几类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艺术风格的话,那么高晓声幽默的艺术风格首先表现为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幽默性格的人物形象。(沈国芳、高虹《高晓声小说的幽默风格初探》)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1)前边的分句(A)所断定的事物情况是假定的,因此它是非确定性假设复句;(2)前边的分句(A)所断定的事物情况实际上是存在的,是确定的,因此它是确定性假设复句。确定性假设复句,一般采用“如果说A,那么B”形式(当然A前也有没“说”的)。
非确定性假设复句表达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这几乎没有什么异议(说几乎没有什么异议,意味着有些异议,实际上有人认为非确定性假设复句有时表达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本文不讨论它。本文只讨论确定性假设复句的逻辑基础。
确定性假设复句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确定性假设复句表达联言判断。如陈宗明先生的《现代汉语逻辑初探》说:“有的命题虽然含有蕴含的语言标志,但实际不是蕴含的命题,而是合取的命题。”接着这段话此书举了一个确定性假设复句。
我们认为将这种形式的“如果A,那么B”看作合取命题,也就是看作表达联言判断,是不妥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看法抹杀了A和B之间的条件制约关系。
有人认为确定性假设复句“如果A,那么B”表达充分条件假言判断。这种看法抓住了A和B之间的条件制约关系,比上面的看法前进了一步。不过这种看法还是舍弃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照我们看来,确定性假设复句“如果A,那么B”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凝缩形式,它表达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式。这种确定性假设复句是把已然的事实A,故意当作假设提出,从而利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推出后件B,这样就突出强调了B。
上面我们说过确定性假设复句所表示的事物情况是确定的,这一点它不同于非确定性假设复句,必须注意。这种“如果A,那么B”,A的真实性是明显的,比如(2),文艺理论知识告诉我们,确实是有些作家“由于思想和艺术方面的个性原因,常常把视觉的焦距对准一类人或某几类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艺术风格”。再如:
(3)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587页)
历史知识告诉我们:秦以前的一个时代中国确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
确定性假设复句“如果A,那么B”前边分句A的真实性有的在前文已经断定过,比如:
(4)如果说词义的形成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单,那么词义的组合就是从一般回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
此例引自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书在说这句话之前已经论述过“词义的形成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单”(┣A),因此这里就很自然地推出后边分句B的真实性,语言表达上也就很自然地突出了后面的分句B。
总之,确定性假设复句“如果A,那么B”是断定了A的真实性的,其真实性是明显的或前文已断定过的,否则不能用这种句式。由于前边分句A有断定因素,所以它表达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
如果p,那么q;
p,
所以q。
像(4)就表达了这样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如果词义的形成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单,那么,词义的组合就是从一般回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
词义的形成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单;
所以,词义的组合是从一般回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
确定性假设复句同一般假设复句即非确定性假设复句的不同就在于它前边的分句A所表达的事物情况是已然的。使用确定性“如果A,那么B”这种句式的人,对这种已然的事物情况主观上是加以断定的。把这种句式看作表达充分条件假言判断,正是舍弃了这一断定因素,这么一来它同非确定性假设复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把它看作假言推理的凝缩式,一方面抓住了A和B条件制约关系,另一方面也抓住了A是已然的,含断定因素这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确定性假设复句“如果A,那么B”的逻辑基础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式)。
(原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试论现代汉语名词重叠
一、几种代表性的看法
1.有关现代汉语的语法著作,在讨论名词的语法特征时,一般都持“名词一般不能重叠”的观点。比如:
杨亦鸣、张成福认为:
名词的语法特征:(一)可以受数量短语修饰;(二)一般不受副词修饰;(三)指人的名词后面加“们”表示复数;(四)名词一般不能重叠,少数带有量词性质的名词重叠后表示“每一个”,如,“家家”、“人人”、“天天”、“队队”等。
黄伯荣、廖序东认为:
名词一般不能重叠。少数名词如“人、家、年、天、队、县”等带有量词的性质,前面可以直接加数词,可以按量词重叠式重叠。
这两家看法基本相同,都认为名词一般不能重叠,只有少数带有量词性质的才可以重叠,表示“每一”的语法意义。
同是持“名词一般不能重叠”观点的学者对名词重叠的例外情形也有不同认识。比如,洪心衡认为:
至于名词重叠,在现代汉语里已极少见。如“爸爸、妈妈、姐姐、弟弟”都算一个词。“人人、家家、年年、月月”可算名词重叠,但也可看作量词重叠。只有两个相类的名词各自重叠而连用起来,才算是名词重叠。如:
(1)傍晚,西藏高原上的山山水水都笼罩在杏黄色的晚霞里。
(2)春节前后,吕梁山下的村村寨寨,一派欢乐气氛。
(3)只要我们一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立刻把我们围起来。
(4)咱们中国的工农群众世世代代受苦。
上四例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等,都是“许多山、许多水、许多村、许多寨”的表示。
洪心衡先生认为名词重叠的例外是两个相类名词重叠的连用,只有两个相类名词各自重叠而且连用,才是名词重叠的例外,这种名词重叠表示“许多”的意思。
2.对“名词一般不能重叠”的观点,也有少数学者持有异议。比较典型的是张静和徐吉润等先生。
张静认为:
在汉语里多数名词的确不能重叠,如“房屋”、“政府”、“问题”等,都不能说成“房屋房屋”、“政府政府”、“问题问题”,但有一些名词还是可以重叠的。例如:
人人事事村村山山水水年年杠杠儿
家家户户盆盆碗碗坑坑洼洼神神鬼鬼
类似这样的例证可以举出百把十个,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是个别现象或特殊现象,最好还是不要把“不能重叠”看作名词同别的词类相互对立的特点。
徐吉润等认为:
绝大多数语法书上说,“名词一般不能重叠”,事实怎样呢?请看下边的“例外”之例:
声声、村村、天天、年年、岁岁、刀刀、桌桌、处处、本本、蛋蛋、兜兜儿、棍棍儿、孙孙儿、盆盆罐罐、头头脑脑、边边沿沿、山山水水、汤汤水水、针针线线、花花草草、祖祖辈辈
还可以举出好多名词重迭的例子。其中有一部分是迭音词,如“棍棍儿、孙孙儿”等,还有一些是有条件的,如“山山水水”是对举性的。但重叠的数量如此庞大,是无法打入“例外”的。这就要调整原来的说法,把“名词一般不能重叠”改为“名词多数不能重叠。”
比较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张静先生和徐吉润等先生虽不赞成“名词一般不能重叠”的观点,但他们之间也有差异。
二、现代汉语名词重叠情况的考察
上面我们列举了几家有代表性的看法,由此亦可见对于现代汉语名词重叠问题还没有一个令人较为满意的答案。那么,现代汉语名词重叠情形到底如何?本文拟对此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
1.讨论现代汉语名词重叠首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区别词的对举重叠不是名词重叠。区别词又称非谓形容词,它的谓词性最弱,相当大的一部分明显是从名词转化来的,从意义上说比较接近名词,但是它的语法特征是只能作定语,显然是不同于名词的另一个词类。区别词中的极少数可以重叠对举,如“男”、“女”等,但这不是名词重叠。上举洪心衡先生论述,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作名词重叠不妥。
第二,现代汉语方言异常复杂,在不同的方言里词类重叠情形不同。比如重庆话名词重叠就比较多,如“巾巾索索、肠肠肚肚、豆豆儿果果、亲亲戚戚……”。我们讨论名词重叠问题是就普通话来说的,不能拿方言中特殊的名词重叠现象来论证问题。
第三,幼儿语言和歌谣语言另当别论。幼儿语言与成人语言有许多差异,许多在成人语言中不能重叠的名词,在幼儿语言中则可重叠,如“饭饭、袜袜、狗狗、糖糖……”这种名词重叠可以说是童趣的反映,表现出亲切喜爱的情感色彩。歌谣属于韵文,与一般文体语言运用自有差异,一般不能重叠的名词,在歌谣中有时也能够成立。如,
主人要我搓索索,
索索搓到丈二长,
拿去西方拴太阳。(川北民歌)
树梢树枝树根根,
亲山亲水有亲人。(贺敬之《回延安》)
歌谣中的名词重叠主要在于协调音节、节奏。
2.现代汉语语料所见“名词重叠”的几种情况
(1)第一类:AA式
第一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舅舅、姑姑、姥姥、婆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娃娃、星星
这类重叠式,单音A是基式,双音AA是重叠式,如“爸”是“爸爸”的基式,“爸爸”是“爸”的重叠式。这组绝大多数是亲属称谓的重叠式名词,基式与重叠式没有词汇意义的差异,也没有语法意义的差异。这组一般都视其为合成词,不看作“名词重叠”。
第二组:本本、洞洞、调调、杠杠
这类重叠式数量极少,单音是基式,双音是重叠式,如“洞”是“洞洞”的基式,“洞洞”是“洞”的重叠式。重叠式与基式相比,可表“小”意。
第三组:年年、月月、夜夜、村村、家家、人人、户户……
这类重叠,基式也是单音,重叠式也是双音。这组基式——单音名词,带有量词的特点,如可直接受数词修饰(一年、三户等),受数词修饰后,后边还可以加上名词(一年时间、三户人家等)。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准量词。这类重叠式带有“每一”的语法意义。
(2)第二类:ABB式
山沟沟、布兜兜、面糊糊、线团团
这类名词重叠,基式是双音节AB,重叠式是三音节ABB。如“山沟”是“山沟沟”的基式,“山沟沟”是“山沟”的重叠式。有些名词形式上也是ABB式,但因为没有AB基式,所以不是名词重叠,只是尾部重叠的单个名词。如,“山丹丹、洋娃娃、蚕宝宝”等,没有基式“山丹、洋娃、蚕宝”,所以,这些就不是名词重叠形式。
ABB式名词重叠不多见,而且这种重叠主要在于表情。如:
哪个学校?我说九中。他释然:就是那个山沟沟里的老二中?我纠正不是山沟沟,是小河边。(吕洪亮《五月六月》)
(3)第三类:AAB式
毛毛虫、拉拉面
这类重叠式极少,其基式是AB,重叠式是AAB。如“毛虫”是“毛毛虫”的基式,“毛毛虫”是“毛虫”的重叠式。这类重叠其作用主要在于增加形象感。有少数名词也是AAB的形式,但因其无AB式基式,所以不是名词重叠。如“毛毛雨”,没有“毛雨”这个基式存在,所以它不是名词重叠式。再如“芨芨草”、“悄悄话”也不是名词重叠式。
(4)第四类:AABB式
第一组:山山水水、祖祖辈辈、汤汤水水、花花草草、坑坑洼洼……
第二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
第三组:世世代代、方方面面
从数量上看,所谓“名词重叠”第四类远远多于前三种类型,而且第一类第三组即朱德熙所说的准量词常常也对举使用,形成AABB式,如“家家户户、村村寨寨、日日夜夜、年年岁岁”。下面我们重点讨论名词重叠AABB式的有关问题。
3.AABB式名词重叠的特点
(1)两个单音名词重叠对举
AABB式名词重叠,绝大多数属于两个单音名词重叠对举。对举的名词从其语义关系来说有三种表现:
第一,同义关系。如“坑坑洼洼”,“坑”与“洼”为同义关系。再如:
头头脑脑、汤汤水水、年年岁岁、家家户户、村村寨寨
第二,反义关系。如“上上下下”,“上”与“下”为反义关系。再如:
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日日夜夜、恩恩怨怨
第三,类义关系。如。“花花草草”,“花”与“草”为类义关系。再如:
风风雨雨、神神鬼鬼、口口声声
两个名词重叠对举是很多名词重叠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有许多名词单独重叠是不能成立的,如“风”重叠为“风风”不成话,“雨”重叠为“雨雨”亦不成话,但“风风雨雨”对举则成话。“神”重叠为“神神”,“鬼”重叠为“鬼鬼”也不成话,但将其重叠对举为“神神鬼鬼”则成话。为什么对举可使名词重叠成立?这是平行结构的粘合作用使然。
只有极少数AABB式不是两个单音名词重叠对举,而是双音节重叠。如“该观察到的方方面面全都观察到了,所作的观察就算是充分的了”。(邢福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充分”》)这里的“方方面面”,显然是双音名词“方面”的重叠形式。
名词重叠的特点主要是同义、反义、类义词的重叠对举。哪些词和哪些词对举,除了有熟语性的较固定外,其他的有一定的随意性。如:
沟沟坎坎——坡坡坎坎、沟沟洼洼——坑坑洼洼
(1)踏遍了世上的沟沟坎坎。(电视系列片《虾球传》主题歌)
(2)所有的沟沟洼洼坡坡坎坎,都被棉堆雪团似的花树压着、盖着。(吴季康《有那样一排白杨》)
(3)积雪并不匀称,坑坑洼洼的地方铺上了一层,裸露在外的草茎则迎着微风籁籁地表白着起来的自由。(阎欣宇《天节台》)
再如,有“坛坛罐罐”,也有“瓶瓶罐罐”、“盆盆罐罐”等。
(2)一部分具有熟语性
如:婆婆妈妈、风风雨雨、山山水水、坛坛罐罐
具有熟语性的重叠形式,表意具有整体性。前后两部分组合起来表示浑然一体的意思,整个重叠格式一般也不是字面意义的相加,往往都有比喻义。
一部分具有经常性。如“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等。
名词重叠AABB式有的只有本义,如“年年岁岁”、“日日夜夜”。有的只有比喻义,如“风风火火”、“婆婆妈妈”。有的既有本义,又有比喻义,如:
(1)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