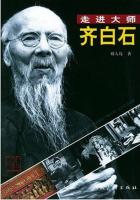李贤见合欢眼光一黯,自知失言,但他本就是个不善揣摩女子心思的人,故此也不知道合欢所为何事,只满饮了自己杯中的酒,以掩饰此刻的尴尬。
两人静了片刻,李贤一指合欢面前的金齑玉鲙道:“现下已过了吃鲈鱼的时节,但小王听闻才人爱吃,所以特地寻了一些,才人尝尝可还新鲜么?”
合欢宴饮的时候曾留心过,李贤案上的切鲙他是一筷子都没有动过,知道他想必是不爱吃这些鲜鱼。但如今他却特意替自己寻了不当季的鲈鱼,合欢心头一热,温然笑道:“殿下费心了。”说罢搛了一筷鲙丝入口,果然是鲜甜细嫩,用来佐酒是再好不过的了。
合欢这一餐,吃得有些醺醺然,也不知道是杯中的剑南烧春,还是李贤的眼波,几乎让她溺死在这丽正殿里。
待合欢出了丽正殿的时候,她的一双脚已是绵软无力了,她走的每一步,都好似踏在云朵之上,踩不到实处,幸好有丽正殿派的宫人扶住她才不至于摔倒。
合欢的心从没有跳得这么欢快过,她想放声高歌,却觉得喉咙很干很紧,发不出声来。她现在只想快点走回宜秋宫去,把自己没在温热的浴汤中,好让自己的心神安定一点。
婉儿在宜秋宫中是等了又等,终于把合欢盼了回来。她忙上前扶着合欢,焦急问道:“姐姐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合欢支在婉儿身上,犹带醉意道:“一会儿再说吧,我现在只想沐浴一下。”
婉儿瞧她醉得双颊酡红,暗自纳罕,但仍稳了心神向那丽正殿的宫人道:“多谢你这么晚了还送唐才人回来。”
一边的丹霞把早就备下的赏钱给了那宫人,那宫人便千恩万谢地去了。
婉儿见她走了,这才把合欢往殿中搀去,一边走一边道:“姐姐喝多了,是不能沐浴的。”
合欢却嘟着嘴道:“只一小会儿是没事的,”神情倔强如孩童。
婉儿拗不过她,只得替她准备。
雾气氤氲之中微带一丝玫瑰的暗香,干花虽不及鲜花柔嫩娇媚,泡开了浮在水面上却也幽美难言,合欢用手拨弄着,只觉温热滋润,十分舒服,神色也舒展欢欣起来。可这一切在婉儿严眼里,却好似合欢被陷在一个无形的牢笼里,不得挣脱。
这两日天气暖了些,雪已渐渐地融了,残雪堆在墙根底下,让微潮的泥土露了出来。瓦缝间略有几丝苍白的雪痕,余下的雪水则点点滴滴地从滴水瓦上坠落,敲在门前的石阶上。
然而这几日,前朝后宫却大事小情不断。天皇宣布改元,上元三年在年末变作了仪凤元年,张良媛虽然解禁,但是却再无恩宠,她倒也不以为意,甚至常常称病不出。然而对于婉儿与合欢,最为沉重的便是凌霜的逝世。
凌霜没有得到晋封,所以丧仪仍是五品的规格,加之凌霜到底身份尴尬,所以更是一切从简。以至于在婉儿看来,和朴昭训的丧仪倒也差不了多少。
日子一晃就到了年末,婉儿因前几日操持凌霜的丧仪而神思倦懒,看见晚膳也没有胃口,便只倒了杯茶来润舌,可入口才觉出那茶早已冷了,不仅苦涩,还凉了喉舌,婉儿也懒得发火,只轻叹一声,放下了茶杯。
忽听殿外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婉儿以为是合欢回来了,却见许燕锦掀了门帘进来道:“三司派人来送今年的节礼了,才人要不要亲自去看看?”
婉儿虽然意外,但仍摇了摇头道:“不必了,你们照单收下就是了,等唐才人回来,你再告诉她一声罢。”
燕锦去了不一时,复又进来道:“这个秦掌严手底下的女史非说有东西要面呈,才人要不然见一见?”
婉儿想起明月就是姓秦,有些好奇,道:“那就让她进来吧。”
片刻后来人入殿,婉儿看时,哪里是什么不入流的女史,分明就是明月本人。婉儿摒退众人后,惊诧道:“你怎么来了?”
明月微微一笑,“微臣全靠两位才人帮衬才有今日,所以额外准备了一点东西孝敬给宜秋宫。”说罢取出了两个小的素面鎏金银盒。
婉儿倒不意外,接过道:“是你自己帮衬了自己罢了,”她打开其中一个银盒,却见四个口脂盒放在其中,只听明月道:“这是微臣亲手制的四色口脂,不单单有寻常的朱红和檀色,还有桃红和橘红,这东西虽算不上名贵,倒也有些奇巧,更是微臣的一点心意,两位才人用着玩罢。”
婉儿见此物新鲜,心中高兴,道:“这东西倒是不错,只是你又何必专门配了鎏金银盒来盛它,让自己破费呢?”
明月道:“是从前朴昭训身边的金银盒子,我留下了两个。但用它盛东西又怕两位才人觉得晦气,所以用那盒子把温奉仪分内的盒子换了出来用,微臣并没有破费什么。”
婉儿见她心思活络,想到丹霞只一味的一味的老实胆小,又想到许燕锦的城府之深,让人摸不清底细,只觉若是明月能到自己的身边当差就好了。但婉儿自然不能碍了明月的官路,因此只能想想罢了。
明月走后,婉儿又陷入一个人的沉寂之中。纵然合欢提前对她说过,然而凌霜的死对她仍是打击极大。其实细细算来,她们三个一起在抔霞馆的日子才是她这短短十三年岁月里最高兴的日子,她从未想过,曾经朝夕相处的姐妹,竟然会熬不过她们入宫后的第一个冬天。再加上如今是年根岁底,人人都有事情忙,尤其是合欢,更是早出晚归,不见人影,似乎整个东宫里就只剩下婉儿一个闲人。再者说,如今官良娣的死因已然查明且报了上去,东宫又出了这样大的事,按理说婉儿她们的任务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是七皇子那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倒是天后提了一次让自己去蓬莱殿伺候,但是因为温奉仪的有孕却又再没了音讯。究竟此方事了,自己该何去何从,也让婉儿头疼不已。
婉儿正想着,一个宫人进来道:“唐才人回来了。”
婉儿忙出去迎她,却见合欢披了一件银狐裘回来,那银狐本就是珍贵无匹的皮料,不是婉儿这个品级该用的,再加上这狐裘油光水滑,在夜风中翻出银浪,并非品相不好的次等货,合欢是万万无处得来的。更要命的却是这银狐裘似乎是男子的样式,几乎拖到了地上,婉儿头皮一麻,心道不好,问道:“姐姐这狐裘是哪里来的?”
合欢本打算悄无声息地进去,见婉儿出来且问她这狐裘的来历,一时有些慌张,只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婉儿见合欢这样,又瞧她面有春色,心中明白了三五分,也不当着宫人的面为难她,岔开话题问道:“姐姐用过晚膳没有?”
合欢摇摇头道:“还没有呢。”原来今日光天殿商议分派各处的节礼,确实是事务繁忙,太子妃身子虽好了大半,但精神却依旧不佳,所以也没有留她用膳。哪知合欢一出了光天殿,就碰到了李贤,李贤非说夜里北风刺骨,要把自己的银狐裘给她披上,合欢推托不过,只得收下,然而心里却是甘甜如蜜。
婉儿吩咐宫人道:“你们把晚膳热一热,就端上来吧。”说罢又向合欢道:“我晚上也没怎么吃,一会儿陪姐姐用一点,也省得姐姐一个人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