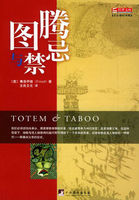用近乎玩笑的方式来决定如此严肃的大事,天下禅林虽有旧例可循,但毕竟太罕见了。大雄宝殿里顿时哑然。
也许这个玩笑的诱惑力太大了,它平等地给每个和尚一个当住持的机会,于是在片刻沉默之后便爆出了空前的活跃。
平时在空无、空相面前极尽趋奉之能事、不敢露出些许僭越意态的那班和尚,最先挤到香案前,看一眼不动声色的慧悟大师,就纷纷动手各抓一个纸阄。
明照站在人群后,当时他很替空无和空相不平,曾经偷偷地观察他们的神态。
那一瞬间,空无、空相脸上闪现过震动和愤慨。随着那一瞬的一闪即逝,他们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不是心如止水的淡漠,而是宽容为怀的蔑视。他们不约而同地互望一眼,相视而笑,将往日的忌恨变成了现在的一致。他们没有对慧悟大师不寻常的做法提出异议,反而抬出禅宗的道理为它圆场,哪怕圆得并不圆。
东院长老空无说:“祖师禅理至明:‘一切众生本心本身本来是佛’,大师圣裁合祖师之意。”
西院长老空相的理说得更顺些:“‘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岁数、职司、资历本不是缘法,于僧众中直接遴选住持,才是禅林正道。”
说罢,两人合十闭目,静坐于蒲团之上,矜持地任由旁人抢先抓阄。
香案上,香烟袅袅,烛焰摇摇。
抢先抓阄的那班僧人个个都怕机会被别人抢走,个个抓到纸阄都急不可待地拆开先看一眼,个个都在看了一眼之后神色惘然地将纸阄交给慧悟。大师每接过一张,看一眼,便宣一声:“阿弥陀佛!”顺手将它们伸向烛火。这些白纸顷刻便化作黑烟。抢先诸僧都是无功而返。
一声声的宣佛,一声声轻轻的叹息,没有对空无、空相起什么作用。他们依旧静坐,双目紧闭,两身如塞,眼角眉梢宛似木雕石刻,俨然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十四岁的明照偷觑他们一眼便满心叹服:看吧,凭人家的定力,新住持也该在他们当中挑!
空无、空相坐着不动,剩下的那些地位低的和尚、资历浅的沙弥又畏缩着不敢上前,空搁在香案上的纸阄使慧悟大师有些不耐,喊道:“空无,空相,难道你们也无此缘分么?”
空无、空相洒脱地同时起身,同时走到香案前,同时向对方谦让着:“师兄请!”“还是师弟先请!”
到底空无出身行伍来得爽快,说声“有僭”,便抓个纸阄递给慧悟大师,既不看又不等人家宣布结果,径直回身坐到蒲团上。
一声“阿弥陀佛”,一片烛上浮火,宣告了空无并不强于他人的命运。空相接着抓阄的时候,刚才的矜持已消磨了许多。然而他的结局跟空无并没有两样。
慧悟大师看一眼声色不动的空无,再看一眼面如死灰再也洒脱不起来的空相,长叹一声,向缩手缩脚站在边上不敢上前的和尚们挥了挥手:“唉——你们也来试试吧!”
这些和尚平日只管挑水、打柴、烧火、送饭、洒扫庭院,清理殿堂、侍候师父等一些杂差,能混到击鼓撞钟的差事就算大出头了。做住持对他们来说是个遥远的梦,谁都不曾想过,现在仍是不敢去做。刚才他们不上前,是依照从来没有资格上前的老习惯;现在有了上前的资格,他们也不指望“走****运”,一下子就抓到手一个住持的身份。
明照甚至想:千万别叫我抓到了,抓到了也退回去!当住持顶不好玩了!
这群和尚,推推搡搡嘻嘻哈哈地拥到香案前,乱哄哄地抓,抓到手就拆。这个说声“没有”,那个叫声“白纸”。喊完叫完,也不管慧悟大师允许不允许,白纸一伸,在蜡烛上边燎着,眼看着火起,眼看它成灰,随手一丢,权当是一场有趣的游戏。
明照既没有当住持的野心,也没有做游戏的兴致,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他没有上前。等大家嘻嘻哈哈抢罢闹罢,他反倒落得尴尬:纸阄只剩两个,有无必居其一。在众人注视之下,他实在不愿去抓这一下,但在慧悟大师的逼视之下他不敢不上前。
这个年仅十四岁的小沙弥到底还是个孩子,低着头走向香案,闭上眼睛抓了一个,递给慧悟之后转身便跑,走到大殿门口,一脚跨在门槛外,一脚留在门框里地站着听结果。他想,只要大师念出那个“有”字,我就开跑!很多人想得而无法得到的这个机会,在他一点也不觉得有多珍贵!
一声“阿弥陀佛”,一掠而过的火光,让明照收回了跨在门槛外面的那只脚——好了好了,不该我当住持了!
大雄宝殿里又变得出奇的安静。
风摇烛焰,声声可闻。
香案上只剩一个纸阄,孤零零地在玉菊前边,却放射出神奇的光彩:它属于尚未出现的抓阄人,玉菊也属于此人,此人就是大龙宫寺的继任住持!
最后一个抓阄人是谁?
是佛法的指点,还是命定的缘分?是胆怯使他一直不曾动手,还是早有成算作出的退让?
所有的和尚都屏声静气,等待那个稳坐钓鱼台的幸运者。心如止水的老僧,惯于嬉戏的职事和尚,暗含妒嫉的各殿首座,少不更事的小沙弥,这些身份经历各不相同的佛国弟子,似乎非常一致地表现了难耐此刻的心境,那神态异状纷呈:引颈四顾的,翘首凝望的,抓耳挠腮的,他们眼里都透着一股好奇。
慧悟大师好像忍不住满心的焦躁,举起那仅存的纸阄,目光威严地扫视众僧,气恼地问道:
“这是哪个没拈的?”
一个胆怯的声音从大师身后传出:“是我。”
“出来!”大师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嗯……”
如来佛两边是文殊、普贤的金身。就在文殊金身的阴影下,一个瘦细的身影畏缩地踱向亮处。在大家面前亮相的,竟是明月!
“啊!”
“是他?”
“……”
僧人们不能不吃惊,不能不议论。大龙宫寺八十多名僧人,懂经文精禅理当过家主过事的该有多少,他们平日费尽心机,今天老了脸皮,都只落得一方空纸,半点残灰!他们认真地争抢的机会,竟被这个刚到而立之年的沙弥,专门侍候慧悟大师起居的明月轻易地得到了!
慧悟大师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他无法保持“不嗔不怒”的庄严妙相,带几分恼怒地向明月喝道:“孽障,为何不早出来?”
大师的语气令众僧动心。大殿内,重新归于安静。
空无和空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点得意,一丝期待。他们都懂得这期待的内容:希望慧悟大师收回成命,起用自己。
但他们似乎都隐隐地感觉到了,这一瞬间的眼光交流,也许会触发他们心中酝酿已久的訇然雷击。
一般的和尚却只关注着明月,看他如何安全地度过眼前一切,保住他唾手而得的荣耀。
明月并没有理解大师“为何不早出来”这一问里的含义,吞吞吐吐只说了三个字:“我不敢……”大约因为“不敢”惯了,这“不敢”两个字,也是一副全然不敢的腔调。
这神情使大师顿时心生恻隐,转缓了语气说:“俱是佛徒,缘法平等,为何不敢?”
明月果然胆壮了一些,清朗地答道:“心中有万种法门,难存一丝妄念。我心即佛,不是住持!”
有资格的和尚们像约好似的,几乎一致地微微点头。有的向邻座说:“难得难得。”有的自言自语地念念有词:“还有些机锋!”
慧悟大师等大家议论片刻,摇了摇头苦笑着说:“唉,罢了!年纪虽轻,一点缘法却落到你头上!”抬起手来,将那最后的纸阄也伸向烛火。
“慢!”空无和尚终于动了声色,极具弹性地从蒲团上跳起来。他已看出慧悟大师毫无收回成命的打算,便凶悍地吼道:“大师,把这张亮给大家看看!”
慧悟大师用目光止住空无:“张张皆无,唯余者自然是有,何须再看!”
说话的这一瞬,纸阄已作飞灰。空无的一丝希望也随之化为飞灰,只留下满腹狐疑,一腔怨恨。他一边逼向香案,一边冷峻地问大师:“假使最后也是白纸,大师的传位岂不是有弊!”
“大胆!佛祖之尊,岂容诳语!就凭你这妄嗔之心,也绝非有缘之僧!”
慧悟大师终于没有收回成命,终于坚定不移地遵照佛的旨意,认定明月是玉菊的承接人,是下一任住持。
传授玉菊的大典,将在三天后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