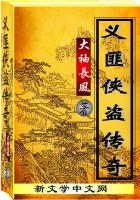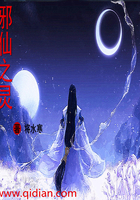第四章
明白和王骁玮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认识是在刘丽的婚礼上。刘丽是明白的学姐,比她大两届,在大学时期可没少帮忙。王骁玮和明白同年级不同系,是那届的校学生会主席,他的地位是学姐刘丽一手捧起来的。
如果没有那场婚礼,即使王骁玮日后来赫拉尔,可能也不会和明白扯上什么关系。2009年10月10号,当他站在讲台上对竞选的职位侃侃而谈时,一定没有注意到教室的某个角落里,有个女孩一边啃着驴肉火烧,一边贼眉鼠眼的东张西望。当某个夏日,他和女朋友在小湖边如痴如醉的亲吻时,一定不知道,几米之外,有个手拿羽毛球拍,浑身湿漉漉的女孩,差点掉进了湖里。
如果没有那场婚礼,即使明白在赫拉尔的大街上偶遇了王骁玮,她也不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因为她知道他,他却不认识她。哪怕之前,她与他在校园里曾经无数次的,擦肩而过。
那场婚礼发生在2011年02月10日,正月初八,因为它,明白差点误了两天后闫乐乐的大喜。
那场婚礼其实没什么,只是结束了学姐的恋爱,开始了学妹的虐情。
明白站在赫拉尔机场门口朝里面张望着,海龙王靠在车子上自顾自的抽烟。前几天,刘丽打电话,说:王骁玮要去赫拉尔开饭店,他初去那里,人生地不熟,明白,你帮忙照顾一下。怎么照顾?明白颇为危难,婚礼上他们也没说几句话,她算认识他吗?更别提了解了。
刚进校门,王骁玮的名声便如雷贯耳,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典型的高富帅,成为无数花痴的梦中情人。关于他的背景,校园里流传着多个版本,靠谱和不靠谱的,足有一箩筐。后来明白知道,他爸爸是个位高权重的官员,妈妈是一个银行的行长,姐夫是个很有钱的大老板。
关于他的恋爱,更是被传为佳话,女主角周宁天生丽质,也是富家之人,两人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大二的那年,明白宿舍有个人使用违规电器被学生会逮个正着,王主席铁面无私,就是要上报学校,最后那个学生托人找到了周宁,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后来两人闲聊无意中说起这陈芝麻烂谷子,明白问,你真的那么听周宁的话,要是学校知道了,你这个主席可能就下课了。那时他们已经慢慢熟络了,会偶尔开个不过头的玩笑。王骁玮白了一眼,说你管得着吗?
赫拉尔机场,明白还是第一次来,比想象中的要破旧的多。王骁玮终于出现了,他轻装上阵,只拎了个电脑包,别无他物。他紧锁着眉头,样子疲惫不堪。明白一紧张,竟然喊了声王主席,他没抬头,右手插兜,慢腾腾的走着。明白咽了口吐沫,生硬的一句一顿:王、骁、伟……他终于听见了,在人群中搜索着呼唤之人的身影,当看见挥手的女孩时没回应,只是露出了大男孩的,干净的笑容。
就是这个笑容,阳光的、干净的、一尘不染的笑容,让明白在无数个日子里中,夜不能寐。
陈思的班,上的心不在焉。昨天还因一个客人的投诉,和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不能怪她,那个客人实在太招人烦,长的和母猪似的,还没有自知之明,一双蒸不熟煮不烂的猪蹄壳儿,还要美个独一无二的甲。陈思歪心思一动,趁着母猪打呼噜之际,给她画了几个小王八,母猪还挺识货,腾地蹦起来,打开血盆大口:什么,为什么在我的指甲上画甲鱼?
陈思之所以敢这么肆意妄为,因为她的美甲技术,确实高超。在大连的七年,她有二分之一时间,都在摆弄手指头盖儿,用骚神的话说:哪块儿是公,哪块儿是母都能分出来。所以昨天的争吵,她显得毫无顾忌,说这几天就算白干了,我不稀罕你那几个逼子儿,有的是要老娘的地方,而后愤然离开,舒舒服服的和老桌儿逛街去了。晚上的时候,老板娘服了软,主动打了求和电话。
在陈思眼里,赫拉尔的变化很大,让她不得不意识到离开了好久的时间。耸立的高楼多了起来,道路繁华了起来,少年时经常光顾的冷面馆,早已不知所踪,替代它的是装着琳琅满目货品的商店。人也变了不少,当初的混小子们收敛了不少,每天为养家糊口而奔波着,老桌儿即将大学毕业,成为大家伙儿当中学历最高的一个,她们当初是齐头并进的,谁也落不下谁,如果她没有放弃学业,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人生?
她虽然很想念这里,但生活在大连的七年,中途没有回来过一次,即使她经常梦见这里的人,这里的街道,这里的建筑,这里的地摊货,这里的一切……要不是老同学们急切召唤,她不会回来参加闫乐乐的婚礼,要不是被友情的温暖深深感动着,她不会决定留下来……
赫拉尔是她的家乡,却没有她的家。
中考,说不清它在人生的地位,一不留神,就改变了一辈子的命运。
当初陈思以一分之差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是多少人的遗憾。又逢家庭变故,让生性叛逆的小女孩远走他乡,这一走,就是七年。七年,她寄人篱下,忍气吞声,没人知道岁月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多上伤口。
俗话说的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陈思自小就是个要强的孩子,不满十四周岁,从未出过远门的她,孤身一生踏上了前往大连的火车。绿皮慢车,没有座位,她在厕所边上站了整整二十八个小时。她是偷偷离开的,买了车票后兜里只剩下几毛钱。
二十八个小时,用捡来的矿泉水瓶,灌了几肚子的水。
在大连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农贸市场当服装搬运工,七十斤的身体要搬一百多斤的货物,弓着腰走一公里。住的是货物仓库,冬凉夏暖,全年潮湿。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菠菜汤,或是高粱米饭就着大葱蘸酱。
高粱米饭和大馇子在现在来说,那是营养丰富的杂粮,纯天然食品,甚至还成了一些饭店的招牌主食,价格不菲。‘云水谣’餐厅在赫拉尔上市后,王骁玮经理历经波折花大价钱才揽到这两种粮食的供应商。后来,‘五谷丰登’成了‘云水谣’餐饮集团的一大特色。
可前些年,在赫拉尔只有穷人才吃这两种东西。陈思没想到,到了大连,一个这么大的城市,还是要噎揦嗓子的红高粱。饭总是煮不熟,可能老板想省点煤气钱,米粒划过食道的过程,简直是在受刑。
不知道是不幸的生活,还是半生不熟的高粱饭,造就了陈思坚硬如铁的心肠。
2011年8月3日,陈思的老爹永远的离开了人世。瘫在医院的最后一个月,他无数次哀求侄子,想见女儿一面,可到死也未能如愿,老人是睁着眼睛离开的,也许在升入天堂的那一刻,他会看到女儿模糊的脸。
“你在我认为需要的时候帮过我,可能不值一提,但我记住了。即使咱们有血海深仇,都可以一笔勾销。相反,你要是惹着了我,哪怕是无意的,哪怕事情微不足道,但进我的心了,有过命的交情又怎样?到时候别怪我心狠手辣,翻脸不认人。
这就是陈思扭曲的人生观。
睿亲王府
马乔豪:09:25:34
我刚主持一婚礼,新娘子跟三婚似的,长的像凤姐。
闫勒勒:09:26:01
马乔豪,你嘴咋那么损呢,小心烂嘴丫子。
刘莹:09:27:09
勒勒,你干啥呢?
闫勒勒:09:27:30
我安胎呢,养个孩子真他妈难呀!刘莹,你来呀,跟我说说怀谭流流时的经验。
刘莹:09:27:59
嗯,一会儿我去,花哨子在吗?他要在我就不去了,我膈应他。
艾佳:09:28:01
我也想去,哎,打针打的浑身疼。
文香:09:28:05
海龙王在吗?出个气儿,我连哥要去大庆,这活接不接?
海龙王可没时间顾群里的召唤,早上他打着出车的幌子,出了家门后直奔麻将馆,此时输的风卷残云,镚子儿皆无,输的海某人大汗淋漓,骂爹骂娘。最后一把牌了,着实不错,有翻本的希望。刚打了两圈就会儿杵了,小和不要。又有人点炮了,不和,他妈的,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牌抓的太顺了,别人出牌也很合胃口,海龙王很兴奋,本想吃了上家的小鸡,再杠一下对家的白脸儿,对家刚刚打了个发财,新抓的白脸儿早晚要出手,到时候他一杠,接着手把一港后会儿杵,那就是个大满,一把牌把之前输的全捞回来了,真他妈过瘾。
不一会儿,对家果然扔出了白脸儿,海龙王大喊一声:杠,他妈的,都别动,老子杠。他笑嘻嘻慢腾腾地拿回牌桌上的白脸儿,又推到了手中的牌……这一刻,海老子愣住了,由于兴奋过度,他忘记了抓牌,直接把会儿打了出去,天衣无缝的手把一,变成了手把没。全完了,大满没了不说,按规矩还要赔诈和的钱……
海龙王把牌向前一推,说了句不玩了起身便走,别人可不同意,上前抓住他说:孙子,诈和,得他妈赔钱。
“你们随便翻,翻出来多少,全给你们……”
海龙王一脸的无赖,三人见状互相使了个眼色,其中一个掏出口袋里的刀子,顶住他的腰说:山炮,找死呀?海龙王哼了一声:捅,不捅,你他妈是我操出来的!
“哎?和我们叫号儿是吧,我他妈整死你。”
四个人扭成一团,另一牌桌的张岭见状,忙过来和解,那三个小伙子很给面子,决定不予追求,临走了还嘲笑海龙王:山炮,没钱就他妈别来这种地方,真他妈磕碜。海龙王还想动手,被张岭一把拦下了。
张岭说:算了,你怎么还来劲儿了,你诈和不给钱,还他妈有理了。
海龙王没接话茬,整了整衣服淡淡的说:谢了。
张岭笑笑:少整那没用的,要不是看在同学一场,我才懒得理这破事儿,那三个家伙可不好惹,要不是看在隋龙的面子上,他们不会买我的帐。
海龙王抬头看看张岭,斜着眼睛说:怎么,还和隋龙混呢?小心哪天死无葬身之地。
张岭瞪了一眼:你儿子他妈死了,我都不会死。
海龙王走出麻将馆,那天的天气和他的心情一样昏暗。掏出烟想抽,发现烟包空空,他没好气的把它扔向远方,大骂了句:操他妈的!靠在车上,摸着瓦盖儿头,想着如何填补财政上的空白。
海龙王的瓦盖儿头很有特色,四周没毛,中间有个比十五的月亮还圆的圆圈儿,据说在赫拉尔只有一个叫阿明的理发师能剃出此头,能剃出如此圆的圈儿。明白第一次见到时吃惊的问:是不是把碟子扣在脑袋上,照着模子剃的?
也就海龙王的才适合这种发型。虽然162cm的残废身材,但他身材比例协调,短小精悍的很精神,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小脑袋瓜子像西瓜,配上瓦盖儿头,也是个小帅哥,痞里痞气,很有男人味儿。
海龙王摸着瓦盖儿头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拨通了邢法的电话,开口就问:有钱吗,借点。电话那头问:怎么,你他妈是要去嫖啊,还是去赌。
“哪他妈那么多废话,到底借不借,老子要去翻本儿。”
“又背着老婆赌去了,你他妈能不能长点心,还以为光棍儿一个呢,有钱,给你儿子买点奶粉不好吗?谁他妈做你儿子,真是倒了血霉了。”
海龙王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不满一岁的大胖小子,心里顿时温暖了许多,他笑嘻嘻的说:你他妈还教训起我来了,你要当我儿子,我还不干呢,有本事你也找女人生一个?行了,我回家吃饭了,儿子,再见!
“去你妈的!”
邢法笑着朝手机大骂一声,挂了电话,他跳下挖掘机,造成了好大范围的尘土飞扬。这里是大庆的一个建筑工地,空旷脏乱的原野上,SD潍坊制造的大吊车、挖掘机、铲土车、四轮子在忙忙碌碌,发出轰鸣刺耳、震耳欲聋的响声。
初中‘光荣’毕业后,邢法无所事事了一年,后来禁不住老爸的打骂,跟着同村的一个师傅学瓦匠。一直以来,瓦匠在赫拉尔农村都是吃香的行业,成手的师傅,一年挣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但是要熬成师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干什么都要从学徒做起,就像妓女,刚开始要四处找经验,经验多了才有希望大红大紫。
瓦匠的学徒,不是一般的人能当的。遇到好的师傅还行,要是碰到缺德的,往死了整你,完了还说是为你着想,真是既当了婊子,还他妈立贞洁牌坊。也难怪,把徒弟教出手了,师傅就多了个抢饭碗的对手,这是个金钱的社会,什么师徒之情,都得靠边站。
邢法的师傅,就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每逢在工地上干活,总让徒弟干最脏最累的。邢法跟着东奔西走了一年,除了搬砖、推水泥车、和稀泥外,狗屁没学着。秋后算账的时候,师傅笑嘻嘻的用红色钞票塞破了口袋,而他,一个子儿也没有。这就是赫拉尔瓦匠行业不成文的规矩:学徒三年,所得酬劳,全部上缴。这也是师傅们冒着丢饭碗的危险,猛收徒弟的原因。
那是前些年的事,近两三年,学徒制改为一年,时间短,交出的徒弟也马马虎虎。没办法,由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赫拉尔立起来的高楼像雨后的春笋一样蹭蹭往上蹿,人才短缺,只能采取速成的办法。之前的师傅,懂得很多,可以算半个建筑师,现在的瓦匠,怎么形容呢?有的连勾股定理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看到同时当学徒的表哥,一年学了不少东西,刑大侠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知道是碰到黑心师傅了,如果三年他都不教正经货,那就别想出徒,即使出徒了也没有人用你,力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才四五十块钱,谁会用一个瓦匠去推水泥车呀?
而且当学徒的一年,他十根手指每天都会有几根是流血状态,膝盖上的痂就没褪去过,三百六十五天,有二百多天睡不醒,工地上的清水白菜,常常让他拉不出屎,到头来呢?啥也没学到,真他妈亏大发了。想到此处,刑大侠气不打一处来,夜深人静之时潜入黑心师傅的卧房,将其暴打了一顿。第二天辞退了他,决定另谋出路。
另谋的出路,也不是人干的活。2007年,邢法开始学开挖掘机,从一点一滴,没日没夜的干起,熬了几年终于出了头儿。刑司机现在每月5000元左右,成为了仅次于何小酷的千年老二。他挺知足,想大学生,也没有多少能挣到这个数的吧?
挖掘机司机,可是个苦差事,这年头儿,干什么容易呀?吃个饭不注意,还可能噎死呢!挖地渠、挖水泥管、铲废楼尾……每天和土喀子破石头打交道,置身于方圆几里的轰鸣之中,盯着无边无际的灰土暴尘,久而久之,让人视觉疲劳,听觉受损,感觉迟钝。
这些客观因素都不算什么,有道是: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近两年来,笼罩在邢法身边的,让他感觉工作没动力的,就是孤独,无法言明的空虚感。他二十二了,还没真正的谈过恋爱,在网上认识过几个小姑娘,面也见了,有一个连房都开了,穿裤子时,他想哭,感觉自己被强奸了一样,他不喜欢那个女孩,一点都不喜欢。
有时候,他站在镜子前,一遍一遍的扒拉自己的脸。那张连不难看,属于中等水平,长时间不见天日,还挺白嫩的,他175cm,连海龙王那个矮冬瓜都当爹了,他不缺胳膊不少腿,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有,到底差哪儿呀?他想有个家了,有个自己的家,发自肺腑的。
邢法停下挖掘机,大喊着伸了个懒腰,这一开又是不停歇的仨小时,他感觉要得前列腺疾病了。带上口罩下了车,快速的朝休息民房走去,边走边拿出手机。在夕阳的余晖伴着尘土的灰黄中,他犹豫再三,发出了一条短信:明天赫拉尔降温,出门的时候,多穿点儿,我不在身边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