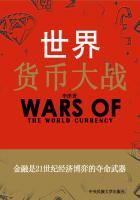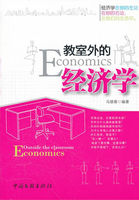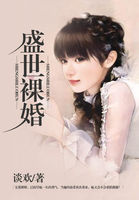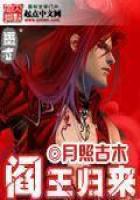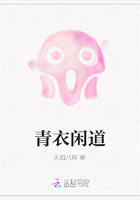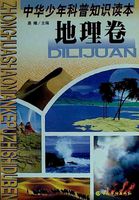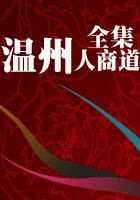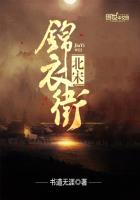历史往往不忍细看。历史之中的金融史,是否更需远观?
亚洲金融风暴、华尔街经济危机、全球货币战争……真相现场的当局者一一来到我的身边,拨开闪耀着传奇色彩的层层迷雾的过程如同拆解俄罗斯套娃,下一个内核,永远都在等待打开。当他们离去,留下的似乎是表象覆盖下被压缩得更为浓厚的谜团。谜团深处是他们故作高深的谨小慎微,抑或是我们急需答案的盲目心态?无解似乎是最好的解释,空白沉默的深处,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在世界的投影。于是我们的所谓领悟,在当局者看来,或许都错了。
2009年,深陷于经济危机的西方世界尚在休养生息,经济增速依然势头迅猛的中国却是大动作频出,政府以“四万亿计划”的刺激性决策抵御世界经济风暴来袭,“有钱”的中国喷薄出诱人的气息——这是一股悬浮于金融史深处的独特味道,唯有新贵,才具备如此生猛的能量。这股力量如同一股高速旋转的龙卷风,自转的同时,也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西方金融界的预言家、哲学家,乃至金融世家,纷至沓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是那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明星。他荣获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来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惊世谶语——成功预测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想象之中,一位能够准确预言两次经济危机的人,必定是思维缜密、行事严谨、时刻被危机论的低沉氛围所包裹的严肃学者。但是看过他的博客以后,这样的感觉一扫而光。“A funny thing happened to me this morning.” 2008年10月13日清晨7时40分,克鲁格曼在题为“一个有趣的清晨”的博客里仅写了这一句话,那一天,他被告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用“funny”这个词来形容获奖,颇具黑色幽默,让人读来更为funny。之后关于这段话的翻译版本各式各样,有的人翻译成“很有趣”,也有人说“很搞笑”。与克鲁格曼见面之后,我立刻求证:获奖后的funny究竟有何用意?一脸络腮胡的克鲁格曼笑了:“美国的喜剧演员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总是说,有一个很funny的事情要发生了,然后就开始讲笑话,我当时就是采用喜剧演员的方式来写的博客。”这位从2003年起就在美国《纽约时报》开办专栏的知名学者,很是知道如何吊起大众的胃口。
和克鲁格曼的对话从晚上8点开始,他刚刚坐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对话》现场就立即开始与多位经济学家进行近三个小时的深入讨论。即便如此,我依然能看到在这位面色疲惫的经济学家眼中闪烁的睿智光芒。也许克鲁格曼对funny这个词有着格外的喜好,当我与他谈到如何看待经济研究中的指标、会否把经济指标加入到全球经济复苏的考量体系中时,他再次“funny”了起来。“过去有一些指标是被依赖的,目前我觉得,对不起,我还要用funny这个词,目前我们处于一个特别的、很funny的时刻,原来的老规律不一定会奏效,我们一定要密切观察,不能凭经验。”
“乌鸦嘴”克鲁格曼这一次有点词穷,但也许funny这个词,正是描述人类重新陷入“不确定性”时刻的最佳词汇。经济学家扮演先知,只需要奉献犀利的预言,如同在历史的纪录片中提供精彩的画外音。然而真正的现场声,则属于制造故事的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主角乔治·索罗斯开始行动的时候,演故事的索罗斯和配画外音的克鲁格曼合力奉献了金融史上的精彩桥段:没有不能钻的经济体制漏洞,只有未能察觉到的金融监管之憾。1994年,有着“亚洲经济四小虎”之称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发展势头被外界普遍看好,而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的克鲁格曼却语出惊人,在全球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论文,批评“四小虎”的亚洲模式重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其实“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危机论虽然言之凿凿,响应者却寥寥无几。20世纪90年代初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之中,东南亚国家每年8%12%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全球的兴奋剂,处于泡沫经济的狂热成就感之中的亚洲银行与政府,进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尺度,却并未意识到自身经济储备的薄弱,以及过度依赖于美元市场在虚高繁荣表面下所隐藏的经济体制漏洞。但是,一双来自美国的犀利双眼却已经察觉到了。擅长乱世求生的索罗斯相信,虽然99%的时间里世界都是依照常规运作,但每次1%的意外发生时,所产生的冲击将远胜之前的99%。“我只对出现变动的1%市场感兴趣。”正是看到了东南亚各国银行急剧增加外债,却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有效的制度来应对外国游资迅速撤离之后的金融市场震荡,索罗斯从泰国入手,强力击中其经济体系的弱点,之后席卷亚洲,在不确定的经济发展中榨取最确定的利润。克鲁格曼对于亚洲金融危机预言的成功验证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然而与声名鹊起的克鲁格曼相比,更大的收益者,则是名利双收的索罗斯。亚洲金融旋风他一举刮走近百亿美元之巨,东南亚“四小虎”几十年经济增长化为虚无,所有人都记住了索罗斯的名字,这个与危机、风暴紧密相连的金融家从此有了新的称号:金融大鳄。
表面上看,克鲁格曼和索罗斯都是经济危机的获益者,但对于精通经济学理论的他们而言,货真价实的馈赠并不在于这“1%”的非常规机遇,而在于这个本身就充满着“非常规性”的易错世界对自己的肯定。秉承着独立经济学者刚直做派的克鲁格曼,或许是活跃在知名媒体上的所有经济专栏作家中最为孤独的一个,政商界的名流晚宴上很少见到这位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经济学家。这份孤独源自他对所信奉经济理念的坚守。博士期间师从新凯恩斯主义集大成者、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克鲁格曼,同样坚持新凯恩斯主义所推崇的经济政策对于市场的良性干预。尤其是在市场面临持久性巨大冲击的时刻,这样的干预,保护的必须是平民大众的社会福利,而非少数精英富人阶层的利益。克鲁格曼对向富人征税、提高低薪工人的收入和福利的克林顿政府赞许有加,尽管后者没有选择他来担任总统经济顾问。之后他对于小布什政府的批评则丝毫不留情面,利用《纽约时报》的专栏阵地,克鲁格曼曾尖锐地指出,小布什为保护少数大公司和富人利益的减税政策、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等,是催生美国楼市泡沫和金融的罪魁祸首,必将引发危机。2008年的经济危机成为克鲁格曼预言的最好印证,接踵而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让社会舆论普遍做出推断:对于克鲁格曼的肯定,标志着新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正如经济学与现实社会的相互博弈,任何一个概念的复归和走红,都是动荡不已的经济现象需求诠释的前奏或总结。经济现象背后的哲学研究,是投资人索罗斯的理论套路。这一套路与他起伏跌宕的生猛命运相结合,探索的是人性深处的本质命题。20世纪40年代求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索罗斯,在这所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社科类图书馆,曾经走出过哲学家罗素、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英伦百年名校里,受到的最大启发莫过于导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创建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的波普尔被誉为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这位哲学大师鼓励索罗斯严肃地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基于导师的证伪主义哲学,索罗斯提出了反身性原理,这为他建立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索罗斯看来,市场参与者的认知缺陷与生俱来,而有缺陷的认知与事件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一种双向联系,一方面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事实存在着偏向;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偏向却也影响着实际活动的进程,这有可能让市场参与者认为他们精确地预期了未来发展,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传奇大鳄索罗斯重出江湖,带着他的著作《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来到中国继续推销他的反身性理论。在北京大学的一场论坛上,我得以近距离地与这位对亚洲“情有独钟”的金融大亨交流。虽然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但精神矍铄的索罗斯给人的感觉却如同雄狮,花白的头发依旧浓密,说话的时候眉峰经常高高挑起,一双犀利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人心。如同百兽之王一般气场强大的人,会如何看待自己?我问道:“人们经常谈论索罗斯先生的投资风格,有人说,您的风格就像是狼?”
“我是鳄鱼。”直截了当的索罗斯狡黠地笑了,仿佛对于亚洲金融风暴所赋予自己的名号早已安之若素。
“但是人们说你像一只狼,发动突然袭击,把牧场里的羊给叼走,如果您不认同的话,您认为哪一种动物最适合形容你?”
索罗斯最后没有选择动物来进行比喻,而是用自己身体的疼痛来进行说明。“动物是很简单的,它碰到天敌后想的就是逃跑,或者决斗。但如果不知道到底是逃跑还是决一死战的话怎么做?你就会很紧张,一紧张腰就会很疼。金融市场就会存在这种不确定性。”这个经常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中长袖善舞的西方富翁将把握市场变化的奥秘演绎得如同东方哲学一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确定性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正是因为不可量化,所以最后毁灭了我们以量化计算所搭建而成的金融体系。”精于计算并不能抵挡所有风险,即使依靠腰痛这样的“直觉”,前景也依然未可尽知。不确定性往往隐匿于黑影之中,是将一切拖入危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一个在我的心中隐匿了许久的问题,凭着这股“不确定性”的玄妙借口,也终于代表现场的观众抛给了索罗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是不是您导演的?”
索罗斯明显有些耳背,他停顿了一下,但回答得颇具意味:“不是我导致的金融危机,我只是比别人理解力更好一些。”就像化学实验里的剧烈反应,索罗斯这样的催化剂至关重要,但是反应环境与形成条件也必不可少。索罗斯把危机看成一场迟早都要到来的爆炸,“事实上市场已经崩溃了,我们必须要进行干预”。他自己则甘愿做那个引爆的人,因为他了解规则,也知道如何玩火而不自焚。“我曾经在英国投机过,曾经攻击过英镑,但是了不起的是,他们也都承认我是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之内采取行动的。”善于从漏洞中赚钱的索罗斯,更擅长的是知道漏洞在哪里。任何人都有弱点,经济体系也是,弱点就是漏洞。讲述起前尘往事,眼前这位表情从容的老人忽然让我感觉分外陌生,远去的是那个传说中的冷血大鳄,清晰的是洞察资本与人性的智慧之王。哲学超越时空的力量带领他统御着复杂的真实世界,鏖战于最激烈的基金地带。金钱爱上了他,他却囚禁了金钱,因为他爱的是抽象,是哲学的抽象。“我是谁?”“我所在的世界又是怎样的?”他对我说,这两个哲学家所思考的终极命题他从小就在问自己,一直问到现在。他知道没有最终答案的存在,但认识自己、理解真实世界的快乐,无可替代。“我以前经常用一些抽象语言思考,但幸运的是我进入了金融界,可以把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实验室,来测试、发展我的想法。”席卷亚洲、影响东南亚国家数十年经济发展的金融风暴,原是一个理解世界的具象论据?不当金融大鳄的亿万富翁不是一个好哲学家,索罗斯的哲学实验是否太过宏大?抑或之前哲学家们的发声太过微弱?这些问题,让我也陷入了哲学家一般的沉思……
巧合的是,克鲁格曼和索罗斯都有着犹太血统,前者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后者出生于东欧匈牙利。有着“犹太人的第二本圣经”之称的犹太古书《塔木德》被犹太人视作经商处世的宝典,这本由2000多位犹太学者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智慧进行发掘与思考的著述,被索罗斯形容为“改变了自已的财富观和一生”。关于金钱,《塔木德》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赚钱不难,用钱不易。花一块钱,就要发挥一块钱100%的功效。”作为在金融界和商业界独占鳌头的种族,犹太人的心中,关于金钱的真相,究竟如何?
2009年4月,犹太裔中的名门望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六代掌门人大卫·罗斯柴尔德决定接受我的独家访问。消息刚公布,我的博客就被各种问题挤爆。关于这个家族的传说实在太为震撼,也太过神秘。当250多年前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普通犹太商人。仅用了不足100年的时间,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金融命脉,在其鼎盛时期,势力范围遍布欧美,所控制的财富甚至占到了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达到5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全年GDP的四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债由他们发行,每天黄金交易的开盘价由他们来确定,世界各国的股市都随着罗斯柴尔德资金的走向而波动,他们被称为当时凌驾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之上的欧洲第六帝国,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折断的五箭齐发的族徽,也因此成为世界金融权力的象征。那时“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在欧洲的影响力远比今天最当红的流行巨星更深入人心,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里,棺材铺的老板都会用这个名字来嘲笑贫穷的犹太音乐家。以色列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城镇和街道不计其数,南极洲甚至有一个岛就被称为“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有着肖邦和罗西尼为其谱写的乐曲,还有巴尔扎克和海涅为其撰写的书籍。财富与名望的双重桂冠一路顶到今天,罗氏家族的历史,有着太多的灿烂与辉煌。
走进罗氏家族的北京办事处,首先进入视线的便是从地角顶到天线的高高书架,书架上摆放着的都是与这个家族有关的传记,“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印刷在各式装帧精美的书本上,颇有漫漫家族长史的厚重气势。大多数的中国公众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许还不甚熟知,这个家族对中国却并不陌生,早在100多年前他们就来到了大清帝国的紫禁城。书架的显眼位置,当年清朝重臣李鸿章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字迹工整的亲笔信,如同文物般珍贵,亦如同勋章一般隐隐散发着一个庞大的西方家族渗透到遥远东方的显赫势力。
虽然这个犹太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已久,但最终引发中国公众对它产生强烈兴趣的,则是一本名为“货币战争”的畅销书。这本书讲述了西方近代史与金融发展史当中,国际金融集团及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如何控制世界财富和金融法则,算得上是一部揭秘性书籍。第一章的标题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道无形”的世界首富。与大卫·罗斯柴尔德的对话现场,我问出了无数网友在我的博客里提到的热点问题:
“你们家族究竟有多少钱?”
“我觉得我不告诉你这个答案你也不会惊讶的,我们从来不对外公布。”这位年过六旬的家族掌门人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问题,开诚布公的回答却将秘密掩盖得滴水不漏。“我们的祖先250多年前创建了企业,到了今天,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再去成天数钱,已经不是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了。”身为“富六代”的大卫早已远离了对于数字的追逐,更为看重的是触碰不到的影响力。而《货币战争》一书在中国为他的家族所带来的影响,显然并不那么令这位衣着精致的爵士满意。他对我说,他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想这可能跟一本在中国出版的畅销书有关,但是这本书和我们家族的真实情况还是有差距的”。
差距在哪里?大卫·罗斯柴尔德特意嘱咐栏目组,自己无意和这本书的作者宋鸿兵见面,因此两个人的对话无法实现。但我的同事们还是兴奋异常,以《对话》的解读方式制作了一份精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档案。当我将这份档案交给大卫爵士的时候,内心忐忑,不知道我们的解读在他看来又将如何,教养良好的爵士抚摸着质地精良的页面留下了一句出乎意料的感叹:你们的做工太细致了!只是感叹归感叹,成长于欧洲的爵士依旧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傲慢,关于罗氏家族发迹的历史细节,他没有任何与外界分享的欲望。同样身处节目现场的里特尔咨询公司中国总裁托马斯·席勒透露,历史悠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各国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来自政府。
“说到这个家族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依靠250多年延续下来的声望和影响力,只和政府做一些很大的生意。你觉得这样的描述准确吗?”我和大卫进一步确认。
“是的,我们确实有很多政府的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个祖训:‘我们一定要和国王一起散步。’”
这个祖训更将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的生态系统推向迷宫,未知的财富数量、远离大众市场的政府交易,却又在冥冥中左右着每一个平民的生活和命运。大卫似乎很愿意聊一聊“命运”这个神秘的词汇,对我说人人都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掌控命运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我们法语有一句俗话,胃口再大也不可能吃下所有东西。”这个热爱美食的法国人将慢慢消化的道理运用于家族业务中,相信每年10%15%的增长已经能够让生意越做越兴旺,“做得太大,你可能会丧失掉你的灵魂。”这或许就是灵魂不死的罗氏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
访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北京办事处的前夕,我曾经借阅过一本名为“世界银行家”的书本,书中的一句话令即将对话大卫爵士的我颇有些泄气:“如果您想完全了解这个神秘的家族,那是几乎不可能的。”有人说,以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像是一艘航空母舰,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则更像游弋在深水区的潜水艇。“低调内敛”成为越来越多的媒体描绘罗氏家族在这个时代的行事风格时所惯用的形容词,昔日庞大家族如今的刻意隐匿身影,是担心树大招风,还是为了故作姿态?以深色调着装沉稳露面于节目现场的大卫爵士淡然一笑:“我们并不是有意把自己藏起来,也没有刻意地保持神秘或者是低调,其实我觉得老是说自己没有什么意义,能够保持一定神秘感的话,你会更长寿一些。”如此看来,名利场果真是新贵们的江湖,历经风雨的百年望族,更在意的是缤纷江湖之外的万古长青。
对于我的问题,罗斯柴尔德的回答几乎都以NO开头。面对那一副“你们,都错了”的表情,我没有感觉迷惑,而是心生一分隐隐的惶恐。中国的财经媒体平台从他傲慢而淡定的表情上,比照出的究竟是什么?追逐财富的商业中国是否跑得太快,使得灵魂跟不上脚步?身处全球金融的江湖之中,新入场的我们都想当那个积极的演员,而不情愿做一名冷静的旁观者。保守、神秘、谦逊、坚韧,从在这片江湖游刃有余已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世界银行家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与风范。说到底,货币战争比拼到最后,看的就是谁坚持得最长久。岁月悠悠,朝夕哪堪回首?
透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弥漫了250多年的风烟,也许只能揭开欧美金融史的一角冰山。两年之后,当我来到世界上最为古老的金融之都伦敦金融城,才亲身感受到这里所隐匿的历史更为浩大——800年的岁月灰尘,厚重到令人窒息。那次的对话现场就设立在伦敦的“心脏金融城”,讨论的主题是这片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地域在800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于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傅思途现场浓缩了伦敦城的历史,从罗马人在这里建立贸易点开始,几百年来一直承担着贸易中心的角色。国际化的进程加速了伦敦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场大变革基本废除了所有限制性的措施,让这里变成了一个轻松的俱乐部。取消几乎所有全球贸易限制的结果,便是大量外国公司的涌入。以美国为发端,之后各国争相效仿,最终让伦敦城变成了金融城,一座真正的国际贸易中心。
“轻松俱乐部”的伦敦金融城,真的轻松吗?站在金融城中心那座被誉为“银行之王”的英格兰银行门前,我似乎看到了索罗斯诡异的笑脸。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辉煌不再,英格兰银行却威信犹存。只要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哪怕经济已然下滑,英镑依旧可以坚挺,不需要其他理由。索罗斯却看到了英格兰银行外盛内虚的本质和英国身处欧洲汇率体系之内维持英镑兑换德国马克现有汇率的勉强。1992年9月15日下午,索罗斯将借贷到的大量英镑兑换为德国马克,以巨大的卖出压力迫使英镑贬值。英格兰银行虽然动用33亿英镑救市,最终也未能敌过索罗斯以及在他的反身性理论影响下牵动的国际游资对英国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充当过“全球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最终无力维持英镑汇率,英镑这一曾经的国际货币一路贬值,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索罗斯此时再用马克低价买回英镑,一举净赚20亿美元。如果说1992年的英格兰银行事件是政府对钞票兑换的放纵所导致的货币贬值,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这座古老的金融城牵连之下遭遇对冲基金等金融产品冲击的时刻,自由贸易市场的集体损失,又应当由谁来埋单?监管,还是开放?持续兴盛,还是慢慢衰微?这样的疑虑似乎不仅仅属于伦敦,而是所有金融历史悠久的城市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置身于国际金融中心历史远超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城,我仰望着古老的灰石建筑所搭起的穹顶,看着大屏幕上跳动的股票数字和戴着蓝牙耳机匆忙涌动的人群,一时之间颇有穿越的感觉。这里成就了索罗斯的金融“声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学到的哲学与经济理论,终于在这座孕育了自己的城市得以论证,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圆满轮回。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金钱同样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第一桶金,家族第一代梅耶的发迹,正是来源于德国黑森公爵所留给他的300万英镑。而这300万现金原是英国政府向黑森部队支付的军需费用,离开德国逃亡丹麦的黑森公爵将这笔财富占为己有,并在临走之际赠予了那个与自己私交甚好的犹太青年——梅耶·罗斯柴尔德。历史的故事总是环环相扣,彼此关联,这座历经世事的古老都城如同依旧坚守于金融市场的“傲慢”英镑,亦如一位长寿的贵族,它在那里,就已经足够。
在这座国际金融中心,英国财政部金融大臣马克·霍班告诉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伦敦很愿意作为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参与其中。在现代金融史上,或许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能够成为下一个真正有实力和影响力的金融交易主场。我只希望那一天能够来得更早一些,从而能够作为亲历者,在主场见证一段属于东方的金融传奇。
身在客场,与英国金融界的对话几乎全程用的都是英文。在英语的故乡全方位地感受英文之魅,这样的经历对于毕业于英语专业的我而言,实是一份莫大的享受。漫步于有着17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精品百货公司哈罗兹,我忽然听到了滚石的旋律: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But if you try sometime you find
You get what you need
这首《你不会总得到你想要的》和其他响彻于20世纪90年代的滚石经典歌曲,曾经陪伴我度过每天念英文的大学时代。那些颓废又美好的旋律,和英文单词一样印入了青春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如今时间、空间均已改变,所幸音乐还执着地继续着,英文的情结,也并未忘却。记得在北京大学与索罗斯的那场对话,由于设备所限无法进行同声传译,于是我用英文主持完了全场。第二天许多同行打来电话:“伟鸿你还能主持英文版《对话》?!”李瑞英大姐还激动地替她那位中科院的博士先生,表达了对我英文口语的赞赏。
常常会有人问我:“伟鸿,你为什么很少用英文主持?”
“因为对话的舞台是在中国,中国才是我的主场。”这是我的回答,也是我为什么不常用英文主持的所谓真相。语言的背后,更为重要的,是立场。
告别伦敦的时候,我把微博的头像换成了在雾都拍摄的一张深秋的风景。天空清澈湛蓝,树叶闪耀着醉人的金黄。一眼便能望到遥遥远方的透彻,让人心旷神怡,只是不知道,那层笼罩伦敦的迷雾,去了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