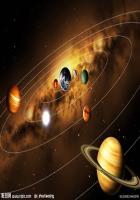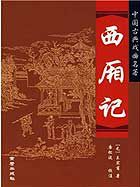在飞仙楼前观战的狼风山,看见豹三威被黑衣人救起,心里正在恼恨不已,又见蛙三娘处境危险,不由得捏了一把汗。连忙故伎重演,暗取火云标在手,把手一扬,喝一声“着”,只见那黑影狐金花一个空中换位,火云标竟敢从她耳边“嗖”的一声,飞了过去。原来那狐儿狐金花欲取碧波水妖蛙三娘性命心中并无十分把握,就来了个虚张声势的动作,实际目的是“回马便走”,脱离战场。就在她折身的时候,狼风山的火云标洽好打了过来,被狐金花侥幸躲过。可是狼风山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个狐金花能躲过他的火云标,武艺、道行皆属出类拔萃,决不能等闲视之。为防不测,急命飞仙楼众值事皆应按照分工各就各位。不得擅离职守。
那狼风山将人员安置停当,便急匆匆地来到闻香阁,一进门,却不见一人,便把看守值事找来问询。那两个看守值事煞有介事地言道:“跑不了,在那桌子腿上绑着哩”。进了闻香阁,一看,也惊的呆了,那桌子腿上只剩下一堆空绳套套,那阿猫早已不知去向。
狼妖狼风山气得一下子坍坐在那软席沙荣垫子椅上,半天没有说出一名话。心中想道:“完了,完了,一切都完。我狼风山在西月教主面前人称智多星,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其实也没有什么过人的能耐。古天存被人盗走了,那是自己没有防备,让人钻了空子。可是这一次又说明了什么?好好地绑在这个屋子里,就那么神密地失踪了。从房间内外的动静来看,没有外人进来的足迹,难道说会是内部出了问题?会是什么人来把他救走的呢?”狼风山百思不得其解。
他无意识地拿着空绳套套左看右看,结是死的,并未解开。啊,他明白了,那阿猫是从绳套里脱出身来跑掉的。
“哼,我本来就不该从迷幻中将他唤醒!”。狼风山喃喃地小声言道。
蛙三娘在外边与人斗杀了大半日,刚一进入飞仙楼的大门,就听说阿猫不见了,急忙跑上楼来想问个明白。见师兄狼风山无精打采地坐在沙发上,便悄悄地问了一声:“听说阿猫跑了?”“是啊,跑了”。这位平日趾高气扬的道兄,今天说话的声音出奇的低,低得几乎让人听不见。她知道,他现在心里烦得很。没有接着往下问。
其实,她蛙三娘的心里也是烦得很。一来自已的作事不捡点,被狼风山抓了把柄,成了狼风山手中的玩具,连索取男人“真阳”这样下三赖的羞活儿也让自己来干,真是丢了祖先八辈万奶奶的人了!二来是那黑影女子狐金花那一套变化千般的博杀手段真个十分了得,如果不是狼风山助我一标,今日定遭其手。想到这里不由得心里又矛盾起来。反正自已的事还未到底,离了狼风山还是不行,便又厚着脸皮,笑着搭讪狼风山:“师兄,别难过了,事已至此,我们只好面对现实。当务之急是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三娘说的不错,我们是应该好好商量下下一步的对应之策。只是眼下,对方对我们略二三,而我等对对方却连一二也不知。这就等于一个瞎眼人和一个明眼人博杀,凶多吉少”。狼风山确实智力过人,在自己连连失手的情况下,能够静下心来,对自己的薄弱环节看得非常清楚,实属难得。
“师兄,依你之见,咱们如何才能探得对方的底细呢?”蛙三娘接着问道。
“唉,是啊,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探明对方谈何容易?”狼风山发出叹息。
“如果不行,我们不如暂且撤离,等我们把情况吃透了,再来报仇也不迟。”蛙三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撤,撤到那里去?我们回去了又如何向师父交代?”狼风山又打出了一张她蛙三娘极不愿看到的牌,既含虚地揭了她蛙三娘的老底,又轻易而举地把一盆脏水泼到了她蛙三娘的头上。好象这一切都是她蛙三娘造成的,他目前的处境完全是为了她蛙三娘。蛙三娘真是丢人打家伙,受窝囊承情,一肚子的苦水怎么也倒不出来。
狼风山毕竟是狼风山,刚才还满面愁云,当蛙三娘再看他时,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却又挂上一丝谁也察觉不到的阴沉的笑容。蛙三娘知道,这是又一个罪恶的计划在他脑子中正在形成。
至于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蛙三娘自然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只是乖乖地照他的意思去办就是了。
夜幕空垂,弯月如钩。
狐家典当商行后院南侧古字楼内,三楼上两间大厅灯火通明,可是外面却看不到一丝灯光。
佝偻大师行云正在和他的得意弟子狐儿狐金花在轻轻地说着什么。从脸色一看,狐儿狐金花显得很兴奋。笑着对师父说:“师父喂,那蛙三娘平日里您总是说她如何了得,今日交手,俺倒觉得也不过如此,就俺这三招两式,一阵博杀,就弄得她狼狈不堪哩!只可恨,那黑羞陋大汉,俺救了他,连一个谢字都没有,滚身起来就驾起一阵风逃命去了,真让人扫兴!”
佝偻大师行云见他的弟子这么轻敌,脸上的笑容一扫而空。低言沉沉地告示诫道:“太不什钱了!一场小胜就令你如此张狂轻敌,犯了江湖大忌!你以为你是博艺高超取胜的吗?非也!一来是蛙三娘与那黑羞大汉战了好此时辰,体力有所下降;二来是你不知江湖险恶,初生牛椟猛如虎。一阵猛杀猛冲,乱了她的阵脚,使她有所顾忌,不敢放开与你撕杀;三来你小师叔一直都在暗中保护。你连句话都没有,就莽然冲了进去,我们实在是揪心的很!”
挨了师父一顿训斥,狐儿脸上顿时没有了笑容。小嘴噘得老高。
九劫仙姑文祖英见狐儿不高兴了,便过来安慰道:“我们的狐儿还年轻,机会多着呢。那蛙三凶狠无度,嗜杀成性,年纪轻轻的狐儿就敢和她博杀一番,而且还得胜归来,就已经不错了,将来我们狐儿定成大器!”
狐儿没有说话,眼眶中噙含着悔吾的泪花。
崂山道童蟒春风坐在古天祥的床边,正在为古公子的昏昏沉沉而发愁。
自从狐儿将他赤身果体背回来到现在,一直昏迷不醒。开始他以为古天祥被那蛙三娘折腾得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就好了。谁知道竟然睡了一天一夜还不见睡醒的迹象。到了这时,只好过来问佝偻行云。佝偻大师听了蟒春风说的情形,便朝古公子床边瞟了一眼,说道:“我来试试。”
佝偻大师来到古天祥的床边,用手指轻轻地将古天祥的眼皮翻开一看,不由得惊呼起来:“呜呀,不好!”弄得众人莫名其妙。
狐儿笑道:“又怎么了,师父也,他不就是睡着了嘛,那里来的那么多‘不好’。”狐儿显得不以为然。
“你们有所不知,这古天祥可不是睡着了,而是中了‘毒’,是一种世上少有的剧毒,叫做‘警世幻毒’。中了这种毒的人,与平的药物中毒不同。平常的人中了物之毒,可以利用事物的相克原理解之,中了警世幻毒就不行了,中毒人一天到晚地沉浸在幸福的幻境之中,身边仙姬成群,房事不断,最终脱阳而死。要救治这种人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千年老蛙身上‘绿茶毒’,用温水冲开,强行灌入患者腹中,以毒攻毒,只可惜,据我所知,这种东西眼下这诺大的城皋城里只有她蛙三娘一个人身上有,彼此正值交攻之际,此妖断然不会给我们;二来可由一个道行高深之人用道行功力将幻毒逼出。除此之外,别无良法。”
蟒春风说道:“师兄,眼下只有你了。我们总不能再跑到到崂山去搬了师父来,是死是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是啊,师兄,春风说的对,就是我们到崂山搬师父,这一来一去,又需要好多时间,救人性命恐怕来不及了。”文祖英也如此说道。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我就只好试试了,只是救人的事,是马虎不得的。”佝偻大师说罢,便把古天祥搬起身来,让他坐起,自已坐在古天祥的身后,闭目收气,双手亮掌,放在古天祥头部两侧,念动真言,暗运神功。只见得古天祥头上有阵阵烟云向上升起。
在说那阿猫,那天在闻香阁与那蛙三娘对了一眼,看到一种异样光色,便觉得头脑昏昏沉沉,只想睡觉,因此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一睡就是两天两夜,如果不是狼风山用法力将他弄醒,到如今还是想要睡觉。其实也是中了毒。只是这种毒的作用与古天祥的不同。阿猫中的毒叫‘爱眠乐’,只要睡了,便觉得舒坦无比,否则就头晕恶心,让人如同得了大病一般。那蛙三娘为了盗取古天祥之真阳,要行儿女偷窃之事,让阿看见了成何体统?阿猫在一边碍手碍脚,倒不如让他一睡了之。睡得越久越好。
谁知道,事有凑巧,蛙三娘眼看自己就要成功了,偏偏遇见了多事的黑影丽人狐金花搅黄了她的好事,白白费了一番心机。按说蛙三娘的道行功力,拿下这次劫人事件本不成问题,只是她当时正是欲火高峰之时,求欢心切,不曾想着有人打劫。等她回过神来,穿好衣服,那黑影就象一只黑蝴蝶忽忽悠悠飘远了去。
阿猫被狼风山唤醒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正处在环境险恶之中,第一句话就问公子去了哪里,狼风山吼道:“嚷什么,小心我搦死你!”瞧着狼风山凶狠的样子,再也不是刚来住店时那会儿见人就笑着打招呼的模样。便就此把嘴闭了,再也不作声。这才意识到他和公子再相见已经是不可能了。心中不由得怨恨起公子来:“要你走,你不走,这下可好了,走不了了,考什么状元,状个屁,说不定连小命还要赔进去呢,妈的,都是那什么蛙三娘闹的,见了公子就情意绵绵的样子,真******叫人恶心!”
正当他阿猫心中恨恨不平的时候,又见过来几个人不由分说竟然把他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阿猫不由得纳起罕来:“哎,这是乍了?难道说我会跑了不成?”
“哼!不怕你跑,我们还不绑了呢!”动手的人说道。
绑就绑吧,到了这个时候他阿猫有什么办法!
看着绑他的人走远了,那只令人喜爱的小怪兽又晃动着身子走了过来。喵哇喵哇地叫个不停。阿猫心中挺纳闷的,这小精灵今天是怎么了?老是冲着我叫,岂非咄咄怪事?咋一看,绳套了怎么那么松哩?一转动身子,却轻易而举地挣了出来。阿猫看看四面没人,便蹑手蹑脚地出了闻香阁,沿着走廊,走到尽头,顺着朝西的那道墙沿,一直沿了过去,到了拐角处,往墙外一跳,就那么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
重新获得自由的阿猫也顾不得心神劳顿,肚中饥渴,顺着回家的路一路小跑。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救出公子,公子就是他的命!
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庄上,碰见一个老翁挑了一担儿炊饼正在叫卖,阿猫来到跟前,肚里正饿得发慌,伸手拿了一个便含在嘴里咬了一口,这边从口袋中往外掏钱,谁知道走得急了,那银子都在行李中放的,不曾拿得一分出来。那老翁见那阿猫掏了半天,不曾摸出一文钱出来,就认定是来唬吃的,便一把将那阿猫抓在手里,气狠狠地说道:“好一个不知道死活的流浪混子,竟来到俺老翁的摊子上唬起吃的来了,俺就是不打勤的,也不打那赖的,就是专门打那不长眼的。昨天一个偷饼贼偷了俺的饼子,俺倒不曾捉得,今番捉了一个唬吃的倒也算数。别人拔了萝卜,俺就让你来把这坑给平了,今天你不拿出钱来,就别想走出俺的大门。
阿猫一听,顿时从头上冒出了汗来。连忙解释道:“爷爷,是这样,俺是……”阿猫的“是”字还没说完,只听那老翁说道:“俺是什么也不听,只是要你把钱给俺拿来!”接着那老翁一声招呼,从一个庭院落里跑出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不由分说将阿猫三下除二地捆了个结结实实,往那院落中一个小屋里一推,拴在一个柱子上,然后把门一关,竟自干别的事情去了。
阿猫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好好吃上一顿饭,又为了赶紧把公子救出来,一路奔波,饥、渴、累急绞在了一起,脑子哄的一声,便晕了过去,人世不省。
待到这一家人该吃晚饭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那老翁卖完了饮饼,挑着空担子走回了家门。洗了手脚,便坐在桌子上准备用餐。忽然想起了下午唬吃饮饼的小混子,便招呼问儿孙们那小斯去了哪里。大孙儿说道:“那里也没去,就绑在那小屋的柱子上哩。“那老翁的气性此时已经消得大半了,便吩咐道:“算了,算了,把他放了,让他来吃了饭,就走得了”。
大孙儿见爷爷这样吩咐,就开了那间小屋,就去松绳子放人。却见那人竟不会说话了。大孙儿便心中慌了起来:“爷爷,你快出来看啊,他这是怎么了,不会说话了也。”
那老翁见孙儿这样说了,急忙来到这小屋里仔细观看。只见这孩子双目紧闭,气息微弱,连忙把绳子松了,与孙儿一道把阿猫抬到自家床上放好了,盖上被子,在自家灶火上烧了一碗红糖姜汤缓缓从阿猫口中灌入,约莫过个巴时辰,才见得那阿猫渐渐睁开了眼睛。
那老翁见这孩子睁开了眼睛,便呜呜地哭泣起来:“孩子,是爷爷的不是了,其实你只是吃一个饮饼,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平日里俺也不知送了别人多少饮饼,也不曾这样,今日里差点坏了孩儿的性命,爷爷愧对天地了”。
“爷爷,快不要这样说了,确实是孙儿我的不是了,不过俺也不是故意的,俺的银子倒有不少,只是都在俺主仆二人的行李里边,不曾拿来得了,俺就是死了也不大要紧,只是俺那公子古天祥的性命全在俺一人身上。”阿猫说着就要起身离去。
那老翁听了阿猫说的“古天祥”三个字,不由得心头一惊:“你刚才说的什么?你能否再说一遍?”
“俺那公子古天祥的性命如今还在虎狼之口中,危在旦夕。俺须立即赶回家中,央人相救才是。”阿猫说着就要起身。
“你说的可是高阳苗顶古大员外古明月的儿子古天祥么?”老翁紧紧追问道。
“正是。爷爷你就让我快点走吧,晚了可就来不及了!”阿猫说着就下了床。
“那你可知道我是谁吗?”老翁问阿猫。
“爷爷,俺也不管你是谁了,如今俺救人要紧。”
“孩子,你就不要再跑路了,俺正是天祥的亲舅舅乐兴元啊!”乐老汉把关系一下挑明了。(阿猫一听是古天祥的舅舅,顿时泪如雨下,把如何到了城皋,住进飞仙楼,又怎样被狼风山、蛙三娘等人所困,古公子又如何下落生死不明,他又如何逃了出来,一五一十地向乐老汉说了一个清清楚楚。
那老汉听了,便对阿猫说道:“孩子,眼前只有这一个办法,天祥的大舅舅,我那亲哥哥就在飞龙顶道观主事,他修为高深,武艺高强,欲救天祥非此人莫属。”
“爷爷,那咱们就不要耽搁了,快点走啊?”阿猫急急摧促道。
乐老汉备好车马,让阿猫也都坐上,手中长鞭一扬,打了一个响亮的鞭花,白马奋起四蹄,向着飞龙顶方向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