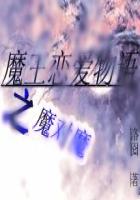长庆六年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她是我的姐姐,有些手足是为了扶持,而有些,注定用来分离。
她出嫁的那天清晨,至我御座前告别,无多少喜悦抑或伤悲的神情。所有该说的话已有礼官代我说尽,而那些不该说的,我没来得及告诉她。
我也没能力告诉她。
落日融金,她之于我最后的印象是血色残阳,映衬姜宫琉璃瓦上璀璨霞光,万千宫羽列阵飞过她行过的轨迹,一点一点走出我的生命。
我木然负手立在城墙边上,鼻腔中漫上酸涩。
这样也好,我想,便不再相见,隔不断思念,便斩断尘缘。
有穷羌族再度进犯姜国边境的消息自前线传来,有时候忍能换来两国世代交好,可是我第一次隐忍,送走顺德,第二次隐忍,死我无数姜国子民。若是再忍,想必天下便真的以为这姜国新主,当真是个脓包。
临行前拜别太后,她突兀地朝着我说了一句:“凡事,当以家国为重。”
我既没点头,亦没摇头,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选的是姜国最精备的士卒,用的是清君侧最正当不过的名讳,连头阵探敌,我亦随侍卫同往。有穷一族接连败退,只是最后在镇江那一战,为了图快,我命士卒追穷寇至关外,那原本便是放牧为生的有穷国最得力的地势。我低估了这点,打得极是吃力,待侍从拼了命将我从鬼门关背回来时,我几乎没了半条命。
在随军御医低低抽气声中,我用手背逝去嘴角血痕,笑得畅快:“这一仗果然痛快。”
领军的曹郁最为审慎,一直劝我此时收兵,吓吓有穷即可,何必如此赶尽杀绝。他觑了一眼,踌躇道:“况且,顺德公主……”
我飞快地沉下脸色。
曹郁垂首,迟疑着开口:“战前,太后……曾托臣告诉陛下一句话。”他没敢抬头看我,像是下了很大一番决心,“为了一个女人,若搭上国家,陛下百年之后如何有颜面去见姜国列祖。”
我笑了笑,转视他:“那劳烦曹将军也把我这句话带给太后吧。”我冷淡神色,将多年怨怼融入诅咒一般的句子里,罔顾曹郁的瞠目神色,冷冷开口,“她毁了我最珍惜的,我便毁了她誓死也要守护的,这姜国山河。”
曹郁睁大双目看我。
我调转身子朝内,许久,才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你说,这仗打下去,有穷大约什么时候会呈上降书?”
曹郁没有开口。因为他实在料想不到,在这仗打得最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没等到有穷王递上的降表,等来的,却是深夜独自而来的她。
我的姐姐,顺德。
距离长庆六年送她离开已有四年,四年,有多少记忆可以欺骗,却永远也骗不了自己,那个婷婷袅袅走入我军帐内,那个披着深色斗篷的姑娘,那个苍白着双颊同样苍白双唇的女子,她是我朝思暮想的人。
我茫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没来得及穿上衣服,露出胸
口大片斑驳伤痕的肌肤。
她的脸色白了一白。
有类似喜悦的情愫,点点涟漪荡入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