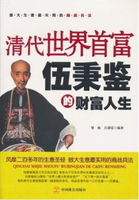在那儿生活很省钱。在小旅馆里解决食宿,一周只要七美元。食品卖得特别便宜。我们戏团的人总是去吃酒吧柜台上的便餐。只需五分钱,就能喝上一杯啤酒,吃上一样可口的菜肴。
戏团里总共十五个人(也许不止),扣除火车卧铺的票钱,每人都能省下一半的薪酬。我一周能拿七十五美元,总是按时存五十美元到曼哈顿银行里。
太平洋沿岸地区是我们此次巡演的目的地。有一次跟我们同去的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得克萨斯州人,他的戏跟我们排在一起。他是个演空中飞人的,但正在犹豫要不要改做职业拳击手。我每天早上都陪他练拳,总能打中比我更高更大的他。后来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好。练完拳之后总要一起吃午饭。他的家人是得克萨斯州的普通农民,因而他跟我谈到农场的生活。于是很快我们就想到要放弃做演员,一起合伙养猪赚钱。
我们大做致富梦,计划用两千美元的存款,在阿肯色买两千亩每亩五角钱的地,余下的钱用来买猪和打理土地。我们按猪每年一窝生五头计算,如果一切顺利,五年内每人就能赚十万美金。
每次从火车的窗户看见养猪场,我们都激动万分,吃饭、睡觉、做梦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猪。直到买了一本教人科学养猪的书,看到里面详细描写了阉猪的方法,我的满腔热情才冷却,渐渐把这念头抛诸脑后了。
这次巡演,我还带上了我的小提琴和大提琴。我从十六岁开始,每天都要在卧室里练习四到六小时。而且每周我都要请戏院的乐队指挥或是他推荐的人来教我。我渴望将来成为一名首席小提琴手,如果实现不了这愿望,那在轻歌舞剧团里拉琴也可以。后来渐渐长大,我意识到自己不是这块料,于是只得放弃。
1910年,依然富有边疆时代精神的芝加哥还在以它的丑恶吸引着人们,偏僻而脏乱。在我的想象中,它跟俄国大草原相仿,应当有着一望无际的原野。这座城市有着拓荒者那种蓬勃向上的彪悍精神,但男性那种寂寞和愁闷又隐藏在它骨子里。这就导致了一种特殊的“歌舞剧”风靡全国。剧里面是一帮举止野蛮的丑角和二十来个合唱团的姑娘,她们中有的年轻漂亮,也有的年老色衰。丑角们挺能逗笑,而这戏的内容却比较粗俗猥亵,强调男人的重要性,再点缀一些讲述两性纠纷的庸俗情节。说也奇怪,这戏不会让观众们联想到****,其中的故事反会惹人同情。
我们到芝加哥之后,住进了瓦巴希大街上的一家旅馆,在商业区外面。演歌舞剧的姑娘们也住在那,所以这冷清和寒酸的旅馆也显得别具浪漫。我们在每个城镇都会找那些姑娘住的旅馆下榻。我也渴望一段艳遇,不过却不曾实现。每天夜里,附近很高的铁轨都有火车疾驰而过,闪烁的光影投射在我卧室的墙壁上,如同老式电影放映机一般。在那家旅馆里我没有什么传奇经历,但还是很喜欢那里。
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总是显得安静而扭捏,不跟其他人在一起。我偶尔经过她身边,也始终没鼓起勇气跟她搭话。从芝加哥去太平洋沿岸时,她和我们同车。有一次,我在车厢里看见她跟我们戏团里的一个演员说话。后来我从那个演员那儿听说她得了梅毒,十分可怜。
到了西雅图之后,她不得不进医院,离开了歌舞团。车上所有的剧团都给她捐了钱,不过这样一来她的事也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不过幸运的是她被治愈了,后来又能够再加入歌舞团。
那时候,美国的妓院到处都是。芝加哥一家万国妓院更是声名远播,据说那儿拥有所有国家的妓女。房间也装修成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是全世界最讲究、最昂贵的一家妓院。百万富翁、行业巨头、内阁成员、议员和法官都会光顾那里。
我越向西走,越觉得那些地方惹人喜爱。从火车里只能看见大片的荒野,虽然清冷落寞,但那种一望无际却让我眼界开阔,充满希望。那儿的城市个个都是一片繁荣,这也让我欢欣鼓舞。我们在其他剧团结交了很多朋友,经常六七个人一起在城镇的妓院区里聚会。有时我们跟老鸨套上了近乎,她那晚就会把妓院全场包给我们。也有些爱上了演员的姑娘,跟着他们到附近城镇去了。
随着继续西进,一路所见的城市越来越干净了,这让我十分开心。我们经过温尼伯、塔科马、西雅图、温哥华、波特兰这些城市,其中温尼伯和温哥华基本上都是英国观众。对于一心向往美国的我,能在英国观众面前演出,也未尝不是轻松愉快的。
终于抵达加利福尼亚州了。这是个在太平洋海岸绵延千里的乐园,风和日丽,到处都是橘树林、葡萄园和棕榈树。1910年,我们到达到美国通往东方的出口--旧金山,那地方在经历了1906年的那场地震,或是人们所说的那场大火之后,已经被重修了。几乎看不出毁坏的痕迹,连我住的那家旅馆在内,所有东西都是崭新而美丽的。
我们在那里的皇后戏院演出,锡德·格劳曼这个戏院老板和他的父亲都为人和善,爱交朋友。那时候,戏报上第一次没有提到卡诺,而登上了我的名字。那些可爱的观众们在演出时笑声不绝,沉闷的《银猿》在那里上演时也能场场客满。格劳曼很高兴地邀我在卡诺戏班演出结束后再回来演出。在旧金山,能让人感觉到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与此相反,洛杉矶则让人感觉丑陋。那里的居民像是患有贫血症似的,个个脸色蜡黄。天气虽然很温暖,但没有旧金山那种清新的空气。
那时候我觉得,将来,即使有一天,好莱坞只剩下了威尔夏尔大街上历史悠久的柏油坑了,加州北部也会因为得天独厚而继续繁华的。
我们的第一轮巡演在盐湖城结束,这个被烈日下的热气包围着的城市,空荡荡的,像摩门教徒一样显得冷淡而沉默。那里的观众也给人同样的感觉。
我们在巡演过后回到纽约,打算直接回英国了。但由于威廉·莫里斯先生当时正和其他几个剧团抢生意,所以我们受邀在他纽约第四十二街的戏院里演出六个星期,上演我们所有的戏目,主打戏是《英国游艺场之夜》。观众对我们的演出大为赞叹。
有一晚,几个年轻人出来打发时间,不经意间走进了威廉·莫里斯的美国音乐厅,看见了我们的演出。他们当中一个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老板,我就要请那个演员演戏。”他指的是在戏里扮演酒鬼的我。这个说话的年轻人叫麦克·森纳特,当时是一个临时演员,每天能拿五美元,是后来奇斯顿影片公司的创始人。
我们这六个星期的演出空前卖座,于是再一次被沙利文和康斯汀轮回上演戏院邀去做巡演,为时二十个星期。
第二轮巡演快要结束,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就要回英国了。这难免让我心中抑郁。
我在离开旧金山前的那天,在街上漫步,偶然走进了一家看相算命的店铺。接待我的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胖女人。她嘴里还嚼着饭,像例行公事一般,看都不看我,就指着墙根的小桌子让我坐,然后自己坐在我对面,对我说:“请洗一下这些牌,对着我抽三次,然后把您的手摊到桌上。”她翻过牌,铺在桌上仔细地看了一会,接着看我的手。“您现在准备出远门,也就是要离开美国。但不久以后您还会回来干另一行,不同于您现在做的。”她说到这里有些迟疑,略显迷惑。“虽然有些不同,但又几乎是一样的。我看您干新的这行前途无量,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职业。”这时她才抬起头来看看我,拉起我另外一只手:“您要结三次婚,前两次不那么美满,但最后生活幸福,还有三个孩子。”(这个她可算错了)然后,她又一次仔细地看了我的手。“这可是一只发财的手啊,您将来会成为百万富翁的。”接着她又给我相了面,说道:“您将来会得支气管肺炎寿终,享年八十二岁。请交一元卦金吧。还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吗?”
我大笑起来:“没有。我还是不多麻烦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