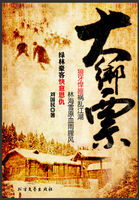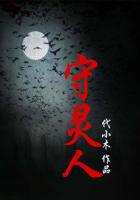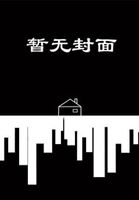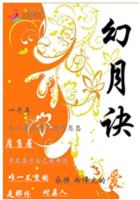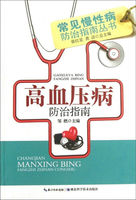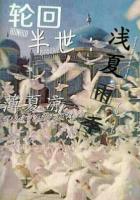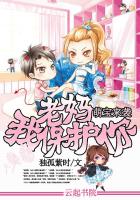梦庄的媳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语言不美。她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或是奶着孩子在树凉里休息的时候,不是谈论哪个男人拈花惹草,就是谈论哪个女人招蜂引蝶。更有甚者,竟然赤裸裸地褒贬自己丈夫身上的东西。她们的丈夫并不在意,她们的公公婆婆也不责怪她们。于淑兰的婆婆曾经笑呵呵地对我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年轻时,嘴更臊。这是我们村的风俗,老辈子的流传。如今,我老啦,淑兰成了我的接班人儿啦,哈哈哈哈……”
在梦庄,于淑兰是个引人注目的媳妇。从外表看,她和她的婆婆大不相同。她很年轻,很俊俏,也很文静。尤其是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仰起,眼睛望着天,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平时,她不爱说话,可是只要一开口,就是一颗“炸弹”。
她头一次和我说话,就是一颗“炸弹”。
那是一天上午,我和一群女社员在村南的麦地里撒化肥,想方便方便,就向远处的坯垛那里跑去。于淑兰尖着嗓子,忽然叫了一声:
“站住!”
我站住了。
“干什么去?”
我没理她。
“尿泡,是不?”
哄的一声,她们笑了。
“到底是城里的学生呀,真文明。”别人都笑,她不笑,一边干活一边说,“这里又没姑娘,净媳妇,我们什么没有见过?尿个泡,也值当跑那么远?想尿,掏出来就尿呗!”
麦地里,叽叽嘎嘎笑成一片,她们似乎得到了一种满足。
一个玩笑,一扫那种高不可攀的感觉。休息时,我凑近她说:
“你说话真粗。”
“可不是,我们吃的饭粗,说话也粗。”
“你们这样儿,男人不生气?”
“梦庄的男人都比女人老实。”
又是一片叽叽嘎嘎的笑声。
开始,我对这些女人曾经产生过一些猜疑。言为心声,莫非她们的作风下流?后来一了解,不是,她们冰清玉洁,品行端正,一个个都是好媳妇。
也许,梦庄的日子太枯燥了,她们喜欢谈论那些男女之事,就像我拉二胡,也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
我猜对了。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在屋里正拉二胡,听见窗外有一种奇怪的响声。那声音一阵比一阵的繁乱,一阵比一阵的稠密,像是雨点儿击打着各种不同的东西。我开门一看,只见院里站着八九个社员,有的打着雨伞,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头上顶了一个簸箕。他们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的窗口。雨水淋湿的脸上凝结着各式各样的笑容……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忙说;
“进来吧,进来吧。”
“不啦,不啦。”
他们讪笑着,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踩着泥水散去了。
于淑兰没有走,她像一个天真的姑娘,一蹦三跳地来到我的屋里。她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那把躺在炕上的二胡:
“这就叫胡胡儿?”
“叫胡琴。”
“我拿拿它,行吗?”
“行,拿吧。”
她小心地拿起那把二胡,在手里掂了掂,立刻又放下了,很怕“拿”坏似的。我看她十分稀罕这件东西,就说:
“你拿吧。”
“不拿了,你再拉一个吧?”
“你喜欢听什么?”
“‘天上布满星’吧?”
我又拉起来了。她侧身坐在炕沿上,眼睛盯着我的手指,听得十分认真。我拉完了,她好奇地看着我,就像刚才看二胡:
“你有这种手艺,怎么还到我们这个野地方来?”
“这不算什么手艺。”我说,“我们下来,锻炼来了。”
“多苦!”
“不苦。”
“多孤。”
“不孤。”
“你认了我吧?”
“认你什么?”
“干姐姐!”
我抬起头,望着她那一双亲切的眼睛,心里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在异乡,在举目无亲的异乡,一个年轻的女人,愿意和我亲近,我感到很温暖,很幸福。她虽然只是想做我的干姐,而不是别的。
我说行。
“那你叫我一声。”
“干姐姐。”
“不行,去了‘干’字。”
“姐姐。”
“哎。——弟弟。”
我干笑着,没有答应。
“答应呀!”
“哎。”
她高兴极了,以姐姐的身份,对我做了许多嘱咐。她说,村里的日子苦,干活悠着劲儿,要好好保护手指头;又说,衣服脏了,不要自己洗,拿给她。她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好好钻研拉胡胡儿,钻研出来有前途……
从此,在梦庄,我有了一个亲人。
她不是我的干姐,是亲姐。
那年秋天,我得了重感冒,她一天不知来几趟。她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服侍我吃饭、吃药、喝水。最使我难忘的是,每当乡亲们来看我的时候,她总是以亲属的身份表示感谢:
“唉,让你们结记他。”
一天晚上,她又来看我。她一见我,吃惊地叫了一声:
“哎呀,怎么脸肿啦?”
“牙疼。”我说。
“哪边的疼?”
“左边。”
“等着!”
她走了。不一会儿,拿来一颗“独头蒜”。她把蒜捣碎了,抹在我左边的脸蛋上。
“还疼吗?”
我疼得冒泪花儿。
“等着!”
她又走了。不一会儿,拿来几个花椒,让我咬住一个,咬紧。
“还疼吗?”
我疼得直哼哼。
“哎呀,别哼哼了,想想李玉和!”
我真的想了一下李玉和。
“怎么样?”
“不顶事。”
“那,我给你讲故事吧?”
我未加可否,继续哼哼着。
她坐在炕头上,给我讲起故事来。她没有什么好故事,不是哪个男人拈花惹草,就是哪个女人招蜂引蝶,有真事,也有演义。奇怪,听着她的故事,似乎减轻了一点病痛。
“好些吗?”
“好些。”
她高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最后一个故事最精彩,很像一个谜语。她说,从前有个媳妇,结婚三年了,不生育。有一天,姑嫂对话:“嫂子,你两口儿不呀?”“不不呀。”“不不怎么不呀?”“不不还不哩,要不更不啦。”她让我猜,其中的每一个“不”字,代表什么意思?
我努力猜着,牙,一点也不疼了。
一连几天,她和她的故事,伴着我战胜了疾病。
我能做饭了。
也能下地干活了。
晚上,我的小土屋里,又响起了二胡声。
一天,我们在青纱帐里掰玉米,我悄悄地对她说:
“姐姐,我猜着了。”
“猜着什么了?”
“猜着那几个‘不’字了。”
她一旺,两眼直直地望着我,好像不认识我。望了一会儿,突然说:
“我白****心了!”
她很生气,咔、咔地掰着玉米,向前走去。我赶上她说:
“姐姐,你怎么了?”
“你,小小的年纪,城里的学生,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你光用这种心思,怎么钻研拉胡胡儿?”
“那天晚上,不是你让我猜的吗?”
“那天晚上,你不是牙疼吗?”
从此,她和我疏远了,再也不到我的小土屋来了。
我几次约她,她总说没工夫。
我很孤独,陪伴我的只有二胡。
真没想到,那年冬天,在全县的文艺汇演中,我的二胡独奏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让我到文化馆当“合同工”去。在离开梦庄的前夕,干姐突然来了,我含着眼泪叫她:
“姐姐!”
“你几时走?”她问。
“明天。”我说。
她坐在炕沿上,我也坐在炕沿上。她侧着身望着我,我侧着身望着她。我们中间躺着那把很旧的二胡。沉默了很久,她噙着泪花儿笑了说:
“走吧,你到底拉出来了……”
为了保护我的手指头,她送给我一副驼色的毛线手套。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再没有见到她。
十几年中,按照她的嘱咐,我一直坚持拉二胡。
我拉二胡没有别的幻想,好像只是为了她的嘱咐。
我学会了不少曲子,但是每当拿起二胡,我总要先拉一拉那首过了时的“天上布满星”……
(梦庄记事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