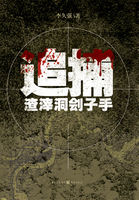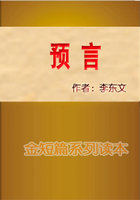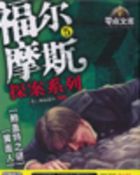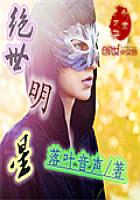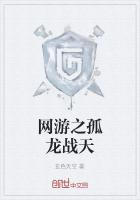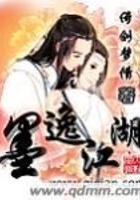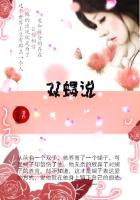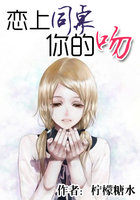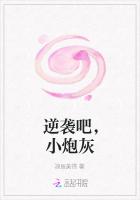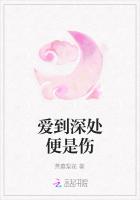我正摆弄着手机,掌中突然震颤,是手机的来电振动。我犹豫了一下,待再次振动的时候,我按下了接收键,果然正是手机的主人。“您是哪位?是火车上的旅客朋友吗?非常感谢您捡到了我的手机。拜托您将手机交给列车长好不好,我会想办法跟她们联系的。真是非常感谢您了,还是好人多啊。哦,还有,拜托替我把手机关闭,再一次谢谢了。”
真的是位很聪明的人啊,不关手机,不定又有多少秘密让人知道呢。
探视
一溜儿轿车引人注目地开进了市立医院。
新任********冯天顺钻出车门,看了看陪同自己来探视的副市长和卫生局长,心中暗暗好笑。自己本是来探视一位旧时的学友,却没想到带出这么一个检查团似的阵势,一会儿老同学见面不知要做怎样想,还以为我在摆谱扬威,他哪知当官有时远不如当一个普通小百姓自由自在。
冯天顺原在外地一个国营大厂当书记,没想这次调整市委班子,竟把他提到“州官”的位置上来了。到了市里,忙了一阵,蓦地想到该会会尚在这里当老师的大学同学李焕林。电话打到学校,方知李焕林正生病住院,不知副市长和卫生局长是怎么知的消息,是不是他们以为我要检查医院的工作?
过大厅,上楼梯,七拐八弯,进入内三病区,眼前骤显拥挤不堪,连走廊里都搭满了临时病床。冯天顺走在前面,他知道身后是按级别和职务的降幂排列。细琢磨一切都有些好笑,可似乎又只能如此。
“内三8号。”冯天顺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迎着身旁病床上一张又一张痛苦而又好奇的面孔,他尽量保持着自己的微笑并频频点头致意。不管人们认识不认识自己,微笑并不使自己损失什么,而且很快人们将知道这是********的微笑。眼下,自己所能给予人们的也许只有这些了。
蓦地,一张消瘦而衰弱的老太太的面庞在他的视框中定格。他愣了一下,急忙停住脚步。那蜷缩在病床上的老太太也似乎一下停住了喘,颤颤地问:“你……大顺子!”
“伯母,我是天顺!”冯天顺一下扑过去,抓住老人的手。
“大侄子,知道你……调市里来了,你忙,还来看看伯母……”老人抓着冯天顺的手,眼里闪着欣喜的泪光。
“伯母,我不知您在这儿住院,不然,早来了……”
“可不,也不想惊动你,可来十多天了,好不容易……才在走廊排上这张床……大荣妹子这才想起你……”
“大荣呢?”
“这些天,就全……累她了……上厕所给我倒便盆去了……”
一瞬间,身后的市长、局长、秘书们已纷纷围上前来,虽不便多插言,可也都极得体地插上一两句问候。从老太太刚才喊出的那一声“大顺子”,众人也多少料知这老人和冯书记的关系非比寻常。
老太太姓赵,当年冯家和赵家是仅隔一墙的邻居。冯家一居室人口多,少年时代的天顺便常到两居室的赵家去借宿。赵伯母中年丧夫,只有二女,对男孩格外疼惜,天顺住她家时,她便让两个女儿住一间小屋,而让天顺和自己睡在一炕上。天顺半夜醒来时,常发现伯母正不错眼珠地望着自己,似乎大半宿都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后来,爸爸妈妈被关进牛棚,弟弟妹妹们也都去了乡下,唯留天顺在家守营,赵伯母不让天顺开伙,连同送牛棚的一日三餐都由自己调理。再后来,便是,天顺考大学,爸爸妈妈也终于搬迁住进了新楼房,两家的来往便渐显疏淡了一位女士端着便盆走来,微笑中不无揶揄:“哟,没想冯书记大驾屈尊,还亲自来看看病老太太。”
冯天顺顿感脸上发烫,他忙站起身,说:“大荣,这可怪你。伯母生病,你就不会给我拨个电话吗?”年轻时就这样的,两人说话常带些挖苦和讥讽,倒显出些兄妹般的亲切。
“哼,还打电话呢!”赵荣将便盆塞到床下,“你那些大秘书横着呢,先问你是干什么的,啥事,然后不是说书记出差就是开会,好像你一离身,肯定天要塌似的。”
老太太说:“大荣,你天顺哥忙……”
冯天顺也说:“那你可以直接给我挂电话嘛。”
赵荣又撇嘴:“你的电话保密呀。还算不错,你那大秘书总算应下传话给你了。”
传话给我?冯天顺心底一动,扭头望了身后的秘书一眼,秘书红头胀脸的正抱着那一网袋食品不知往哪儿瞧。唉,他有意给我挡驾,虽说是好意,却险未陷我于不仁不义。看来,今儿也只好假戏真唱,就算是专程来探视伯母吧。
又谈了些别的。闻讯赶来的院长、科主任们也满面尴尬地挤到床前来,忙着给书记汇报老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冯天顺又询问、叮嘱几句什么,转身从秘书手里接过那袋食品,放在老人床头:“伯母,你老先养着,改日我再来看你。有什么困难,就让荣子直接打电话给我。”他又转向赵荣,笑着说:“谁要再敢挡驾,你先指名骂我,好不好?”
冯天顺告辞了,身后的人挨个向病恹恹的老太太殷勤致意,然后尾随而去。走廊里的患友们惊异这骨瘦如柴喘成一团的病老太太竟还有如此靠山,那投来的束束目光陡增了许多敬畏与羡慕。
当日晚,冯天顺突然想到李焕林一定会知道自己去医院的事,该如何和他解释呢?他想给医院挂个电话,却不想电话先叫来,里面是熟悉的火辣辣的声音:
“我是赵荣。我说书记大人,你快给医院下个命令好不好,请他们无沦如何不要给我们调病房了,我妈说这样挺好,住走廊虽说乱点可心里舒坦。”
冯天顺一惊:“怎么呢?”
“怎么呢!你没想想,病房里都是满满的,把谁换到走廊里不骂?骂的那话难听死了,骂医院,骂我们,也骂你。”
“骂我?骂我什么?”冯天顺又一惊。
“骂人的话我学不出口,你大书记还琢磨不出来?可医院还死活非得让换。有个好心的病友主动提出可以搬到走廊去,人们又骂他舔溜须,你说人家好心好意的冤不冤?”
“他是哪个病房的?”冯天顺似乎预感到什么。
“8号。”
“哦?!叫什么名字?”
“李焕林,是个老师。”
冯天顺不言了,好久好久,才沉重地说:“请跟李老师说,还是先不换吧。我看,明天,你们换个医院……再有,你跟李老师说,我问他好……”
同一首歌
三八节前夕,市里召开妇女工作会议,特意请省妇联主席光临。为表重视,市委首席领导高肃哲书记专程从南方学习考察现场飞了回来。按惯例,本来有一位副书记出席就可以了。
妇联同志的工作很细致,会议进行得也很顺利。会场安排得庄严肃穆而不失热烈,千余人的剧场座无虚席。红领巾献辞,工作报告,经验介绍,领导颁奖。进行曲,闪光灯,红花绶带,礼宾如仪。一切有条不紊地完成后,也就到了大会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时,领导讲话。先是省妇联,语重心长,纲目清楚;接着是********讲,高屋建瓴,统领全局。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圆满的大会。
功德的最后圆满当是会后的报道。电视台在当晚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里,用整整三分钟的时间报道了这次会议。第二天,市报也用头版头条配照片报道了会议消息,全文发表了********高肃哲同志的重要讲话。省妇联主席的讲话则是隔了一天发表的,也是头版显着位置。新闻要讲规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将市委主要领导的讲话排在前面,天经地义。
时间过了半月。忽一日,高肃哲的小孙孙问:“爷爷,您在大会上讲话,为什么要跟省里的领导讲的一个样?”
小孙孙六岁了,正读学前班,聪明得让人恨不得抱住他咬一口,他的最大爱好是喜欢拿着报纸给别人磕磕绊绊地念。高肃哲拍着小孙孙的脑袋说:“瞎说,爷爷还没老糊涂,怎能学八哥,跟别人讲一样的话呢?”
小孙孙从背后拿出了两张报纸:“我才没瞎说,您自己看,是不是一样?”
小孙孙拿的就是报道市妇女大会的两张报纸,一张登着********的讲话,另一张是省妇联主席的讲话。高肃哲接过两张报纸比较着看了,心里顿时狠狠吃了一惊。岂不真是一样,要说小有不同,也是自己在讲话前勾改的几个地方,就好像两个孪生姊妹站在面前,不同的仅仅是她们的服饰。高肃哲掩饰着恼怒,给小孙孙的解释是,“一定是报社印错了。这两张报纸给爷爷,明天我去批评他们。”
第二天,高肃哲一上班就吩咐秘书马上将报纸给报社总编送去,他在报纸天头处纵笔批示:“如此游戏,请给解释。”
市委主要领导的这种批示,已是再严厉不过的批评,那“游戏”二字足有万钧之重,登时就把报社总编脑门上的汗珠子压了下来。他匆匆看过报纸,急急找来总编室主任,又慌慌地将前几日负责采访的记者叫来,几番问过答过,再望定那两张惹祸的报纸,竟是张飞瞅绿豆,大眼瞪小眼,呆呆地再说不出话来。
总编没有主动去向高肃哲解释,他希望********能把这件事忘掉。但一周后,高书记亲自给他打了电话,那口气仍是不容商量的冷硬,“你不是想让我去你的办公室听解释吧?”
总编忐忑地走进高肃哲办公室,将两份讲话稿呈放在********的案头,并字斟句酌地做了如下说明:“这是您和省妇联领导的讲话稿原件。我们已做过深一步的了解,您的讲话稿是由市妇联秘书准备的,妇联领导的讲话则是由秘书准备的。问题的症结出在两位秘书,她们竟在网上鬼使神差地下载了同一篇文章,彼此又缺乏必要的沟通。现在网上这样的文章很多,点击率也很高,各级领导在不同会议上的讲话都有现成的样板,秘书们图省心,便常走了捷径。当然,我们报社的编辑和审校人员也有责任,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在此,我特向领导表示深刻反省与检讨。”
像突然坠入隆冬的冰窟,彻骨的寒意漫透全身,又向心底逼袭。高肃哲哑了嘴巴,他万没料到谜底抖开,给人的会是这样一种尴尬。如此说来,那会场上千人对领导的讲话竟都是充耳未闻?数以万计的市委机关报的读者们也都对领导的讲话视而未见?那天省妇联领导讲话在前,端坐在主席台上的自己又在干什么?而尤为可叹的是,用一根小竹签扎爆了如此庞大气球的竟是一个六岁的稚童,这不会是一篇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吧?
高肃哲向总编伸出了手,苦苦一笑:“谢谢你的批评。”
“高书记,我……”总编不知如何作答。
高肃哲紧紧握住总编的手,说:“这件事,还请所有知情的同志暂时为我遮丑。我要反思,也要检讨,但要给我时间,也给我机会吧。”
送走总编,高肃哲叫来了秘书,指示出文集的事立即叫停。再过几月,高肃哲就要退休了,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们早就张罗着为他出一本论文集,其中收集的多是他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秘书不知缘由,还想阻止,说印刷厂发排就绪,只等开机付印了。高肃哲坚决地摆手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抄来抄去没提高。赶快拉闸吧,没人喜欢再听那同一首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