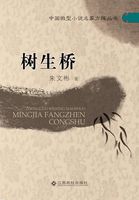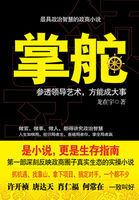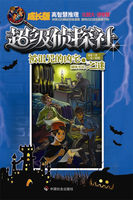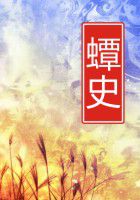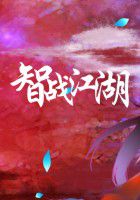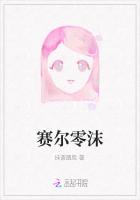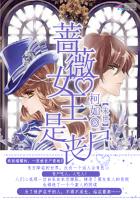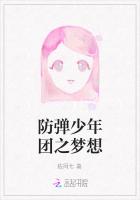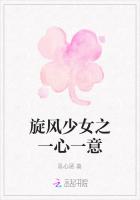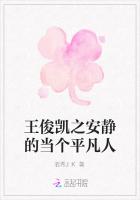物的形象
这里的“物”是指故事中的动物,如蛇、鳖、狐、狼、猪等。这些物都是贯穿整个故事的形象,
这些形象具有三个共同构成要素(或者说特点):一是着染自然界的神秘色彩,二是作为“老人形象”的精神寄托或心灵皈依,三是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1着染大自然的神秘色彩。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宇宙(或称世界、大自然)现象的了解越来越多、对本质的理解也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越来越”相对于无限的宇宙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有限时空中的人直观无限的宇宙秘密时必然产生认识的局限和心理感受”,从而产生了神秘色彩,“具体表现为先民对气象万千、威力无比的大自然的无限敬畏与崇拜”。
在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生存规则和生存欲望下,许许多多的动物的举动通常是它们的一种趋利避害、力求生存的表现,可谓正常现象,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但是在这些正常现象之外,在人类的限知领域里,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动物的不同寻常的行为是难以或者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至少是目前的科学水平),于是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为就着染上了自然界的神秘色彩。这正如陈赟认为的那样:“世界的不可测度性表明世界本身所具有的神奇的、神秘性的特征。”阅读孙春平“老人系列”的人随时有可能被这种表现在动物身上所着染的自然界的神秘色彩所纠缠住,似乎回到了《聊斋志异》所描绘的精灵世界。先看看《老人与蛇》中的蛇是如何具有神秘色彩的:
“徐老顺大喊一声“嗨”,那蛇好像中了定身法,立刻停在那里不动了。徐老顺走上前,让人难以置信的神奇一幕出现了:只见他把手伸出去,那蛇便乖乖地爬到他掌上,盘成一砣再不动。”
“静卧草中,几条蛇在他身上温顺地盘卧……”
“通体银亮……只要我一进那片滩,它就簌簌地跟在后面。我躺下,它就盘到我脖上来。”
“最先登到楼顶的人曾看到徐老顺的胸口盘了一条白白亮亮的小蛇,见人们近前,便呲溜一下逃走了。”
这里,蛇不仅能够听懂徐老顺的人类语言,而且还能理解他的思想;不仅在外形上的世间罕有,而且行为上也极端不可思议;不仅难以想像地咬死徐老顺,而且会辨别陌生和熟悉。这一切都是那么让人费解的,难以想象,难以和科学对号入座。而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蛇”身上体现出来的矛盾:当徐老顺与蛇和谐相处、爱蛇、护蛇的时候蛇对他天生惧畏,而当徐老顺被迫砍蛇的时候蛇又把他咬死。这真是蛇对徐老顺的报复吗?如果是,那么“棺木缓缓落入墓穴那一刻,众人眼见有一条白亮小蛇从脚下草丛里窜出,眨眼间便钻到棺木下不见了踪影”的陪葬式行为又应该如何作解释?无疑,这一切都是不认人所知(至少是目前不为人所知)的神秘在发挥作用。
与《老人与蛇》有所不同的是,在《老人与鳖》、《老人与狐》以及《老人与狼》和《老人与猪》中作者对动物身上这种神秘色彩不仅使用了正面的描述,而且还通过了间接的渲染来印证。正面描述如:
鳖不仅“足有脸盆大小,青幽幽的鳖盖上泛着暗绿的光”,而且鳖能够“贴着一角,大大小小的鳖们竟叠垒起一个塔形鳖堆”并以假象来掩护野生老鳖的逃亡。(《老人与鳖》)
白狐竟然会“用三只野鸡两只山兔。这是想讨好德四爷呢”和“乞求德四爷放掉它的孩子”,并而洞悉了德四爷的想法而通过“突然正对着房门的方向,伏下了身子,两只前爪平伸着,脑袋就伏在那两爪间”来引颈受戮;在面临生死抉择时白狐只是“身子微微抖颤了一下,却仍不躲也不动,只是把眼皮轻轻地合上了”来等待德四爷的棍棒;当德四爷放小白狐的时候“白狐跳到院门口时,又转了几个圈子,然后立起身,合起两只前爪对作了个揖,便驮着小狐钻进夜色中去了”。(《老人与鳖》)
大灰不仅在佟二爷送它上山的时候“似乎听懂了佟二爷的话,伸出舌头在佟二爷掌心里舔”,而且还会“捕到野鸡山兔舍不得吃,送回家来报恩”;甚至领会佟二爷的招手而“溜碎步跑进来,硕大的脑袋往佟二爷怀里扎,长长的舌头又在佟二爷粗大的掌心里舔”。(《老人与狼》)
老八有着“野猪的种,家猪的胎,吃狗奶长大”的身世,又表现出“不合群,不与同类亲近”的习性;既“有野猪的敏捷与凶猛,有狗的忠诚与驯服,当只和老太在一起的时候,又像家猪一样温和与依赖”的独特个性,又有“红了眼睛的老八壮烈地嘶吼了一声,又向开枪者扑去”的正义。(《老人与猪》)
上面的正面描述和我们的现实经历是多么的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会被认为是玩笑、是天荒夜谭,因而它需要一种印证,于是间接的渲染就应运而生。如:
鳖爷“你们太狠啦,要绝根啊,老天报应啊!”的放声哭诉和“怔怔神,不哭了,突然伏在地上磕头,磕得地皮咚咚响,眼看那额上就青紫了,红肿了,浸出殷殷血丝”的表现,以及“此乃天意,老天有眼啊”的倒背着手仰面大笑。(《老人与鳖》)
珍贵的白狐突然出现多年没有来连“跟土疙瘩差不多颜色的土狐狸都难见”的大山。(《老人与狐》)
“塌山了,一窝狼都滚坡砸死了”而大灰却奇迹般毫发无损。(《老人与狼》)
“就在最后的这只老八即将丧命的时候,袁老太来了”的似巧合又似是传奇的经历。(《老人与猪》)
这样的间接描述(渲染)同样是让人费解的或是纯属巧合的,而这种让人费解恰恰和纯属巧合能够和上面的正面描述相互印证,构成神秘的极合理解释,从而使鳖(狐)身上体现出来的神秘色彩更加丰满鲜活、更具说服力,进而更加使神秘具有不可测度性。
作为同一系列的这种正面描述和间接印证的方法在《老人与狼》和中,狼(大灰)也具有这种神秘的色彩。大灰不仅在佟二爷送它上山的时候“似乎听懂了佟二爷的话,伸出舌头在佟二爷掌心里舔”,而且还会“捕到野鸡山兔舍不得吃,送回家来报恩”,甚至领会佟二爷的招手而“溜碎步跑进来,硕大的脑袋往佟二爷怀里扎,长长的舌头又在佟二爷粗大的掌心里舔”。这些都是人的性格和行为,体现出不同寻常的神秘色彩。
《老人与猪》中,老八(猪名)这种神秘色彩既表现在它临死获救的似巧合又似是传奇的经历和“野猪的种,家猪的胎,吃狗奶长大”的身世,又表现“不合群,不与同类亲近”的习性上;既表现在它“有野猪的敏捷与凶猛,有狗的忠诚与驯服,当只和老太在一起的时候,又像家猪一样温和与依赖”的独特个性,还体现它“红了眼睛的老八壮烈地嘶吼了一声,又向开枪者扑去”的正义上。特别是老八对歹徒斗争的英勇,活脱像一个正气凛然的大侠,而这对于一头猪来说只能用自然界的神秘去解释和理解了。
综观“老人系列”的“物的形象”都具有着自然界的神秘色彩,尽管这种自然界的神秘色彩在各自的体现上是有着细微差别的(蛇和鳖身上体现出来的神秘色彩更多接近于“自然性”,而狐、狼和猪更多的接近于人的性格和行为),但是不管是“自然性”还是“人性”,当它们在动物身上出现的时候,它的“不可测度性”都使之归属于自然界的神秘色彩。
在以上例子中,无论是蛇、鳖、狐,还是狼、猪,都仿佛真的有那么一种不为人类所知晓的神秘力量蕴含在动物的身上,仿佛有“神”在驱动着动物的一举一动;但是这样的“神秘力量”和“神”绝不是迷信意义上的万能的“神”。首先,作者是一个现实主义现代作家,自然不是迷信之流。再次,“神秘力量”和“神”的真正指向还是陈赟所说的“不可测度性”。《周易》说过“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和“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周易·说卦》)。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是指阴柔与阳刚无法使人预测叫做神秘(神奇),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的意思是神(秘)就是万物的奇妙无比。所以,孙春平笔下的动物的神秘色彩不是有神论的夸张渲染,而是“蕴藏与万物之中的生机,是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奇妙莫测的生命本身及其过程”。
2心灵皈依和精神寄托。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现代社会心理正处于一种浮躁和盲目的状态:物质欲望日益膨胀而精神价值不断消解,物质欲望逐渐取代精神价值在人的审美情感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世俗化、功利化及物化浪潮的驱动下,精神价值的失范和消解成为一种必然”,而这种精神价值的失范和消解对人直接的影响是使人丧失精神寄托和心灵皈依,这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还有一些人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时,没有失去自己灵魂的重心,他们仍然追求心灵皈依、保持着自己的精神寄托。“老人系列”中的老人便是这些人的代表,且看《老人与蛇》:
“我又问,就为抓三条蛇,不过你老抽袋烟的工夫,怎么一走就是一天?
徐老顺说,我顺河套遛达,累了,找处荫凉躺下歇,找来几条粗大些的长虫,让它们趴在我身上,那东西把凉啊,三伏天在这心口窝一盘,啧,那美劲,甭说啦!”
这文中“我”与徐老顺的对话。在这里,作者通过徐老顺和“我”的对话,将老人“志趣”完全展示出来:与蛇(自然物)没有尔虞我诈利害关系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是老人心灵追求的皈依。其实徐老顺三岁的时候便和蛇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情结,而这种情结实际象征了徐老顺的童年的纯真天性。所以徐老顺的心灵追求实际上是对童真对纯真天性的皈依。作为一个老人,虽然有儿子徐军相伴,但儿子徐军更多的是看重老人捕蛇的技巧,也就是把老人当作一种财富来源,而未能真正懂得老人的精神世界(从他把徐老顺要冒着生命危险与其弃蛇行为进行抗争认为是赌气这一细节可以洞悉)。“我是轰不动大牲口啦,又不想白吃白喝看他们的白眼,要不,哼,就这三条,他也休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儿子徐军对赡养实际上是对徐老顺经济上的“施压”。所以,作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不愿意在家里享受温馨“一走就是一天”,因为他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一种心灵的皈依。
同是一种心灵的皈依,《老人与鳖》中的鳖爷的心灵皈依更偏重于向信仰的皈依。鳖爷“八十来岁了,无儿无女,老伴也早过世,自己孤苦地过日子”,是鳖养活了他,因此他感恩于鳖的恩赐(“你们太狠啦,要绝根啊”),他深信鳖的灵性(“此乃天意,老天有眼啊!”);自然而然,在鳖爷的信仰里鳖已经是“鳖神”了。具体地说来,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鳖爷只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去抓鳖“家里有病人需大补,大夫开出方子啦”,而决不为乡长为巴结县长的丑行而抓鳖,体现出对自己信仰高洁本质和尊严的维护。
再次,为了极力反对和阻止乡长的竭泽而渔的勾当,甚至喊出了“我、我不活了!”的反抗绝吼,可想是一种对自己信仰的抗争和扞卫。
第三,当鳖爷阻止不了乡长抓鳖的勾当后,便“瘫坐在地上放声哭起来,‘你们太狠啦,要绝根啊,老天报应啊!’”,这是对破坏自己信仰的咒骂。
第四,当他心中的“鳖神”被抓以后,“鳖爷怔怔神,不哭了,突然伏在地上磕头,磕得地皮咚咚响,眼看那额上就青紫了,红肿了,浸出殷殷血丝”,这既是对自己信仰的膜拜,又是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向信仰表示惭愧和忏悔。
第五,为了营救“鳖神”鳖爷先是再抓了“两只个头也不算小的老鳖”送给养鳖场场长并不要任何报酬,然后利用场长的过意不去和骄傲无知来调虎离山“你把场里的人都叫上”,整个计划是鳖爷苦心孤旨的过程,体现出鳖爷对自身信仰执着和拯救。
最后,当“鳖神”获救以后,他“倒背着手仰面大笑:此乃天意,老天有眼啊!”的细节更是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对信仰从获新生的热烈拥戴。
与上面两例有细微不同的是,《老人与狐》的心灵皈依是一种情感的交融和相通。文中的德四爷虽然还有老伴的健在,但是他的儿子却被滚石砸死了,所以德四爷夫妇对儿子的那份心灵是空虚而渴望的。在和白狐的一番恩恩怨怨以后,德四爷夫妇和儿子的情结已经和白狐的母子情结交融在一起--“天地之间,******,都是血肉之躯,同情同理”,白狐的行为给了他情感的共鸣。白狐的护子情深实际上是德四爷夫妇的护子的情深--“他想起儿子刚死时,老两口悲恸欲绝的情景,老伴儿叨念足有上万遍:老天爷,让我死了吧,只求换回我的儿子”。白狐的母子团圆实质上是德四爷夫妇对儿子的深切怀念和父母与儿子情缘的再续,以及德四爷夫妇希望儿子能够奇迹地死而复生。“白狐得到了生命,德四爷得到了解脱”。
而在文章的最后,“多少钱值这一片心啊!”则更加有力地将人与物的情感、遭遇高度集中统一起来,达到情感的相融相通。实际上德四爷“睡得格外香甜”是对德四爷的解脱、****情感相融相通的点明,也就是对德四爷这种心灵的皈依的点明。这正如程习武先生点评的那样:“人与狐最后的心灵的交融,让人与狐都得到了一次崭新的升华。”
以上三例,不管是对童真的皈依,还是对信仰的皈依,还是情感的皈依,都是一种发乎心灵深处指向心灵深处的皈依,而蛇、鳖、狐是这一种皈依的载体。
与蛇、鳖、狐所承载的心灵皈依一脉相承,《老人与狼》和《老人与猪》中狼和猪承载的是老人的精神寄托。《老人与狼》中,佟二爷虽然有佟二奶为伴,但是浓厚的传统意识让佟二爷因为没有儿女而精神缺少寄托。(这从佟二奶“一辈子没生养,所以总觉欠着什么,逆来顺受的,惯了”的表现可以得到佐证。)
在佟二奶反对的时候,佟二爷说“可见这东西也讲仁义”,可以体现出佟二爷对“仁义”(特别是对后代的仁义,父母很忌讳儿女不仁义)的寄托。
当知道是大灰反哺报恩的时候,佟二爷“大灰回家来啦!大灰捕到野鸡山兔舍不得吃,送回家来报恩啦!疯了一样往屋里跑,嘶声地喊,是大灰孝敬的我,是大灰呀!”这些孩子一般的狂喜表现,可以知道佟二爷已经把大灰当作自己的“儿女”,把大灰的报恩当作是儿女的赡养。
另外,当记者来采访的时候“兴高采烈,满面放光”和对记者“你那照相机贼光一闪,别说大灰,连我都吓一跳。狼最怕光你知道不?”的拒绝可以反映出佟二爷对精神寄托的欣喜和维护。
至于佟二奶被大灰的报恩感动得“昏花的老眼也湿润了,喃喃地说,这孩子……这孩子呀……”,以及当大灰被伤害之后“佟二爷大病了一场……病好后去山林里转了好多日子……一下苍老了许多”更是生动深刻地反应出老人精神寄托得以满足时的欣慰和失去精神寄托时的颓废。这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动物是人类的一面镜子,动物的行为将激起人类心灵的共鸣、震颤和反省,使他们由兽性想到人性。”
《老人与猪》中,袁老太是“孤苦零丁的一个人,中年丧夫,两个女儿也先后嫁出了大山”,一个这样的老人同样渴望儿女的相伴。这从熟悉、了解袁老太生活起居的邻居的话语中得到佐证:“候在院门外的孩子父母闻言,立刻齐齐跪倒,大哭求告,袁奶奶呀,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你的亲儿子,我们给你养老送终啊!”由此可见,老八其实是袁老太关于儿女的一种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