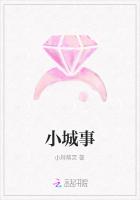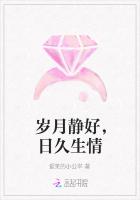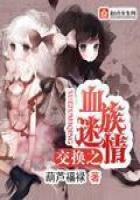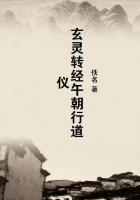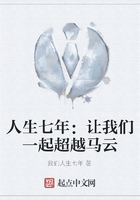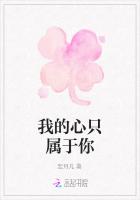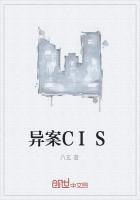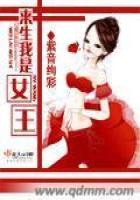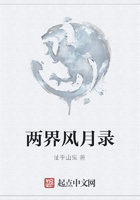老爷在家停放的第七天上午十一点,棺木必需要离开家,这是端功先生高老爷看的期辰与时候,这意味着老爷要被抬去埋葬,从此离开这个家。
第六天傍晚来家里下祭、送礼金、送花圈的亲朋好友,还有周围团转的邻居们,实实在在把二丫家热闹了一翻。这自然要招待大伙吃上一顿,明天送老爷上山后,还有一顿。
二丫从未看见过家里,有如此“山潮、水潮,不如人潮”的热闹。看着这样的热闹,说明老爷平时如奶奶讲的那样,做人厚道,死时才来那么多人凑他的热闹,不然生前再是达官显贵,死时连鬼都没一个。
老爷要是能看见这些多好?证明他活着的时候,平身没做过什么大事,但一直用真情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才让他的厚道收获如此平凡的人气。
终于摆桌子待客了,待客的桌子,就摆在围绕二丫家左右周围的邻居的家里,每家腾出来的位置只能摆两张八仙桌,这样的酒度差不多摆去了半条街的位置,让中山路面街的公房有三分之二的人家户也跟着热闹起来,忙得二丫当总管的那位堂伯,吃饭时双手围在嘴边当喇叭,一下朝上、一下朝下,大声对街喊到,生怕来的客人没有听到,错过坐酒席的机会:“各位亲朋好友,我替主人家,请各位入席,准备上菜啦!”
听到这一声后,三五成群站街边吹牛摆壳子的人,在安排就坐的引导人的帮助下,各自组伴入位。大人声、孩童的嘻哈声、婴孩的哭泣声,全渗混在这热腾腾的气氛中,简直要把这公房的屋顶给掀翻了。
小城像老爷这种人的很多,每家办这样的事,都很热闹,就像办一次盛大的亲朋好友的聚会,借着这样的机会,把平时因忙于工作;忙于生计的人们又聚拢在一起,联络联络彼此间的感情,既使办这样的酒席让主人家非常劳累,可主人家些还是乐此不疲,一家又一家还是照办不误。
在一个办这样的酒席,还能让陌生的、熟络的各种人,借酒席上的酒助人兴,三杯酒一下肚,你一言我一语就开始划起拳来“哥俩好啊,亏就亏啊…”
不一会全打成一片,陌生的也成熟人,熟悉的更是熟悉。
在二丫家帮忙,更少不了杨阿姨。
帮忙难免会弄脏衣裤,有的人便会故意穿脏衣服来,可杨阿姨还是穿得那样的得体又干净,站在那帮负责站桌抬菜、添饭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中间,显得她的拽气依然咄咄逼人,可她性格活跃的一面,又把这拽气中和,不然难与她们相处得愉快。加上她又是单身,所以抬菜上桌的青壮年男人们,个个争先恐后地围上前去与她打情骂俏,她风趣又不失娇媚的语言惹得这些男人,一个二个也不是省油的灯,照样以风趣挑逗的语言来以牙还牙。这个男人说:“你看我跟你家仙咡当爸爸怎么样?”
那个男人又说:“干脆办完孟大伯的事,将就这些东西,我们俩把结婚的酒席也办了。”
“是啊!将大伙的热闹继续,将大伙的热闹进行到底,何乐而不为呢?”又是一阵阵骂俏声。
“去你的,大白天痴人说梦话,想得美。”说完杨阿姨一下打这个一拳头,一下又飞脚去踢那一下。
说归说,笑归笑,不经意间杨阿姨瞄见到龚华新,那不是冯婉莹的男人吗?杨阿姨像换个人似,立马止住笑声,边朝龚华新走去;边又说了一句:“你们慢慢做你们的黄梁美梦去,我见到一个老熟人,过去打声招呼都。”
说实在杨阿姨还是关心冯婉莹,她跟妈妈、王伯娘一样,由先前的不满,到最后同情她,再到最后希望她有好的归属。
冯婉莹结婚后,再没进城过,不知是她恨这伤心地还是怎的?对她是从陌生到熟悉,再由熟悉到陌生,就因为是熟悉后的陌生,好奇不得不让杨阿姨产生。
冯婉莹在乡下过得怎样?能适应乡下的生活环境吗?做得惯农活吗?…………突然冒出这么多的问,也把杨阿姨吓一跳,为什么要这样问?她现在的结局不是满好的吗?也许同是女人,都希望彼此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属,自己不也正朝这方向努力寻找吗?可另一面,她还是替冯婉莹惋惜,这么标致的美人,怎么去配这样条件的男人?明摆着的鲜花插在牛糞上吗?唉!以她的思想,以她的眼光,就是不协调,太不般配,真不知道这月老是怎么搭搞的?
杨阿姨怀揣着一肚子对冯婉莹婚姻的不满意,带着对冯婉莹婚姻很难说清的那种忧杞人忧天的疑问,隔着人便跟他,打起招呼来:“唉!你也来了”。
“孟大伯的事,怎能不能来?”望着龚华新一脸漫不经心的淡淡表情,自认他们的婚姻是将就搭配过日子,对这样不看好的婚姻,俩人能过得好吗?可俩人结了婚,日子毕竟是俩人在过,我也没理由去对俩人再评头论足,杨阿姨想到这,终于让自己轻松起来。可面对龚华新,俩人没有相处过,礼节性地打过招呼后,竟语塞似地找不到谈话的主题,让俩人都有点尴尬。可杨阿姨太想从龚华新嘴里知道冯婉莹的近况,可又不好直接问他,竟让口齿一贯伶俐的她如卡带一样结巴起来:“能来就好,啊…那个…那个。”一脸不惑的龚华新看着她那怪怪的表情,一脸的迷惑不解,心一慌竟让他的脸红起来,整个人便促促不安起来。
看着龚华新的促促不安,见过世面的杨阿姨突然想起了彬彬,对孩子啊!想也没想嘴里就冒出这样的一句:“彬彬还好吗?”
谈起彬彬,龚华新一脸竟是幸福的味道,话多了起来,听他这样说,他对彬彬应该好:“彬彬啊!可听话,可懂事了,跟我俩个儿子相处得还算好,三个经常约着上山捣鸟窝,不时会跟着大儿子去割割草,帮我喂喂马,只是很不愿多说话,一看他妈妈不在家,就会很着急地四处找。”
“那冯婉莹还好吗?”杨阿姨终于问出这句。
提到冯婉莹,龚华新的脸沉了下来,眼望着远处的那凤翅山,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慢开了腔:“唉!就是话太少,整天只知道做事。”
“你别怪她,只有等她适应了,会好的。”杨阿姨嘴上这样说,心理却这样:话不少才怪,结婚的条件,反差那样大,还嫌她话少,你就知足吧!
看着龚华新点了点头,杨阿姨又说了起来:“多理解一下,多关心一下,人心都是肉长的,再冰凉的石头也会捂热。”
“我会。”听了杨阿姨的话,这时的龚华新只会点头应着,就不再出声,看得出他非常喜欢冯婉莹,他愿用时间来包容她、守候她、与她一起白头到老。
“唉哟!我得帮坐酒席的人添饭去,你去忙你的去吧!。”这时酒席快摆到尾声,杨阿姨这才想到她帮忙的任务,便对龚华新说了一句,就转身走开。
已吃完饭的人陆陆续续离开桌子,陆陆续续被收拾下来的脏碗筷,堆满在二丫家里的那只大白铁皮盆子里,只见王伯娘、么妹的妈妈,还有两个大娘,快速地在盆里洗着碗,又快速地在旁边的另一只大白铁皮盆里清涮着碗。
负责扫地的通鼻子更是忙不过来,只见她提着扫帚,这家急忙扫完,又慌忙那一家,因摆酒席的战线太长,她便把小老七利用上,叫他带揪上几个大点的孩童,去负责几家。
热闹终于转移了二丫对老爷突然离去的不适应,她也加入帮忙的队伍,与幺妹、还有发珍一起,专门抬垃圾倒去桥头边。
在这热闹中,最累的是做厨的师傅们,他们为今天傍晚与明天中午摆的酒席,已经忙了两三天。
除了自己家这样,平时的二丫很喜欢与奶奶去吃酒席,因为酒席上做的菜,全是具有小城特色的地方菜,统称为“水八碗”。
这时,又听见总管发话:“酒席摆得差不多,今天大伙辛苦了,我替主人家谢谢你们,接下来轮到我们帮忙人吃饭,吃完饭,大家收拾好桌子,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点来,好不好!”
“好。”大伙齐声应到。
这时有人约总管上桌:“总管,我们一桌,将就干上一杯。”
二丫、幺妹、仙咡、发珍、小老七与另外五个孩童不约成一桌。饭吃到最后时,小老七不知从哪拿来大半瓶子酒,接着又端来几个土丕二碗,并在每个碗里倒上小半碗的酒,然后叫了起来:“来,我们也干一碗,不干的是猪。”
二丫不愿当猪,立马伸手过去端起了一碗,就放在嘴边敏了一下,这酒真不是好吃的东西,酒味呛鼻不说,还有一股辣辣的味道刺激着她的口腔,让她不舒服地打了一个冷颤,只好把它给放回到桌子上。
那知幺妹也端了一碗,楞头楞脑地就把它给喝了下去,不一会她告诉二丫:“二丫,我头有点晕,看不清楚你们,我想回家了。”
说完就从二丫身旁起身。没走两步,二丫发现她歪歪叽叽,高一脚低一脚朝门外走去,哪知人还没走到门槛边,便一下栽倒在地上,涨着通红的小脸,不断大声地喘着粗气。这下把旁边一桌的幺妹妈妈吓着,急忙走过去一把把幺妹从地上揽到怀里,急切地连连问了起来:“幺儿,幺儿你怎么了?怎么满嘴酒气,谁叫你喝的酒。”
“是小老七,他说不喝的是猪,幺妹就把它给喝了。”与二丫在一桌的孩童嚷着回答了幺妹的妈妈。
幺妹的妈妈立马被这话激怒了起来,一个转身就把矛头指向小老七,什么也不顾就开始骂了起来:“你是有娘养,无娘教,这么大一点的绝种呔呔,竟做一些缺心、缺肺、缺**的事。”
“你这种是在说谁?谁有娘养,无娘教,你才样样.”与幺妹妈妈在一桌吃饭的王伯娘,当然不能接受骂孩子,会用这样的语言,本能也让她火冒三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