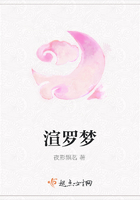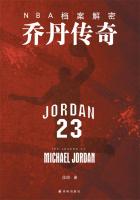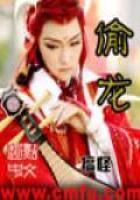二丫家的楼梯下,依墙码着一堆半腰高的煤炭,奶奶把大坨的堆码在外,小坨、碎屑的放在里,并把砸煤坨的榔头也放在煤堆上,方便把大煤坨砸小,好捡去添炉火。
煤堆旁朝门外的那方又堆了一小堆拌稀煤用的泥巴,泥巴平整处上靠里竖墙跟放的是一把方形圆角底,口内卷的竹编筛框,这是家里专门用来筛炭灰的筛子。它的旁边靠外放了家里的挑水木桶。
小城每家都必备这样的筛子,因烧煤炭火,炉子是小城特有特点的敞口、肚鼓、腿脚细的圆喇叭状的大煤炉子。往往添进去的煤炭燃烧不完全,烧过的炭灰用用这种筛子,把灰与颗粒分离开,让没完全燃烧的炭二次利用,这也算是节约能源。
框下筛出的细粒过炭煤灰,也不能白白丢弃,它是很好的天然建筑材料,用它加一定比例的石灰粉拌成浆灰,可以用来抹墙、抹地、砌墙,二丫家楼上的地板就是用这种浆灰抹的。
清晨,中山路的那边桥头与这边桥头的沟壑边边,全是倒粉色过炭灰的垃圾场地,来一个人,就是一撮箕的倒下去,灰尘如一团粉色气流,瞬间四处张扬、散漫、飘荡,再加上有人在旁筛过炭灰,扬起的灰尘,更是散了一团,又来一团,对于路过的二丫,只能快速逃离这灰尘埃埃的雾茫之地。
小城的气候环境多数在阴天、雾气、湿气、绵雨中渡过,街道自然是稀稀垮垮的泥泞地,加上这过炭灰的忐忑张扬,所以在二丫眼里小城有这些,自然不清爽。
每当过炭灰堆到一定的程度,总有一个包打着黑色头帕的伛偻老太婆,一身衣裤与过膝的围腰,又脏又破破烂烂,特别那围腰中部的补丁,补了一层又摞上一层,斑斑驳驳跟地图似。
看这老太婆的头,虽打着黑色头帕,可头帕包不住她乱如杂草的灰白色的头发,凌凌乱乱跟鸡窝似地遮掩着她的整张脸,让人看不清她的长像。只见她露在外的是她皱皱的脖颈、僵皱的双手又脏又黑,十个粗糙开裂的手指关节还肿胀变形,不得不让二丫眼里满是唏嘘的可怜,她只是一个旁观者,注意不注意永远不知道炭尘中的老人有多少辛酸事?有多少的沧桑事?
每到筛灰,她总穿一双糊满泥灰的黑色雨鞋,兀着双脚站好,把一条两脚向外撇的长条凳凳面向着自己竖起来,并在竖起的凳脚上摆一把筛框,放稳后才缓笨着身体把旁边堆起的过炭灰,用铲锄铲进撮箕里,再吃力地抬来,倒在凳脚上的筛框里,只见她一只手抓住竖立的凳头,另一只手扶好筛框的卷口,慢慢地崴着地面的凳头,一前一后平静地摇晃起来,那专一的神态,不受周围人与事的影响,好似只有她一个人存在。
没过几天,堆满两桥头的过炭灰,就被她用这种简易的方法,一筛框,一筛框地把它们又筛了一道。
来桥头边倒灰的人,倒了灰,筛了灰转身提脚离开,从不与老太婆讲话,老太婆筛自己的灰也不与倒灰的人打招呼。
老太婆筛灰的第二天,准会来一个里穿蓝四开袋外衣,外挂前门襟有许多盘扣的深蓝色坎卦的中年男人,驾着一辆带竹围栏的马车,在以后的天数里,不定时候,把老太婆筛下的过炭灰,一天拉一车拉走,直到老太婆筛完,他也就拉完。
筛过炭灰剩下的垃圾,最后被老太婆团围一堆,用火柴点了烧了,两桥头自然又清爽,不在有堆积的垃圾和遍地的炭灰。
每次她来筛灰,中山路公房的人都知道她存在那,可谁也不知道她从哪来?住哪?中年男人把过炭灰拉去哪?
后来二丫听说老太婆是麻疯病人,中年男人是她的儿子,从末结过婚,难怪人们不搭理她,她也不搭理人。麻疯病是传染病,小城把所有麻疯病人集中,全送去乡下的一个特大的天然天坑里与世隔绝,让他们在哪进行封闭治疗。
娘俩也就默默无闻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完完全全成为二丫成长路上的过客,她自然存在故事里。
娘俩走后堆在桥头两边的过炭灰,有人需要时,便有人出现在哪,没人需要时,堆啊堆,堆多了又滑下那沟壑下面去,占据着沟壑里的水道,夏天涨水,水又会冲走许多,不管是人为清理,还是自然清理,最终还于自然。
筛框是小城人家户必备的生活用品,自然有大有小,筛眼随框的大小而定,簸箕也是小城必备的生活用品,二丫家煤堆上方的墙面钉子上,就挂着两个不大也不小的竹簸箕,这类簸箕是专门做包谷饭的容器,因为小城人的主食为苞谷,苞谷要拉成面,才能做成常吃不厌的饭。
奶奶每天根据家里人吃饭的量,把苞谷面装在里,洒上一定的水把它发一下,再倒入木甑子里面用炉火篜,篜得差不多便倒回簸箕成圆圆的一坨,面变为夹生的饭,奶奶趁热又洒一定的水量好好让它发一下,边发边使用木饭瓢把没有发松散的疙瘩,又是杵又是按,不一会满簸箕发过的细小饭粒,就变得颗颗匀称,这时奶奶又倒回木甑子里重篜,经过这两道工序,做出的苞谷饭,舀在碗里才会又松又软,越吃越香,越嚼越有味,容易消化。
吃苞谷饭时,包谷饭粒满口钻,这时最好不要讲话,不然会溢喷出来,还会呛进气管“咳咳咔咔”,咳得你双眼直冒泪花子,鼻腔发痒伴随清涕而出。
二丫吃饭时,把饭扒进嘴里,便紧闭着双唇慢嚼,只看见两腮与糊着饭粒的嘴唇,喉咙在蠕动,再看她左手抬的土丕二碗里,碗边糊得粒粒啦啦,右手拿的筷子也是,所以吃饭时,奶奶特别叮嘱大姐、二丫:“一个碗边,半截筷子上啷是不要糊上饭粒。”
二丫听到后,就会把筷子勒在上下唇间使劲地勒,大姐看见:“你那样勒,吐沫也被你勒上,不准你下锅夹菜。”
二丫才不听大姐的,右手使着的筷子没有勒干净,沾着粒粒哒哒的饭粒,又朝沙锅里的酸菜夹去,不得的大姐一把夺过二丫的筷子,顺手扔在三抽桌上。
突然,被姐姐这样用力一夺,二丫身子不平衡地晃了一下,左手抬的碗“哐啷”一声又摔破在床前的踏脚板上,连同半碗的包谷饭,挡灰框里的过炭灰上也有泼洒的饭。
“你两个绝呔呔,吃饭不好好吃,不想吃把碗放下,那边地站着去。”妈妈指着屋里较宽的那塌地。
知趣的大姐立马把端着的碗和筷放到三抽桌上,很快就站在屋里较宽的那一塌地上,耸低着头,不停地绕着背在后边的十个手指头,也不出声地看着自己的右脚尖,忍不住去踢那凸出地面而又坚硬的土疙瘩包包,这土疙瘩包包奶奶称它为牵脚泥。
牵脚泥是这样形成的,它根小城的气候有关;也跟住户家中的土地面有关。
小城大多数住户家里的地面,是原汁原味的土地面,加上阴天多,绵绵雨多,炭灰多,街道上随时是稀垮垮的泥泞地,人走过泥泞的街道,稀泥便会沾在脚底板上带进屋,而进屋的地又比较干,稀泥便在此沾上,时间一久,屋里门槛下的那塌地上,就会凸凹不平,比屋里的其它地面高出许多,这就是牵脚泥。
牵脚泥糊到一定厚度,小城人家户会铲平它,不然会崴着脚,二丫家来的人多,随时看见奶奶在铲除它。
“奶奶,这牵脚泥太厚了,一个包一包的。”站在那的大姐终于说话。
“你最好站在那,不要说话。二丫,二丫还不快点站过去,老是在这磨磨蹭蹭,慢的蚂蚁子在你面前过,你也踩不死它。真是一头慢牛,慢牛,要急死人。”这是妈妈的脆音,也是对二丫性子慢的无奈。
二丫终于磨磨蹭蹭地与大姐站在那塌地上,低头数着自己的手指。
“就怪你。”站在旁的大姐边不得,边用脚踩了一下二丫的脚说道。
“唉…嗯…嗯…”被踩疼的二丫干哭起来。
奶奶边扫踏板上的饭,听到二丫干哭起来,嘴里边自言自语:“还哭,还哭,啷是半碗饭都泼了,粮食啊,粮食,好可惜,现在生活好了,能吃饱肚子,三年饥荒时野菜、树叶、泥巴能吃的都吃,好可惜,好可惜!”
“哎,老婆子,你啷是又在念哪样,可惜啥,碗烂了就烂了,饭泼了就泼了,啷是念念叨叨的,娃儿吃饭哪有不天一半,地一半的,打烂一个碗,过一道关口是好事,这样子娃儿才好养,才好带,啷不要再说了,吃饭,吃饭。”听到奶奶的念叨,老爷也不想再责怪孩子。
“哎,你两个丫头还不抬碗吗?哦,老婆子给二丫重舀半碗苞谷饭来”。老爷又喊两姐妹重抬碗吃饭,并喊奶奶重舀饭给二丫。
老爷非常喜欢自己的每一个孙子,不管姑娘家还是儿子家,他时常叮嘱有点重男轻女的奶奶要做到手心手背都一样。
除了做苞谷饭的簸箕,还有的比这更大更大,有的直径有一米五到两米,或超过这。
这么大的簸箕又用在什么地方呢?
小城人过年最爱吃汤圆,这时大的竹簸箕便派上用场,那就是用来摊晒湿润的糯米粉,最大的便是小城酱菜厂用得最多,酱菜厂用的簸箕,大小都可以利用。
二丫家是直径一米五的大簸箕,平时就挂在楼上朝北的墙面上。
摊晒糯米面,在年前一个月左右,就要准备好糯米。
糯米是粮食局在过年时,按每户有多少人口,限量供应,大米也是这样,要在逢年过节的那几天,人们才能打牙祭,平时家家户户以包谷为主食,可这也是按户按人口供应,如没有户口,不要说吃粮,就连其它的票证也没有,生活当然艰难。
糯米在成米粉前,要在水中浸泡一下,才用竹眼篼背去有踏碓的人家户,交钱排队碓捣成粉。
小城新街有好几家这样的碓房,没有出现电动小钢磨时,踏碓比石磨省力,也会把苞谷粒碓成苞谷面。
到碓房的奶奶,要在碓窝四周垫一圈牛皮纸,怕碓头起来时,把碓窝里的粮食带出掉到地上,可惜了。
奶奶曾经挨饿过,她是被饿怕的人,所以对待粮食特别的珍惜,看不惯一丁点的粮食被浪费,有时走在路上看地上有一粒苞谷或豆子,她都要弯腰把它捡起来,回家后就把它烤在火炉墩旁。有时烤熟让二丫看到,拾起也不擦一下就往嘴里丢,让这丁点的焦脆香味让她过一次馋嘴巴的瘾。
碓房,每当有人在碓糯米粉时,总有一人或两人在踏碓尾踩踏板上的碓尾头,再由一人蹲在碓臼窝边,趁石碓头抬起的间隙,趁机用小瓢在碓窝里捣翻。
碓得差不多,就把带有粉与颗粒的糯米粉舀进细蔑筛分离,把粉分离在下面摊好的大簸箕里,粗的颗粒又倒回碓窝重搗,直到全部的糯米变成粉为止。
踩踏碓与碓臼边捣翻的都是技术活,踩不好的会扭伤脚与腰,捣翻的抓不好时机,同样会伤到人。
所以这碓房也是危险地,奶奶不会带二丫姊妹几个来。二丫喜欢吃汤圆,可为了吃,这也是一件费力又费时的活计,难怪奶奶去碓房捣糯米粉,加上排队一去就是一整天还多,回到家常常夜也很深。
奶奶去碓房碓糯米粉,前脚刚走,二丫后脚便跟在后,偷偷撵奶奶的路。
到了碓房,二丫不敢进去,只能依在门旁偷偷朝里望。望一会,便觉无趣又悄悄的溜回家,小城的碓房,二丫差不多都去过,有时还会给别人指路,让奶奶吃惊不小,才知道她在撵她的路,便戳着二丫的额头,连连说二丫是小撵路狗。
每当此时,只要走在街上,听到远远近近的嘎吱……咚,嘎吱……咚,奶奶总要叹一口,然后才说这一年又过去了,时间真快啊!啷是又要过年了。
对于二丫来说,时间真慢啊!巴不得立马长大。
公房每家住的屋子有限,进家门的房间里都会安置一张床,有的安置两张,那床前便是长年不熄火的大炉子,长燃这样的一个大炉子,就因小城煤炭资源丰富,盛产亮晶晶的无烟煤。
小城煤多,煤矿自然也多,自然有卖煤的人,人们称他们为煤炭匠,煤屑离不开泥巴的拌粘,那卖泥巴的人,称他们为泥巴匠,补锅的称补锅匠,还有鞋匠,箍桶匠,铁匠……全用匠来称呼他们的职业。
煤炭匠、泥巴匠的职业是小城最脏的职业,他们全身上下,一头一脸,一双手及一双脚,没有一处不被煤的黑色浸染;被泥巴的粘灰糊染,让人一看除了脏,还是脏,连走路也离他们远点,怕沾上,所以也是小城人最看不起的职业,连奶奶也会拿他们来吓唬二丫家几姊妹,再哭就喊煤炭匠把他拉走,喊泥巴匠背走。
可他们虽然外表脏,但小城人需要烧煤,又离不开他们,导致他们不停地走街窜巷,成为街道上的一道街景。
煤多,在小城日常生活中就数它不要票,价钱自然便宜。加上小城的气候四季阴天多,日照少,冬季较长而寒冷,春秋雾气重,阴雨绵绵不断,夏天明媚简短,这样的气候小城人离不开炉火,也离不开煤炭。
家家户户,都烧得起煤,并用它取暖、煮饭。
屋里屋外到处是人们码堆着的煤块、煤坨,还有泥巴。
它们不仅堆码在屋里有空的墙角、墙跟处,还会占据到床底下、桌子底下。屋外它们又占据屋檐下、人行道上、窗户下的墙跟。自觉的堆在该堆的地方,不自觉的便堆码在街道边,拦脚绊手,不得不让性格直爽,音粗嗓门大的那些爱管闲事的小城人,实在看不下去,便会站在煤堆旁,泥巴堆前大声吼上一句:“谁家的煤炭、泥巴,堆得无依无实,赶快盘开,不然我叫板车拉走。”
胆子小的人家户,立马从家里提着铲锄跑过来,不吭声地弯腰又铲又刨,重新挪一个地方。胆子大的便会气汹汹地回上一句:“一个大活人,你不会往哪边走。”
就这样,屋外的公共地盘,谁家霸占谁家堆。
二丫家堆在自家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