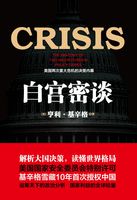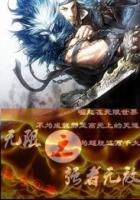一一评甘阳《与友人论美国宪政书》w
甘阳先生向自己的友人介绍了他对当代美国宪政制度实践的思考,并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自由派学者对西方哲学的解读之中的严重的价值流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正如《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一文体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的某种误会砠,在《与友人论美国宪政书》131这篇文章中,甘先生对自由主义思想原则仍有某种程度的误解。
本文拟从甘先生提及的“儿子要和妈妈结婚,父亲与女儿做爱,甚或人与猪狗做爱结婚,是不是也应该都是‘宪法权利’”,是否“完全可以符合自由主义原则”开始分析,借此指出,对自由主义的这种误解并非是一种偶然,乃是一以贯之的一个重大政治哲学偏见。考察思想史,这种偏见并非孤例,而是有其强大的历史渊源和知识背景的,体现了法政理论的各种中国阐释者对丰富多彩的“开放社会”的巨大误解也。
一、被****书写的自由历史
人类的两性关系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群婚制到一夫多妻制(或者是一妻多夫制)最后到一夫一妻制的衍变过程,这一历史同时被视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两性关系的“进化”既然已被视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部分,性价值取向上的“厚今薄古”就势所必然了。一夫一妻制时代否定了群婚制和一夫多妻制(或者是一妻多夫制)。在很多国家,法律还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倘若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之间发生了性关系,在文明的人看来就是“乱伦”,必须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甚至是法律上的制裁。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作为“本我”之体现,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当这种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产生诸如乱伦、****等各种非常规的两性关系。因此,本我有待接受自我之统治,并接受超我之监督、批判及管束。超我的特点则是追求完美,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以理性的名义引导激情,所遵循的正是“道德原则”。
某些特殊的性爱关系受到了异常强大的抵制。以基督教为例,《旧约》上有两段关于同性恋的语录。一段是“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利未记》18:22),另一段是“人和一个男的同寝,像和女人同寝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厌恶的事,都必须被处死;流他们血的罪必归到他们自己身上”(《利未记》20:13)。同性恋应当受到咒诅。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罪”冒犯了三一神,冒犯了受造的自然法则和秩序。
中世纪晚期,欧洲兴起了以教权为斗争对象、以个性解放为目标的文艺复兴运动。古希腊神话里,那种体现生命力激情的性爱观念一一包括对同性英雄的崇拜一一不能不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紧接着,欧洲社会又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约翰·洛克干脆鼓吹起“宗教宽容”。应该说,相对改革之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较之中世纪时期,要“宽容”很多。“禁欲主义”成了众矢之的后,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便开始了一个自我确立合法性、解除法律束缚的解放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这种人本思想看来,人类的发展与欲望息息相关。自由感与幸福感的产生,本质上就是一个欲望得到满足的过程。没有欲望就没有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人类。欲望无须论证,只可描述。从欲望中得出自由和权利意识,这种观念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变革。
伴随着这场变革的正是市民社会的兴起与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生活可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性关系正是私人领域之一部分,不容政府染指。从这个论证来看,****,就人类这一最本源的欲望而言,法律的治理(法治,rule of law)并非万能,反而导致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与人的尊严,从而破坏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本着“个性解放”的原则,国际上于1978年成立了世界性学会。在1997年6月于天主教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召开的第八次世界性学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性权宣言,称为《巴伦西亚性权宣言》(Valencia Declarationon Human Rights)。在中国香港召开的第14次世界性学会议上通过的《性权宣言》,即以《巴伦西亚性权宣言》为底本修改而成。这两项宣言总的原则是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维护性权利,促进性健康,维护性的多样性。
根据这种精神,既然法律已经实现了自由和宽容,只要不是宗教信徒,任何人就没有义务遵守宗教性的清规戒律。但是,这个观念并非一开始就成为英美社会共识。以同性恋的“****罪”为例,直到1869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处罚仍是死刑;到了1969年,该州才将****罪的死刑取消,但仍然要判60年徒刑。在1986年Bowersv.Hardwick一案中,法院维持了乔治亚州《反****法》的合法性,为同性性行为贴上了“可耻的行为”的标签。同时,美国共有25个州有类似的立法。
到2003年,仍然有4个州立法限制同性间的性行为,另有9个州限制任何类型******间的****行为。不过,因几乎从不执行,这些法律变成一纸空文。
1998年,蒂龙·甘莫(Tyron Garner)和约翰·劳伦斯(John Geddes Lawrence)因在休斯敦的公寓内发生同性性行为而被警察逮捕。根据得克萨斯州《反****法》,其行为被认定为轻罪,罚金200美元。此案后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3年,安东尼·肯尼迪(Anthon Kennedy)大法官在宣读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时说,“同性恋者有权利获得他人对其私生活的尊重”,“说服自己的同胞是一回事,强加自己的意见于没有民主的大多数将是另外一件事”。根据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即卩“正当程序条款”(该条款包含“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前者是对联邦和各州立法的一种宪法限制,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者反复无常的,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要求),判决认为:同性恋关系属于公民隐私权的一部分。2003年6月26日,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判决,推翻了得克萨斯州的《反****法》,宣布各州政府不得禁止成年人间相互同意进行的****性行为。肯尼迪大法官指出,希望国家仅仅承担消极不干涉的义务,但并不承担保护促进的义务,诸如以同性性权利为基础的同性婚姻。1“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进一步扭转了美国法律文化。
由于现代性带来的世俗化,美国早已为“堕胎的权利”、“持枪的权利”、“公立学校祷告”和“犯人的自我保存权利”等法律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联邦最高法院这一判决激起了保守倾向明显的基督教社群和其他各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巨大不满。正如甘阳先生所说:“美国保守派的极大愤怒是这些‘新权利’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因此强烈批判法院和法官没有权利‘制定’这些在宪法条文中没有的‘新权利’,而自由派法院则声称这是从宪法精神中可以引申出来的基本权利。”到底应该怎样以自由主义对待这些“堕胎”、“乱伦”等行为,甘先生一筹莫展,只是指出这些行为都“符合自由主义”。如此看来,自由主义理论似乎到了对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的道德堕落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二、****究竟是哪一种自由?
对同性恋之类的异常性行为,西方社会整体上是越来越“宽容”了。1963年,英国的《沃芬顿报告》(WolfendenReport)是最好的证明之一:“除非社会通过法律机构专门去将犯罪与恶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否则就应保留一个由个人来判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领域,这个领域用简明的话来说,不关法律的事。这么说不是要宽恕或者鼓励私下的不道德。相反,强调道德或不道德的判定纯属私下的及个人的性质,是为了强调个人与私下的责任。可以期望一个成熟的人会在没有法律惩罚的威胁下,自觉地承担起责任。”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19世纪上叶法国哲学家邦雅曼·贡斯当批评了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度,指出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在此基础上,20世纪的以赛亚·伯林又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消极自由”关心的是“政府干涉我多少”,“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或自由地做哪些事”;“积极自由”则关心“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做什么事”。“消极自由”的提出在逻辑上深化了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主张。
20世纪中期,哈特反对德夫林勋爵关于“乱伦”等罪行的危害不亚于叛国罪以及进而提出的“以刑法推进道德”等偏激主张。为此,哈特写下了著名的《法律、自由与道德》。这些法学家指出:“在任何社会中起实际作用的制度,包括其实在的道德,都应该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去面对批评。因此,那种认为强制推行道德具有正当性的命题,一如它的否题,是一个需要某些一般性批判原则作为其支撑的关于批判的道德的论题,它不能仅仅通过简单地指出一个或者多个特定社会的实践或者道德来确立或者拒绝。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一个社会之存续必须要求道德被‘如此这般地’强制执行。”
甘阳先生则指出,“例如今后如果儿子要和妈妈结婚,父亲与女儿做爱,甚或人与猪狗做爱结婚,是不是也应该都是‘宪法权利’,因为都是他们的个人自由,并没有妨碍他人,完全可以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既然乱伦“完全符合”了自由主义原则,是不是就意味着自由主义鼓励乱伦?自由国家体制允许同性恋和“儿子要和妈妈结婚,父亲与女儿做爱,甚或人与猪狗做爱结婚”,是不是意味着自由主义鼓吹非正常性关系,否定家庭关系,败坏社会道德,以致最终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产生了这种质疑之后,甘先生很快就联想到了“程度深亥”的后现代福柯,并对法治制度的合法性进行了质疑。
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学说,“它视与义务判然有别的权利为基本的政治事实,并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保卫和维护那些权利”。181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国家必须维护公民权利,并不关心在私人领域内公民权利如何去行使这个问题。
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对公民权利的鼓吹,被伯林看作是最纯正的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伯林看来,没有消极自由这一底线,任何形式的公民权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自由主义反对那种不要消极自由只要积极自由的伪自由观。自由主义主张之个人自由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法律之下的自由和不被他人奴役的自由。它并不关注所谓内心自由的问题,也不关注除去社会关系之外的其他自由形式。
根据这种思路,否定了父亲与女儿做爱的自由,接下去是不是要否定其他形式的性爱的自由,最终意味着以道德的名义,否定公民的任何一项自然权利?然而,人类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乱伦毕竟是不可取的,确实会破坏家庭关系,威胁人生幸福。自由主义不能因为珍视消极自由而鼓励乱伦,又不能在政治哲学上鲜明地反对乱伦。
面对这个烫手山芋,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国家将何以为之?应该说,由于采取普通法体系,而不是大陆国家那种过多依赖成文法,试图一劳永逸落实某种原则的法制,普通法系国家越来越体现了对待这类极端行为的审慎与无奈。它将针对这种特定行为的意见隐藏起来了,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既不作出肯定回答也不作出否定回答。只要公民的这类行为没有侵犯到相关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和侵犯到其他公民的个人自由,就是被法律许可的行为。只有当政治国家以道德国王的****态度利用其政权机关侵入公民私人生活领域时,才以法院的判决案例形式对这种暴虐行为进行禁止。但这种针对特定行为的保护工作并不代表法官个人和其他公务员群体对这种行为在道义上的支持。
一个人要不要满足自己的****,选择与谁做爱,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他人做爱,就政治而言是他个人意愿的问题,是他的消极自由。因此,甘阳先生所云的“女儿与父亲做爱”,只要不涉及刑法意义上的强奸,最多只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自由主义不反对乱伦,并不表明自由主义赞成乱伦。严格说,私人生活及其方式与自由主义无关。
甘先生这里的逻辑是混乱的。他提出人类必须有种自然权利观念,如果没有就必然导向虚无主义。也因此,美国兴起了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理念。然而,历史更证明,自然权利思想来源于自然法理想,来源于基督教教义。与施特劳斯这位犹太人一样,甘阳先生绕过基督教思想,大谈自然权利思想,就不能不说是学术上对根本性的一种回避。
暂且搁置此一讨论。甘先生没有意识到,自由主义或曰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一个重大原则乃是自由国家的核心义务在于维护个体不折不扣的自然权利。但是自由主义或曰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这种意见并不表明它赞成市民社会领域、私人领域内的某种胡作非为。由于社会关系领域的“不反对”并不表示“赞成”,所以就严格的形式逻辑而言,甘先生和他的批评对象反而将人类丰富的、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当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
这就是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这些事物赋予超出其能力的责任的恶果。很多自由民主“战士”或自由主义的误解者以为这样是爱自由主义、爱自由。其实更多是害了自由主义,也害了自由本身。根据甘先生提及的这一逻辑,“自由主义者,既然你赞成维护公民的自然权利,反对来自政治国家的权力干预,那就去乱伦吧,和你家人做爱去吧,和猪狗去做爱吧”!其中思维的极端之处,让人忍俊不禁,也值得在规范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层面深入反思。
三、前、后现代派“程度深刻”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