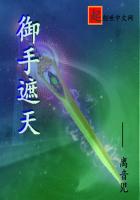天比初时亮了一些,沈临川微微弯下腰,看到冷汗一滴一滴从顾长容额角打落,泅湿了一方宣纸,眼里闪过一丝不忍。
他抬手,想帮顾长容拭去汗水,还未触碰到顾长容的额头,就见到顾长容侧过头去,他的手僵硬在半空中,半晌才收回。
顾长容五识六感之中,缺了一样视,却也因此让了其他感官变得更加敏锐。
譬如,她的听觉。
“我作画时,不喜欢别人触碰我。”顾长容不带情绪地说道,声音极其虚弱。
感觉到沈临川收回手,她换了支笔,控制住微微颤抖的手,继续作画。
沈临川站在一旁,不再有动作。
屋内一时只余下顾长容的微弱却急促的呼吸声,以及汗水时不时滴落在宣纸上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顾长容抬起一张苍白的脸,嘴角弯了弯,未及说什么,沈临川已经急切地捧起画纸。
顾长容虽然看不到沈临川满目的震惊,但那画既然是经由她手画出来,却也猜得出沈临川此刻内心必然不会很平静。
良久,沈临川才回过神来,将已经风干的画纸小心折好,纳入袖口。
他这才朝着顾长容长长一揖,略有些关切地问道:“你可还好?需不需要。。”
顾长容摆摆手,从容弯下腰,摸到脚边另一只丝履,缓缓穿上。
沈临川的关心,就好比这穿了一半的丝履,一旦牵扯上顾长欢,高下立现。顾长容早知道这点,却到此刻才真正死心。
顾长容慢慢直起腰,对牢沈临川:“你走吧,只当我们相识一场,从此两不相干。”
沈临川看到顾长容眉眼间的决然,一双赤眸清澈沉寂,若不是自幼相识,他绝不会相信这样一双眼睛,居然看不见任何东西。
似是无可若何地转过身,沈临川迈出两步,又回过头:“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我保证断然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你。”
顾长容不置可否,只是略略垂下眼眸。
沈临川初初掩上门,顾长容终于松开紧紧拢在袖子里的手,再无法自持,呻吟一声,翻倒在地,青竹轮椅沉沉压在她身上。
腿骨犹如针扎油淋一般的痛,顾长容一头青丝在牵扯间引得头皮撕扯,钻心刺痛。她不由自主双手紧紧掐住腿上薄薄的一层皮骨,试图以此来转移疼痛。
然而剧痛之下,她连挪开椅子都做不到,顾长容痛得狠了,却不由自主笑出声来,这把笑声似有无限愉悦,丝毫不曾作伪。
门突然哐当一声响,顾长容止住笑,怔怔勉力侧过头,心里忽然生出一抹希望。
“阿容姐姐,你怎么了?”
随着东西掉落在地上的声音,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向她迎来。
顾长容的笑僵在嘴角,她心里忽然生出一丝羞耻,也许是痛意削弱了她的意志力,她竟然寄希望于沈临川会去而复返。
就在那一瞬间,顾长容长久以来飘浮不定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处。没有希望和所求,也就不会再有畏惧。
来人手忙脚乱搬开压在顾长容身上的轮椅,用尽力气扶起顾长容:“阿容姐姐,你莫要吓青止。”
这把声音里的哭意让顾长容觉得四肢百骸不再那么凉气逼人,她虚虚抹了把额头,架在身旁少女的肩膀上爬起来,却双膝一软再次跌倒在地。
青止五年前目睹过一次类似的场面,然而那时她还不过十岁,与顾长容还未有多深的交集,是以当时也未有更多感触,早早就将此事抛诸脑后。
但在这长达五年的朝夕相对里,青止的心态早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年来,青止从来只见过顾长容冷静自制的模样,何曾见过她如此狼狈,慌乱之下,青止大声哭喊出来。
“阿容姐姐,阿容姐姐……”
“青止,莫哭。”被吵得头痛的顾长容,哭笑不得地发现因为注意力被分散,腿上的痛意终于消减了一些,她勉力吐出这句宽慰,终于支撑不住,沉沉昏迷过去。
*****
“少爷,听说容姑娘昏迷了,可要派人……”
“暂且不必,你先退下。”疾行在前面的沈临川头也不回进了屋子,他未说出口的话却是,不让她顾长容吃些苦头,怎么能让她死心塌地为他所用?顾长容已生离意,但她的一身异能对他尚有莫大作用,顾长容若是落入他人手中,势必会成为对付他的上好利刃,他绝不能冒险。
身后的中年男人心知沈临川不会再改变主意,却是不由自主叹息一声,悄然退下。
沈临川进到屋里,在床边坐下,看到烛光照在顾长欢惨白的脸上,一时无限憔悴。他双手紧紧握住顾长欢冰凉的手,略有些歉意地说道:“长欢,我今天才知道……抱歉,我不能让你这么早醒过来。”
在顾长欢额上印下冰凉的一吻,沈临川匆匆起身离开,在经过门口的时候,他冷冷地交代门口的婢子:“注意着姑娘床头的灯,不可熄灭。”
“是。”婢子清晰地应了一声,抬头时,沈临川已经扬长而去,视线之内只余薄薄玄衫一角。
屋内烛光打在顾长欢一头银发上,泛着寒气,分明四下无人,却不知哪里冒出一声轻叹,似带着深深的怜悯。
*****
顾长容是被热醒的。全身像是经历了一遭剥皮抽骨,无一丝力气,腿上犹有褪不去的隐痛。她想抬头拭去额角的汗,却被青止夸张的三床厚被压得动不了,几乎要再次晕厥过去。
她虚弱地轻声唤青止。
“啊?啊?阿容姐姐?”青止端着一碗清粥,刚进得门来,听到长容醒过来,连忙快步走进内室。
看到顾长容挣扎着要翻开被子,青止把粥放在床头轮椅上,慌忙去按住顾长容的手:“阿容姐姐,你莫要想了,这回你无论如何要听我的。这被子是我从阿爹那里搬来的,你若不盖,我又得搬回去,你就让我省省心吧。你今天早上真的快把我吓死了……”
顾长容突然觉得牙齿有些疼,无可若何地说道:“……你若非要把我当蚕来养,我拼着一张老脸也要化蝶给你看。但你好歹要让我喘一口气吧。”
青止见顾长说得认真,才微微叹口气,上前帮顾长容掀开被子,就是这么一动之间,顾长容床头一袭丝袍滑落到椅上的粥里。
青止欲哭无泪:“我的粥……少爷的袍子……”
早上她给顾长容带的粥已经掀翻在地,她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清理干净。
今天早上阿爹生病,她才来得晚了,没想到撞上这让人胆寒的一幕,她都快淹死在自责里,偏偏顾长容是个讳疾避医的,她连叫郎中来看看都不敢,刚刚熬好的粥又……青止不由懊恼极了。
顾长容听到青止的话,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伸手摸了摸,冰凉的丝袍入手,她缓声对青止道:“无碍的,我现在不饿。”
歇了歇,她继续说道:“青止,若从我在你家少爷中选一个,你会选谁?”
青止听到这句话,脸色突然煞白,她从五年前被派来照料顾长容,早就把她当姐姐一样,内心里,无疑她与顾长容更为亲近。
然而这五年,她背地里,也干了些上不得台面的事,虽然她怀疑顾长容都了然于心,但到底没有戳破。
少爷要她汇报顾长容的一举一动,她不敢不从。她虽然平日毛躁一些,但顾长容的心性也隐约揣摩到一二,顾长容断不会是受制于人的人。
虽然隐隐知道总有这么一天,但今日听顾长容讲得明白,却仍然接受不了。选谁?她不是没有想过,只是每每逃避而已。
“你,选谁?”顾长容再次问道,明明白白,青止再也无法逃避。
她跪在地上,深深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来,面上挂了两行泪:“阿爹在少爷手下。”
寥寥七个字,话中之意,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