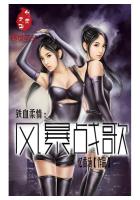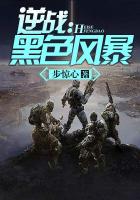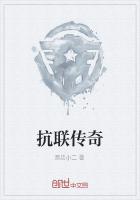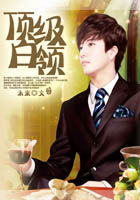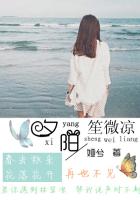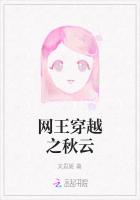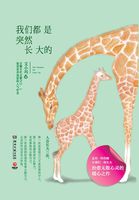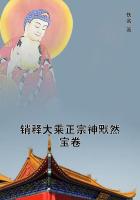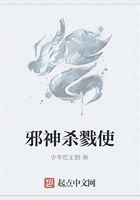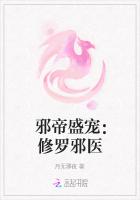从此,他与血与火、沙场与战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脱离军界留学海外的日子里,他关注的还是军事。他当时去德国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学军事。他认为中国当时的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中国军队应该改革。他还对人说,他是个军人,来德国主要是学军事,但来的不是时候,德国刚战败,巴黎和会后军事机关好多都被限制或取消了,困难比以前多。他还曾找过当时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祖,想入军校学习,后魏回信给他说,德国没有军校。后来他只好在柏林大学旁听政治经济学。
在德国,他除了想学军事,还想学航空,他说,因为四川山多,交通不方便,所以想学航空。虽然没有进入军校,但他仍非常关注军事。他曾找一个德国将军,向他学习军事。他当时还买了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役经过的著作,有一二十本,请德国将军讲战役的打法。
在德国各地参观游览,他也都在设想将来这里打仗如何打法。他自己也承认:"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
在德国期间,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1923年夏天德国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演习,朱德在观看了有20万人参加的检阅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
在德国未能入军校学习,朱德便打算赴苏联学习军事,他抱定学习军事为党服务的信念,"来莫(指莫斯科---引者注)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
从此,他的军事生涯便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运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三、身先士卒,履险如夷
朱德打仗,智勇兼备。其"智"在后面的兵法论列中读者可以知其大端,这里只论其勇。
"勇"为军人武德之一,岳飞论何谓天下太平时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是谓天下太平。""武官不怕死",说的就是"勇"。可以说"勇"是对军人的最基本的要求。
朱德的"勇",表现在他每当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身先士卒,或一夫当关,或冲锋陷阵,每每拯全军于败亡之际,扶大厦于将顷之时。
朱德的"勇"又非一蹴即跳的匹夫之勇。他的"勇"与他的"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勇有谋,两者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朱德最初以英勇善战声誉闻于全军的是在护国战争时期的泸州、纳溪之战中。在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他以敢打敢拼,屡挫强敌的实际行动赢得护国军上下的一致赞誉。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后,迅速出兵川南北上讨袁。1916年元旦,护国军第一军分左、右两纵队挥师北伐。朱德为右纵队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支队长。护国军进入川南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但当护国军进逼川南重镇泸州时,袁世凯任命的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曹锟、前敌总指挥张敬尧亦率部抵达泸州,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双方兵力悬殊,护国军被迫后撤,北洋军大举向泸州以南纳溪挺进。于是,川南战局逆转,护国军进攻泸州之战一变而为保卫纳溪战役。
纳溪战役又以纳溪城以东棉花坡一带高地的阻击战最为激烈。2月19日,朱德部接任棉花坡正面防务,同时指挥第三、第六两个支队。他指挥所部以白刃战和夜战,顽强抗击北洋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以攻势防御,采用侧击战术,夺回失去的阵地。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护国军于3月7日撤出纳溪,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保卫战结束。
棉花坡阻击战之激烈残酷,后来有人记载说:"是役也,我军以寡敌众,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总计伤亡及失踪不明者不下千人。而敌军死伤尤众,泸寺观均为医院及停棺之所,弃置双合场一带尸体,尚三四百具,足征此役之剧烈矣。"
3月17日,蔡锷根据全国风起云涌的反袁形势,决定对泸州发动第二次进攻。朱德、金汉鼎支队是反攻的主力。朱德率部经过5天激战,连续突破北洋军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直插离泸州只有十几里的南寿山附近。这时,恰逢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护国军的进攻遂停顿下来。
泸州、纳溪之战,护国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少击多,屡建奇功,对推动全国人民反袁斗争高潮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朱德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他英勇善战,战功卓著。很多次当战线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他率领的部队一赶到,就支持住了,往往还能反败为胜。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他抗战中写的《朱德将军传》中描述道:"纳溪战役,在火线上的朱德同志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只带了两个步兵连及一个炮兵连,在棉花山顶上抵抗敌人一个旅进攻,几乎被攻击毁灭了。
结果,只凭着一千发炮弹,打退敌人。而在最后的反攻里,击破张敬尧。"
"在泸州一次恶战里,把衣服帽子都打烂了,马也打死了---朱德同志仍然没有丝毫损伤的。因为在火线上,他胆大与沉着兼备,使朱德同志从残酷的千百战争中来,没有受过伤。"
泸州、纳溪之战,使朱德成为远近驰名的滇军名将。吴玉章在祝贺他60岁寿辰时曾著文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这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也大大提高了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他自己后来说过:"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朱德投身革命后,就常伴着逆境险情,或处绝境身先士卒,冒险犯难,杀出一条血路;或逢险情泰然自若,机智应付,从险境中走出坦途来。表现了一名伟大军事家的大无畏精神。下面举几个例子。
1927年10月,朱德率千余南昌起义军抵达闽赣交界的石经岭隘口,为摆脱追敌钱大钧部一个师,他手持驳壳枪,亲率几名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在敌人侧后发起攻击,抢占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保证了后续部队通过隘口,摆脱追敌。
1927年11月,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托,带着"赣南三整"时建立的教导队从崇义县上堡出发,去汝城同范石生部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谈判。在宿营汝城濠头圩祠堂时,半夜间突然被土匪何其郎部包围。土匪冲进祠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朱德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伙夫头。"土匪又问:"你们的司令在哪里?"朱德指着后边的房子说:"住在那边。"由于朱德穿着简朴,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土匪信了,就往后跑去。朱德乘机从窗户里跳出,脱离了危险。
1928年6月,国民党军杨如轩、杨池生两部以为红四军主力远出湖南,下令进犯宁冈。杨如轩率三个团从永新县白口向永新、宁冈边境的老七溪岭进犯;杨池生率两个团从龙源口向新七溪岭进犯。
朱德亲率第二十九团在新七溪岭截击杨池生部主力,红军首先抢占了新七溪岭制高点望月亭一带,多次打退了进犯敌军。但敌军在火力的猛烈掩护下,抢占了红军前沿阵地风车口。在这危急关头,朱德手提花机关枪(冲锋枪)赶至望月亭,亲自组织力量把敌人压下去,夺回风车口阵地。战斗中,朱德的帽子被子弹打穿。
这次七溪岭、龙源口一仗,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1929年1月,红四军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决定向赣南出击,以"围魏救赵"方法打破"会剿"。但红军下山后,在赣敌轮班穷追政策下,一度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大庾(今大余)一战,红四军仓促应战,伤亡达二三百人。红军撤出大庾后,朱德亲自殿后,掩护撤退。在向赣粤边境的罗福嶂开进时,朱德和毛泽东及军部被打散,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着,朱德率领他们且战且退,在支持了十几里后,分作两路,朱德仅带一名警卫员,才摆脱了险境。就在这次突围中,朱德爱人伍若兰被敌人抓去,惨遭杀害。
此时红四军决定北上会昌,后情况有变,转攻瑞金。这时城外的红二十八团被敌团团围住,局势十分危急。朱德下令:"全团一个方向,一营跟着我从中央突破,二、三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带头向敌阵地冲去。第二十八团终于杀出重围,同第三十一团会合。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朱德曾又一次兵临险境。那是在1931年8月进攻良村的战斗中,朱德仅率一个警卫排向良村插去,在途中同正由良村增援莲塘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一个旅遭遇。按预定计划,红四军应该抢先占领路旁的山头,但他们没有按时到达,所以被郝部抢先占领了。朱德到达山脚下时,才发现这个情况。当时,他身边只有几个参谋和一个警卫排,兵力悬殊,可想而知。但朱德毅然率部投入战斗,一直坚持到大部队到达,经过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毙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退。朱德又一次及时地扭转了不利局面。
到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已是八路军总指挥(又叫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2月又任第二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即东路军总指挥),除指挥八路军和山西抗日青年决死队第一、第二纵队,还指挥国民党三个军又三个师、一个旅。他临危受命,依然身先士卒,战斗在枪林弹雨之中。
2月20日,朱德和左权率八路军总部和警卫通讯营两个连约200人离开洪洞县牧马村,准备去太行前线。这时,山西局势突变,日军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其中东路日军由于没有遇到正面国民党军的有效抵抗,沿临(汾)屯(留)公路长驱直进,对晋南重镇临汾构成极大威胁。当时,朱德等正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很容易的。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如让日军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朱德除令东路军各部采取相应部署外,毅然率警卫部队在临屯公路上的安泽县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迟滞日军西进。
2月24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同日军先头部队发生接触战。第二天,战场局势更加严重,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攻击更加猛烈,并出动十几架飞机轰炸朱德的驻地古县镇。然而,日本空军驾驶员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后方的人都为朱德安危捏着一把汗。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却被朱德率领的两个连阻击了四天三夜,伤亡达300多人。至28日,日军苫米地旅团才进入临汾。
解放战争时期,已是堂堂300万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还有一次与国民党军大队人马擦肩而过的险情。那是1948年5月朱德赴濮阳视察华东野战军的路上。那天,朱德与陈毅、粟裕率一个车队乘夜南下,突然前头发现正在徒步行军的国民党军,后面又发现几辆国民党军车朝他们开来。有人提议躲一躲,朱德考虑了一下,果断地命令:"前后敌人都不用管它,车子继续前进!准备战斗,没有命令不许开枪!"车子一路前开,行军的国民党军纷纷躲向路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闪而过的车队里正坐着解放军的总司令。
朱德就是这样,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危险,他就战斗在哪里。令人惊奇的是,他身经百战,却从未受过伤,尽管他的坐骑被打死,他的帽子被打穿,敌人的子弹却从未擦破他的皮,仿佛是炮弹、炸弹和子弹都长了眼睛似的,不敢去碰这位伟人。美国记者斯诺在谈到毛泽东多次"大难不死"时曾对毛泽东说:"救了你性命的命运中这些意外的事件,已经使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事业成为可能。"这些话用到朱德身上也完全合适,他人生经历中的这种奇迹似乎预示着他所献身的事业的必然成功。
四、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打败蒋介石
这是朱德给他的云南讲武堂老同学、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对手杨如轩的信中写道的一句话。其豪迈气概,足可睥睨千古。后人读到此语,定能击节三叹,拍案叫好。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每当革命的重大转折关头,都会出现许多父子、同学、夫妻因政见不同而反目为仇,以至在疆场上兵戎相见。第一次大革命是国共合作进行的,两党都网罗了一批有志青年。北伐战争,共产党员的鲜血和国民党员的鲜血流在一起。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原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战斗在一起的国共两党的有志青年开始分道扬镳,成为仇敌。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途中,在会昌与沿途追来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展开恶战,战斗惨烈,可更为令人扼腕的是交战双方不久前还是共同北伐的战友,许多基层军官都是黄埔出身的同窗好友。交战中,双方互相呼喊着对方的名字,厮杀在一起,许多人死在同学的枪口、刀刃之下,这是一幅怎样的惨景啊!
朱德与杨如轩,不仅是同学,还是同盟会的同志,护国战场上的战友。双方的交情可以说是不浅的。南昌起义后,朱德曾劝杨如轩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当时江西境内主要是滇军,其将领大多是朱德的同学或袍泽。除驻临川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外,还有驻九江的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十九师师长杨池生(后来在井冈山,朱毛红军所说的"打败江西两只羊"的"两羊"即为朱德同窗袍泽杨如轩、杨池生。世事沧桑,同学反目,令后人感慨不已)。朱德劝杨如轩弃暗投明的信是这样说的:
"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铠,弟掌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
接信后,杨仍顾虑重重,一怕反不成被杀头,二怕朱德吃掉他。所以没有回信,但也没有与朱德为难。
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朱德率余部来到崇义、上堡一带杨如轩的防区。这时,朱德又给杨去了一信,希望杨如轩"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他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打败蒋介石"。杨虽未作正面答复,但也"沓起眼皮",没有去骚扰起义军。
"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打败蒋介石",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作此壮语,并非吹牛,它建立在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之上。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徘徊、迷茫,感到没有出路,悲观失望,以至一些人脱党、叛变。但朱德却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个信心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上,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上,建立在革命武装必将战胜反革命武装的信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