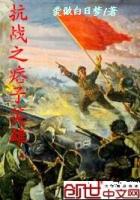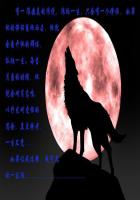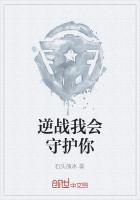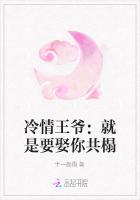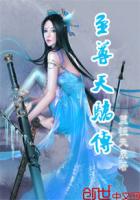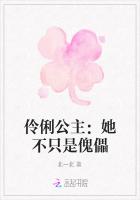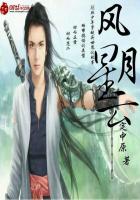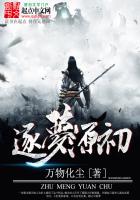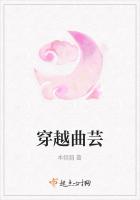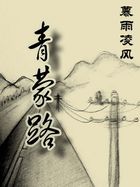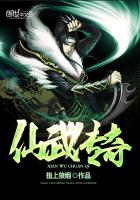八、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在朱德早年生死与共的朋友中,范石生是一位有头脑、有眼光且又曾在朱德艰难困苦中帮助过他的患难之交。但1928年7月红四军攻打郴州一战,把他们的友谊打断了。对此,朱德一直惋惜不已。
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两人交情甚笃,曾结金兰之交,结拜为兄弟,又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还一起参加蔡锷领导下的护国讨袁战争。范先后任滇军第二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同蒋介石矛盾甚深,同中国共产党则早已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四一二政变后,他对蒋介石的"清党"命令阳奉阴违,搁置不理。所以,在他的十六军里一直保存着共产党的组织。范对朱德的军事才能和救国救民大志非常佩服。
1927年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后,朱德带领余部蛰伏湘、粤、赣交界山区整训。一天,他意外地从报上看到范石生的第十六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为保存革命力量,他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范石生,希望同他合作。
信发出半个月后,范派人送来了复信,信中说:"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信中流露出对朱德和他的救国救民事业的理解和钦佩,亦表明了他想与朱德合作,共图大业的愿望。
当朱德与范石生达成改编协议后,范认真履行了协议,即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等要求。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令要范解除起义军武装,逮捕朱德。同时,命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石生的动向。范接到蒋的密电后,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刻派人持信前往部队驻地犁铺头,告诉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来一万块钱,表示他的诚意。信中说(大意):一、"孰能一之?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语出《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一"是统一天下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谁能统一天下,不滥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
从范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朱德和他的理想、事业确实非常钦佩,并从中看到将来的天下非共产党莫属。识英雄于困败厄亡之中,实属不易。能从一个人的穷困潦倒中看到他的胜利前途,表明范亦非等闲之辈,他有眼光,有头脑,也有民主思想。他"收编"困境中的朱德所部,既有出于两肋插刀的朋友之谊,亦有出于"英雄惜英雄"的相知之情,他看到朱德将来必成大事,因此不怕戴"红帽子"来相救。
但是,遗憾的是,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却没有对得起这位有眼光、有头脑的朋友。
1928年7月,朱德率红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进取酃县后,本拟再攻茶陵,重回永新,但由宜章农民编成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欲回湖南家乡,不愿回永新,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红四军军委为防止第二十九团回去孤军作战为敌所算,遂命令第二十八团也去湖南。24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城里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曾经帮助过朱德的范石生的第十六军。这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他们多年前在韶关分别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杜修经坚持要打,说:
"已经打响了,就打吧!"这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攻击事实上已经不能中止了。郴州打了范石生,打了朋友,在政治上是失策的,在军事上也是失利的,郴州打开了,但被范石生一个反击,又仓促撤出。这一仗,红四军领导迁就了农民意识,又受当时"左"的影响太大,结果打了一场完全不应该打的仗。
对此,范石生很不满意,他在总理(孙中山)纪念周上责备朱德,说朱德从广东退回无衣少食,他给朱部以补充,现在朱全不念旧情来打他,不够朋友,云云。
这件事当然不能简单地从个人恩怨来评论,那时候,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这方面确实做了不少蠢事。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这位在困难时帮助过革命的朋友,也不会忘记他对朱德的评价和期望。
九、近"朱"者赤
这个"朱"指朱德。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中有人对与朱德交往较多,过从甚密,因而抗战较积极的卫立煌将军的讥讽。
卫立煌,行伍出身,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成为蒋介石的一员得力战将,他是国民党军中少有的非黄埔嫡系出身而受蒋器重,权倾一时的人物。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围剿"。1932年9月,率部攻克鄂豫皖苏区首府金寨,受到蒋介石特别嘉奖,蒋特地将金寨地区改名为"立煌县"。
但卫立煌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
抗战开始后,他先后在平汉路、同浦路与日军作战。
忻口战役中,他任第二战区前线总指挥,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他对在山西作战的八路军有一定认识。他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非常佩服。八路军人少,武器差,却比人多武器强的国民党军能打仗,这使他不能不感到惊奇,加深了期望了解这支军队的愿望。他对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心仪已久,朱德也很赞赏他积极抗日的态度,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印象。但在头半年的抗战中,两人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朱德在路过临汾时才第一次同卫立煌会面,并同车赴洛阳。
这次同车去洛阳,给他们提供了一次长谈的机会。两个人谈得很投契。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的道理,给卫立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朱德领导的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朱对卫的印象也很好,他说卫立煌这个人可靠。从此,这两个有着类似出身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发展起来。
1938年8月,朱德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于7月5日离开总部,经沁水于8月上旬抵达山西垣曲辛庄的卫立煌驻地,再次与卫会晤,受到卫立煌的热烈欢迎。他们两人单独长谈了整整两天。长谈中,朱德提出:八路军已经比以前扩大了,准备向蒋介石要求增编三个师。卫对此表示同情,并答应接济枪支、弹药和炮弹。这次会面后,卫立煌对人说:"朱玉阶(朱德字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
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不仅积极抗战,而且在国民党军不断向八路军摩擦的时候,他一直同八路军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一些人借此讥讽他是"近"朱"者赤",意思是卫受了朱德的影响被"赤化"了。确实,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在抗战中为民族做了一些好事。
朱、卫之间的友谊始终保持着,即使在后来的三年内战中,也并未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1948年1月,卫立煌出任国民党军东北行辕代理主任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辽沈战役失败后被免职并被捕,1949年初获释,后寓居香港。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卫从香港致电朱德,请其在大军南下路过卫的安徽合肥老家时设法照顾他的家庭安全。朱德将来电转给毛泽东。为此,毛泽东于4月5日专门致电前线部队首长,令他们在路过卫的家乡时注意保护卫的家人亲属和财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自香港致电表示祝贺。这个一年前尚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的高级将领的这个举动,表明他对内战是反对和不满的。
1955年3月,卫立煌自香港回到北京定居,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的回归,谁说与朱德的影响没有关系呢。朱德人格的魅力从卫的转变和归来上得到充分的说明。
十、没有朱,哪有毛
朱德与毛泽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谈朱德,不能不谈毛泽东;谈毛泽东,也不能不谈到朱德,特别是在红军草创时期的井冈山,三次反"围剿"时期的赣江边。
朱德与毛泽东,人们称之为"朱毛",开始很多人都以为是一个人。美国人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也说到:"甚至连中国的一些人也以为"朱毛"是一个人。毛泽东是智囊,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以全部的才能看,是一位人民的领袖,人类物质的领袖。这两个人,都是优质材料制成的。"朱毛之不可分,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韦尔斯语)。国民党叫嚣的"杀猪(朱)去毛",没有让他们分开。长征途中,张国焘要朱德反对毛泽东,朱德仍然不紧不慢,心平气和,但又义正辞严地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朱毛不可分。早在井冈山时期,"朱毛"二字在红四军中就曾写为一个字。那时,在行军途中的岔道口,经常可以看到或字,这就是"朱毛"的合字。大家都明白,见到字就向左转,见到字就向右转。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这个字代表着朱德和毛泽东。朱毛红军也就是这样叫起来的。那时候,老百姓这样叫,中央文件上这样,就连白区的报纸、国民党的电报也这样称呼。
朱毛不可分。直到这两位老人耋耄之年,毛泽东仍记得朱毛的称呼,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
那是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朱毛的交往和友谊历时整整半个世纪。这种情谊经历过血与火、胜利与失败的考验。每到关键危难时刻,毛泽东总关心着朱德的安危。1947年9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的大清河北战役结束后,由于仗一未打好,朱德和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朱拟去野战章军整理一时期,随同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红---引者)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竖立起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回电,电报中关切地说:"朱总是否亲临前线,请加慎重。"而此时毛泽东本人正率领一支很小的部队在陕北高原与胡宗南重兵周旋。不顾自己的安危而关心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战友,这是何等深厚的友谊啊。
毛泽东关心朱德,信赖朱德。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朱总司令。"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朱德六十寿辰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人民的光荣"。即使在"文革"这样的动乱中,毛泽东对朱德仍是相信的。虽然林彪、"四人帮"处心积虑想打倒朱德,但是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我要保他"。使他免遭残酷的人身迫害。由于毛泽东的表态,在党的九大、十大上,他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样,朱德也十分信赖毛泽东。"文革"中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四十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把我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朱德还说: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正是这种对战友的信赖和对革命的信念,才使他在错误打击面前沉着坚定,泰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