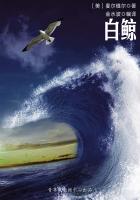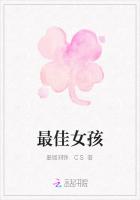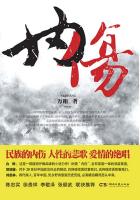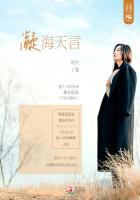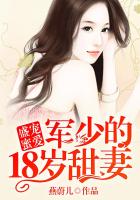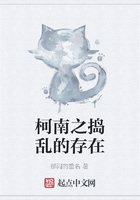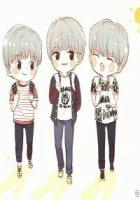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后来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写一个青年****在劳改期间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后来“落实政策”也没遗弃这个姑娘,而是白头偕老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轮廓也许到处都有。因为青年****在劳改期间娶农村姑娘的事例太多了。患难夫妻,没有爱情也有感情,****分子中的“陈世美”终究不多,一般说来,只有暴发户和新贵才会“富易妻,贵易交”,中国的知识分子信奉这一教条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尽管是“责任型夫妻”,也甘愿把这责任负到底而没有反悔。这就是《牧马人》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在三余庄的老庄员中,就有一个与《牧马人》电影情节十分相似的故事。
张永贤,出生于湖北荆州,抗战中随父亲逃难到重庆,在重庆读书长大。划****之前,原是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的助教。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属于军工系统,他在指挥仪专业。所谓指挥仪,就是指挥高炮,用炮火攻击飞机等空中目标的仪器;实际上就是一台包括雷达、光学仪器、机械电气系统的复杂的大型仿真计算机。他教的课程是陀螺仪原理与应用。
他酷爱读书,因此是一个知识面极广的人。他上知天文历算,下知水文地理。他学的是理科,但是文科知识绝不比正牌儿文科大学生少,写起总结来,条理分明,用词准确,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秘书。当时三余庄****队中有位叫杨路的北大数学系学生、1957年百花学社的主将,上学期间就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关数学上的问题,三余庄的人无法与他讨论,只有张永贤跟他说得上话。当时我正在研究古汉语和方言,和他谈起有关音韵学上的问题,他也知道得不少。他父亲是个医生,因此有关医学知识更是得之家传。他爱好音乐,嗓子也不错,是标准的男高音。“****”期间,我还和他合作谱写过许多首“毛主席语录歌”。我常常开玩笑地说:这是个总理的人才。因为当总理不一定需要专家,但必须是个杂家,必须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我也曾经说过:尽管我有3500万字的著作,而他至今连一本书也没出版过,但是我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我却大都不知道。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的时候,他偶然看见一本讲计算机原理和BASIC语言的书,就啃了起来。没有计算机而要学计算机语言,简直就好像在沙漠中学游泳一样,困难之大,难以想象。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他都有了计算机之后,他立刻就能够用BASIC语言编写应用程序,而我则至今仍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什么程序也没有搞出来过。
他的许多知识,有的其实还是在划****之后获得的。划右之前,他有自己要学、要教的专业,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不务正业”,涉猎自己专业之外的课题。划右之后,先被“下放”到北京近郊的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厂里有一个颇大的图书馆,这是他汲取知识的大好时机,就静下心来,有意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他按图书目录的作者顺序一本接一本地读世界文学名著,一共读了有一百多本。后来偶然读了一本《自然地理》,发现地球上的气象变化与天文学密切相关,于是又读了些天文和历法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无人问津的音乐理论书籍,如乐理基础、和声学、曲调作法等。顺便也读了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书。书倒是读了不少,却也因此背上了“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升级”进了劳改单位。
1969年末,根据****的“第一号令”,劳改单位也进行“战备疏散”,大批的“二劳改”被疏散到内地去,张永贤被发配到山西。那里的看守人员(即所谓的“队长”)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作风虽然更野蛮些,但整体的“政治气氛”却比北京差多了。这对我们这些“右”字号来说倒是“好事儿”。“坏”字号的爱闹事儿,队长们忙于对付那些偷摸、打架、诈骗、乱性的事情,对这些老实的“右”字号反倒很放心。****们在北京怕被批判,大都不敢看书;来到山西以后,不仅可以看,甚至还会受到表扬:因为看书的人绝不会闹事儿。有个叫杜友良(记得好像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的****在编《汉英大词典》,收集了几十个练习本的单词,队长根本不懂,却在中队会上作为“努力学习”的典型进行表扬。由于中国与苏联闹翻之后,机械工业方面制定了新的国家标准,熟悉这些标准是必要的。张永贤就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一些机械技术方面的书籍。听说有个叫韩大钧(原科学院的研究员)的****利用业余时间,把一本苏联编的难度颇高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中两千多道题全部做了一遍。为了锻炼,张永贤也买了一本《习题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用十几个练习本完成了这一“长征”。当时他在钻井队,有一个在机运队的****胡伟(原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四年级学生),因宿舍靠近,经常来找他讨论力学方面的问题。陀螺仪的基础本来就是力学,讨论起来也就驾轻就熟。这也就是张永贤劳改20来年,学业和基础理论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所提高的原因。
在三余庄的年代,我担任大门口值班,张永贤担任二小队小队长。大家都知道,凡是能在教养队当“小队长”的人,都是队长眼中的积极分子,是要“帮助”队长“做工作”的。反过来说,也不免要“得罪”甚至“伤害”一些“自己人”。独有这个张永贤,以“不出卖同类”为原则,是几个“小队长”中口碑最好的一个。当时我与他的过从并不密切。我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半,1963年仲秋季节,就从教养队搬到了就业队。他的定期是三年。前面说过,凡是定期三年的“三余庄庄员”,除少数几个外,劳教期基本上都无限期延长了。他恰恰就是那少数几个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够“准时”解除教养,不是因为他表现得特别突出,而纯粹是“撞上大运了”。
《劳改教养条例》,是1957年8月3日公布的。当时所有被劳动教养的人,都没有定教养期,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结果是被劳教的人没有盼头,情绪低落不好好儿劳动。为此,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在1961年5月24日给全体教养分子定了教养期,日期却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以前不论已经劳动教养多少年,一律不算。但也不是一儀切,其中也有例外。张永贤就是这少数“例外”中的一个。
北京市公安局在教养分子中召开大会宣布教养期固然是在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进行的,但是给教养分子定期限这一决策,则必然早于5月24日。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凡是5月24日前不久处理的案件,所定的教养期就是从宣布教养的那一天算起。张永贤被划为****分子以后,先在清河制呢厂监督劳动,因为把时间都用来看书,被定性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于1961年4月27日在海淀区公安分局宣布“升级”送劳动教养的,定的教养期是三年。因此到了1964年4月27日,他的教养期满了,农场当局就准时宣布他解除教养。而在他之后,凡是三年到期的,时间虽然不到一个月之差,因为政策临时有变,就再也没有人准时解除过。他搭上的是“三年到期准时解除教养”的头班车,也是末班车。由此可证:定期三年不解除教养这一决策,肯定是在1964年4月27日之后作出的。
他解除教养以后,并没有搬出教养队,而是担任七中队的统计员,与中队技术员云照洋合住一屋,房间里冬天有火炉。除此之外,一切待遇都不变。
他是三余庄出来的****中第一个娶媳妇儿的人。但这绝不是他主动想争这个第一,而是“天上飞来的金凤凰”,真正的“喜从天降”。
三余庄七中队是个教养中队。当时的规定,教养人员是不许结婚的。一旦解除教养,留场就业,名义上是“公民”了,当然允许结婚。事实上,当时就业人员在农村搞对象结婚的也不在少数。只是****教养队出来的人,幻想比较多,总惦着能够回到原单位去,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有人想到要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安家。我就曾经宣布:不离开劳改农场,绝不考虑婚姻问题。
三余庄七中队猪圈有个喂猪的老头儿,姓韩,家住德胜门外,他老婆是延庆县农村人。他见新上任的统计员年轻英俊,为人厚道,一打听,原先还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就惦着让老婆在延庆农村给他找个对象。于是这个“月老”就主动地找到了张永贤,半年中不下三四次跟张永贤说起这件事儿。说那个姑娘今年还只有18岁,怎么漂亮、怎么贤惠之类。那一年,张永贤28岁,两人相差十岁,差距不算太大。但是他也很犹豫。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劳改农场不是成家立业的地方。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在这样的场合结婚。可又架不住韩老头儿一个劲儿地相劝,张永贤终于被他说动了,答应先见个面,时间定在1964年的国庆节。
到了国庆那一天,姑娘已经到了德胜门外韩老头儿家,张永贤却临时有事情去不了。
什么公务如此重要,连相亲这样重大的事情都顾不上?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而是与教养人员利益有关的小事儿。
那时候,团河农场承接了一宗“买卖”,要在农场的南面开挖一个人工湖,把挖出来的泥土堆成假山,再建起一些房屋来,以供人们度假用。任务就落到了三余庄这些****们的肩上。挖土方可是个重活儿,不论是挖土的,抬土的,每天都要出几身大汗,光靠早晨那一个窝头一碗粥,根本顶不住。因此凡是北京有家的,纷纷要求家里送吃的,最好是肉食,最多的是炒面。北京没家的,就偷偷儿写信回家要家里寄。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为了“贪图享受”,而的确是肚子饿,干不动活儿。按说,教养人员从自己家里拿吃的来,为农场干活儿,是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应该鼓励,至少不应该反对。但是当时的劳改农场最怕传出“劳改队里吃不饱”的“谣言”,因此特地规定:不论是接见送来的还是邮包寄来的,食物一律不得超过一公斤。我值班的时候,采取的是“瞒上不瞒下”政策,让队长检查的,的确只有一公斤左右,剩下的,都塞在我的铺底下,等晚上再叫人家悄悄儿拿走。曾经有过一个姓林的劳改释放人员当值班员,采取的是“铁面无私”政策,接见的日子,凡是家属送来的食物,愣是用秤称过,多出一公斤的一律退回!在队长面前,他固然赚了个“好”,在教养人员的心中,可也赚了不少的骂!
在南苑街上,有一家小饭馆儿。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透露的消息,得知三余庄有这么一批“饿鬼”,常年患有“胃亏食”症,于是每逢三余庄休息日,就派两个姑娘用三轮车拉来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在七中队门口叫卖。开头只限于手头有几个零钱的人光顾,后来有人到队部去苦苦哀求,总算说软了队长的铁石心肠(关键还是吃饱了好多干活儿),允许手上没有现金的人,采用统一记账的方法,也能吃到油饼。但是一次只允许买两个,多了不许。
统一记账,任务就落到了中队统计员的身上:谁买了油饼,要开列名单,从各人的存折中提出钱来,汇总后交给卖油饼的姑娘。原先主持这一工作的统计员姓苏,上海人。这个人劳改出身,对教养人员的饿肚子,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执行队部的指示很坚决:队长指示每人一次只许买两个油饼,他就多一个也不许。因为他说话有些女声女气的,大家都叫他“苏三”,以此发泄对他的不满。
自从张永贤接任统计员以后,他是亲自尝过“饿鬼道”中的滋味的,知道饿着肚子做土方,饿得眼前金星乱迸有多么难受,因此采取的也是“瞒上不瞒下”政策,只要买油饼的时候队长不在旁边盯着,就网开一面,只要不过于出格,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尽可能敞开了买,以满足“饿鬼”们的需求。
国庆期间,正是“油饼姑娘”来卖油饼的日子。张永贤如果不在,势必由队长亲自“主持工作”。那么一来,“每人每次两个”的规定,势必坚决执行,节后的一个星期,必然又要“眼冒金星”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张永贤国庆节期间没有休息,10月3日赶到德胜门外,那个延庆姑娘见他老也不来,差点儿就要走了。
一见面,那姑娘果然长得不错,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辫子长长的,身材也很苗条匀称。既然是“相亲”,反正就是玩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怕路途遥远,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儿个痛快。
姑娘姓阎,延庆县紧北边的阎庄子村人,家里父母双全,贫农成份,有个哥哥是乡村小学的教员,还是党员。她自己小学毕业,是共青团员。
一听她家的政治情况,张永贤就觉得两人的身份有些悬殊,无法结合。如果女方是地主或富农的女儿,倒是“门当户对”了。于是他尽自己所能,给她解释什么叫做“****分子”:简单地说,****分子是“****、反人民、******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阎姑娘不信,反问:你不是已经摘了帽子了吗?只要摘了帽子,就说明你不再“****、反人民、******主义”了。张永贤只好再给她解释为什么摘了帽子的****分子依旧是****分子。但是说来说去,怎么也无法使她明白他们俩是两个政治体系中的人,是不能结合的。阎姑娘最后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要是就因为我是个团员你不能娶我,那我就去退团。
看起来,阎姑娘是真喜欢上这个一肚子学问的****分子了。也许她十分明白:张永贤要不是一个****分子,像她这样一个农村户口的小学毕业生,是说什么也不可能跟他谈婚论嫁的。
张永贤被阎姑娘的朴素纯真感动了。这是一张真正的白纸,可以让张永贤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天的畅谈,婚事就这样基本上定下来了。
11月7日,星期六。张永贤请假由西直门乘夜间火车去延庆阎家。实际上是上门去让女方相亲。这样的人才,当然老岳父一眼就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