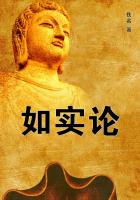别了邢家母女,一路上封氏皆微皱着眉。姜母初见邢婆子的作派,也狠瞧不上眼,未免刻薄两句。封氏方叹道:“她女儿岫烟倒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只是可惜了。”姜母点头,“说的就是呢,好好一个孩子,摊上这样长辈,将来终身指不定要受拖累。”
两个都不免叹息。英莲在旁不便插嘴,心底却笑她们枉作杞人了,岫烟家境虽然贫窘了些,父母又是年高无德的人,难得姻缘却算好的。
薛蝌人物自不用说,形容举止原似宝钗的亲兄弟,又有个绝色剔透的妹子,他还能差到哪儿去?再者薛家根基尚在,虽富而不贵,在世人眼里,也属佳婿了。若说有遗憾,也只是包办一条,且日后脱不了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俗套罢了。
可话说回来,现今这世上,心意相通两情相悦的眷侣又有几对呢?恐怕,也只得宝黛两个痴儿了,一生所系,惟情之一字,至真至纯,可欣可羡,偏结局又极惨淡。
正思忖间,忽听姜母话头一转,问封氏:“人家孩子的终身咱们且不去管,倒是你在那里得了句甚么高兴话?我才几次要问呢,竟都岔了过去。”她心里原存着一段心事,对此自然热切些。封氏也明白,当下微微笑道:“也并没说甚么,不过是教我放心吧,到时候自有结果。”
英莲已经走远了几步,偏耳内听得真切,禁不住摇头,这卜辞倒同妙玉的一个样了,偏妙玉结果又不曾言中。想来也只是那老太太故弄玄虚一番搪塞罢了,于是一笑而过,不以为意。
姜母见问不出来,也只得怏怏作罢。封氏心下惭愧,惟有粧作不知,一时坐船到家,晚上在枕畔才同士隐细细说了。夫妇二人一宿言谈商议,不在话下。
转眼到了冬底,甄家忙着过年事宜。长安也回来了,到家先把帐册子给英莲看。英莲仔细翻完,除去本金并各项费用,这间小小铺面连头带尾不足一年,所赚竟也有七八百两银,虽不是大利,也甚可观,足够她来年再买间铺子了,自是欢喜。
因算了年账,铺内掌柜活计都要回家团圆,士隐身为东家,免不了治酒饯行道一番辛苦。长安作陪,席间主雇把酒言欢,十分尽兴。那郝伯原是个积年的老买卖人,生意做精了的,因见主家实诚,又是旧主人所荐,酒至酣处,少不得把肚内密藏的细话也说与一二。生意场上的关窍,士隐虽不大懂,长安却晓得利害,一面点头,一面都记下了。
一时说起香料贩卖利息更大,郝伯道:“往年也曾跑过北边的,一趟下来,除去关税花消,也剩得几倍利息。”士隐听得北边二字,不觉心动,于是问:“既这样,咱们眀年便跑一趟何妨?都中我虽没甚熟人,但想来也不难罢。”
郝伯忙笑道:“不是这个话。都中咱们虽也去的,只是一来本金有限,纵使七八百两全拿出来,一趟够干甚么的,赚头不多,还白搭了工夫。二来仓促之间,也不知明年行情怎样,若是短缺还好,倘那边已经积压的多了,咱们去了不赚反赔,所以要先打听准了。”
士隐听了有理,笑道:“倒是我性急了。”亲自斟了杯酒与他吃,郝伯忙起身谢领了,喝干坐下。众人又把盏多时,至酒席散后,士隐又亲送出去,议定灯节过后铺子开门。
回房同封氏说起,封氏也嗔他急,“即便再等一二年也无妨,打谅到时怎样呢,偏你才听见个音儿,就又坐不住了。”士隐正要辩驳两句,抬头见他女儿笑吟吟进来,也就停住这话不提。
诸事妥当,年也就到了。岛上人口单薄,以往甄姜两家总是凑在一处守岁,今年也不例外,可喜仲康亦不曾外出,长安也在,除夕之夜,大家宰鹅烧鱼丰丰富富吃了顿饭,另摆了许多茶点果品,耍子猜谜,讲笑话,说故事,闹到三更方散。次早起来又紧着拜年,都穿着姜母封氏亲手裁剪的新衣,虽不抵华裘锦裳,也个个脸上喜气盈腮。这发自内心的欢欣与喜悦无疑感染到英莲,她怔怔的想,或者,就这样过一辈子,也是好的。
花苞在枝上悄悄探头,一点,两点,三四点,狠不爽利。因记挂着岫烟相约的事,英莲对屋后一干梅子树也不免注了意,每日都去转两遭。
长宁笑她呆,“横竖今年花期已是迟了,有这样等的,倒不如直接去看的干净,纵不赏花,望候望候人也好,来回也才半日,船又现成。”
英莲一想也是,便央了士隐封氏,因是节间,士隐痛快也就答应了,还说:“你们先去哨探哨探罢,只是白跑一遭,回来可别哭鼻子。”听的人都忍不住笑。英莲也故意跺脚,“我都多大了,还哭鼻子?也忒小看人。”
说着出来,上船径直到了蟠香寺邢家,一起的还有长宁长安姜福。兴冲冲一到邢家门首,先就见着大门紧闭,门上已封了锁,众人不免傻了眼。还是长安走去问了邻居,才知投亲去了,离开已有多日。
英莲原地懊恼了会儿,说声,“走吧。”一面也就慢慢出了巷子,邢家投亲到贾府本是迟早的事,她只是诧异怎会这样急?明明岫烟过了年也才十二岁。长宁见她闷闷的,自己也分外扫兴。姜福不知就里,说句,“好歹梅花还是在的。”把她噗哧又逗乐了。
这样回去总是败兴,四人站在巷子口商议下一步去哪里探梅,正争执不定,忽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迟疑问:“这位,莫不是甄姑娘?”英莲忙住了嘴,拿眼一看,来人却也认得,正是妙玉跟前的那位老嬷嬷,不由一愣,忙说声是。
柳嬷嬷这才扫去愁容,露出一点笑来,“邢家去南京了,因走得急切,来不及跟姑娘招呼,邢姑娘便留了封信在我们姑娘那里。”说着前头颤巍巍带路,领他们去。
一路上闲谈,英莲才知,此番邢忠投亲,去的不是都中贾府,而是南京他弟弟邢德全那里。柳嬷嬷又说:“这几日我去河沿子问船,来回经过都要在门前望一望的,生怕错过了人来。”英莲忙又道谢,柳嬷嬷摆手,“应该的。”
英莲总觉她满腹心事,有话要说,于是问:“妙玉还好吗?”柳嬷嬷嗐了一声,就不言语了。英莲心里一想,妙玉得罪了陈家,所谓权势不容,这里自然是住不得了,多半怕也要走,遂安慰道:“放心,这一节总能过去。”
谁知柳嬷嬷听了这话,愈发愁眉,“这个劫。”欲言又止。一时到了妙玉院门前,因长安姜福两个男子不便入内,英莲便教他们暂去别处逛逛,到时辰寻不见,就在自家船头等着。
柳嬷嬷看他们去了,才忍不住问:“是你自家的船?”英莲点点头,也不曾多想,一脚随了她进院。院内梅树依旧,树下石桌石凳俨然,英莲轻轻走过,心中不觉起些异样。行儿打起帘栊,一面向内回话:“甄姑娘来了。”
英莲忙抬步进屋,先就见着紫檀木大条案上铺有画纸,雪白的底子,斜逸横出三两枝梅,花骨朵点上去,嫣嫣的,似已经等不及开了,口里忍不住赞声好。妙玉一笑,从案后转身出来,请她榻上去坐,一面吩咐上茶,取邢姑娘的信。
两个便坐着说话,英莲因她多日不见,比先越发清减了,便猜是为着陈家的事烦恼,有心开解两句。不想妙玉已含笑道:“可恨岫烟原约了你来此赏梅的,现今梅花将开未开,已是眨眼的事,她倒先走了,独留你我。”
英莲见她言谈轻松,且能顽笑,不由也放了心,说:“等哪日见了,必要罚她。”一面接过信大略看过,也就收起。行儿自拉长宁去外间吃茶。
柳嬷嬷便走进来说:“难得姑娘与我们姑娘有缘。听说那日姑娘来,还是师太请的,姑娘不知道,我们老师太时常闭关修炼,一年里也难见几个人,就连我们姑娘,除了功课训导,也难进她院子。不想姑娘得她老人家青眼,且一来,便遇着我们姑娘,可不是有缘怎的?”
英莲心底暗吐舌头,却也不好道破老太太的身份,只得说声惭愧。却听柳嬷嬷又道:“院里这红梅花,原是极好的,可惜我们也等不及看了。”英莲一惊,情知她们必定要走,却不料也这样急,不禁追着问了句,“怎么?你们要走?几时的事?”
转眼看妙玉。妙玉也不瞒她,“左右就这几日了。”柳嬷嬷在旁插嘴,“自然是越快越好,可惜没。”却被妙玉打断了,说声头痛,意思便要送客。
英莲知她性子,也不好再留,告辞出来,下了阶,走了两步,心底便疑惑起来,一转身,柳嬷嬷皱着脸还在送,于是住了脚。
妙玉对着茶杯出神,见英莲去而复返,也并不诧异,只抬手请她坐了。英莲想了一想,遂道:“才竟忘了说,我原是做生意的,打谅也要去都中探探行情呢,不如我们结个伴,搭个伙,一路上也好彼此照应。放心,我的船虽简陋些,里面装七八个人并十来箱子家什还不成问题,管船的人我也现有,也不是没走过远路。”见妙玉不出声,笑了一笑,便问,“你看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