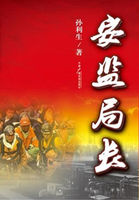宇文介最怕的一桩情形出现了——
太子营帐里,宁歌尘坐在主位上,正低着头闲闲地看书,从头至尾眼皮都没抬起过。
宇文介坐在左上首,瞅着对方那清淡如水的神情,脸都要扭了起来:难道,是昨晚上那个小美人伺候不周,惹恼了这位不成?
可这关我什么事啊?你老人家委屈给我看,我又委屈给谁看?
要知道,他宇文介此番可算得上是史无前例地忍痛割爱啊,如果不是看在彼此从小厮混到大、好歹二十年左右的交情上,他怎肯如斯慷慨地将那等绝色尤物就这样拱手相让?
不过从宁歌尘的面上,还真让人看不出什么喜怒来,好在之前,宇文介为保自己万无一失,特地从别处摸到了风向:太子帐中的碧莲姑娘,正是他一手安排而进的亲姑表妹。
碧莲虽然一贯不喜多嘴,奈何被他问及,还是一五一十全倒了出来。
据说他们这位主子,对那位侍寝的美人不是不满意,而是满意得太过了,一整晚上温存怜爱不说,到了第二天早上,居然还不肯善罢甘休,一路追着人家不让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看上去被人劈了一剑的样子,总之回来的时候,太子殿下不止有伤在身,而且神情很不一般。
“伤倒是小事,”碧莲鬼鬼祟祟地道,“不过你简直无法想象,主子当时候的脸色,真够吓人的,好像要把我们大家都给吃了。”
太医给上药包扎后,宁歌尘就一声不吭地冷着脸坐在那里,握笔写写画画什么的,横竖也没人敢梗着脖子上前看。
也不知道他到底写了什么,时不时将上好的宣纸奋力揉成团,烦躁地一把丢进纸篓里;等到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却又耐不住地重新提笔,继续一笔一划地写,然后毫无意外地再行毁掉……
反反复复,纠纠缠缠,前所未有地心浮气躁。
她们这些人,对这一幕都看在眼里,心中未免好奇。
后来,还是胆大的霓裳趁人不备,从废弃的篓子里偷出一个纸团来,私下拿给众人一看,只见上面重复不断地写着的,竟然都是很简单的同一句话——
你若撒野,今生我把酒奉陪。
仿佛压抑着内心深处波涛汹涌的情感洪流,他的笔锋凌乱锐利,落笔处看似无意,却好像要力透纸背。
这一堆青春懵懂的姑娘们,看到纸上那一行行用尽全力写就的字,忽然之间,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心里自然都很不是滋味。
就连碧莲这种心胸豁达的,都难免怅然难受,仿佛遗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话说回来,宁歌尘已经保持那个坐姿长达三个时辰了,还让宇文介在一边干巴巴地坐着陪读,专门欣赏他老人家一成不变的绝世风姿,左手举累了换右手,右手举累了换左手……这还是人类应有的行为吗?
感情你是要跟我拼耐力啊?想让我憋不住开口,好让你落井下石?没门……宇文介恍然大悟似的,连忙挺直脊背,摆了个正襟危坐的姿势,决心奉陪到底。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了,渐渐地,渐渐地,宇文介化作了一尊僵硬的石头雕像,而太子殿下还是一副淡定自如的模样。
傍晚时分,这位一宫主终于涕泗交零地败下阵来。
“阿尘,”宇文介努力抻着自己早已僵硬的胳膊腿儿,以一个极其艰难的角度缓慢地上扬着,做了一个甘拜下风的手势,“你老人家还是这么毒,总能找到清新脱俗的法子整我,找我来究竟有什么事,求你还是快说清楚吧,无论赴汤还是蹈火,我都答应还不成吗?”
宁歌尘等的就是这句话,这下终于肯掀起眼皮看人了,闲闲的,凉凉的:“你要是敢出尔反尔,后果自负。”
宇文介点头之余,暗自抹着泪花儿:其实说之前,他就已经后悔了……
宁歌尘看到对方那副表情,脸色稍稍和缓了些:“从明天起,你这一宫主万事不做,天天给我负责保护一个人的安全……”
宇文介惊愕了:“你让我吃闲饭……周围这么多人的眼睛看着,影响不太好吧?再说了,我也不好意思呀。”
“既然如此,”宁歌尘顿了一顿,善解人意道,“要不现在就撤了你的职,好让你心无旁骛?”
宇文介揩揩冷汗:“……其实这个世上,闲饭还是要有人吃的。”停了一拍,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要是真撤了我,我手下那一部群龙无首,拖儿带女的,还不都得去喝西北风吗?”
宁歌尘想了想,重新选拔一个一宫主的确比较费事,他懒得去没事找事做,于是道:“行,不撤,不过保镖你也得给我兼任。”
宇文介知道自己落了套,这对他而言,等于是在翅膀上套上了一副铁链子,可还不能拒绝,只得苦大仇深道:“你让我给人无偿卖命,好歹也让我畅所欲言,提几个小要求吧?”
“你说。”太子殿下对他还算不错的。
宇文介这才奸计得逞似的,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不慌不忙道:“你要我保护的对象,如果是老头子老太婆什么的,可千万别找我,我可没那个尊老爱幼的耐性,也许一不留神就把他半路送上西天了……”
“要是俊男的话,你应该找天衡出马,那小子长得一副娘娘腔的样子,跟那个什么雪国皇帝有得一拼,他们俩挨得又近,鬼知道背地里到底有没有一腿?总之天衡是最适合凑在男人堆里搞断袖的人选……”
雪国,雪皇跟天衡在冥冥之中对视一眼,齐刷刷打了个冷颤。
“女人嘛,成色差的跟中人之姿的都该找阿飞那小子,反正他也不懂欣赏美丑,天下间的女人在他眼里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压根就没什么区别,让他照顾美女不是浪费资源么……(阿飞也在直径距离三十里之内哆嗦着);成色好的话,在你说之前,我肯定已经贴身保护过了,而且至今都保护得很好才对,应该不会有啥漏网之鱼吧?哇哈哈哈……”
他还没笑完,一本硬皮书已经结结实实砸到了脑门上,宁歌尘恼羞成怒,一脸黑线地在座位上斜睨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