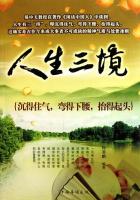札兰丁回头冲他挤挤眼:不用,我有人伺候。
伊勒纳赤丁小声地问:想娶媳妇?
札兰丁摇摇头:我有媳妇,我这就去接。
伊勒纳赤丁也听说过札兰丁在蒙古有一相好的姑娘,一听札兰丁提起知道他是想把那蒙古姑娘接来了,就笑着回头对站在院里的弟兄们说:等十户长接了媳妇来,让他请客。
札兰丁爽快地答应着:一定。
大家围着札兰丁号下的院子,找了几家房子好一点的,三三两两自动结合安置好了住处,又把马匹集中起来,把领到的驻屯物资、马匹、草料大车、毡房统统收拾好,这才正式驻扎下来。
伊勒纳赤丁猜中了札兰丁的心思,他真的想去趟蒙古了。安排好驻屯事务他就趁百户长巴雅尔来视察时提出了请假申请,他是军户,出远门是要请假的,没有巴雅尔的批准,他到不了蒙古就会被抓起来。
那天,他陪巴雅尔在村里转了一圈,察看了军士们的住处、马厩、伙房,然后就顺着一条小胡同出了村,来到村外的地头上。
这里和札兰丁自小居住的草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致,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散落着一个个村落,村与村之间有被行人车辆踩出的道路连接着每个村子都是由很多的小家小院组成,小的村子也有十几户,大的有百十户人家,尽管房子有新有旧,但大部分还是一致的,都是用土坯垒成,打开门窗,房子里敞敞亮亮的,虽然不能和他们攻陷的州城府县相比,可遮风挡雨还是比蒙古人的毡房要舒服得多。附近的几个村子有的还有人家居住,有的就成了空村,札兰丁住进这个村子后有人偷偷进村被札兰丁的属下抓住,札兰丁叫人放了他,并告诉他愿意来和他们一起住就可以留下那人回头领着一家人回来了,后来又陆续有几户人家来到村里。显然巴雅尔注意到了这一点,出了村他问札兰丁:你这里原本不是没人吗?哪来的百姓?
札兰丁赶紧汇报着说: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村的,是躲避战乱出去的听说战争停了又回来了。
巴雅尔脸沉了下去,他站在地头扬手一画,不耐烦地说:现在这里是大蒙古国探马赤军的驻屯地,不是什么大金国的村庄,他们还想来要回他们的东西?做梦去吧。
札兰丁走到地头蹲下,抚弄了一下正在分蘖的麦苗对巴雅尔说:百户长你看,这叫冬小麦,听说是头一年种上的,这时候刚返青,到底怎么侍弄它们,我们一概不懂,咱们都是牧民出身,啥时候摆弄过庄稼地?回来几个不正好给我们当当教头嘛。
巴雅尔无话可说了,他望着眼前铺展开去的绿油油的麦田,慢慢地点了一下头:你小子算是跟巴根学好了。
札兰丁一看巴雅尔的脸色有所缓和,忙装作讨好地请示着:我做得不对?不对我再撵走他们。
巴雅尔想了想,甩了一下手:算了,就叫他们留下吧。他说着向村里走去:回去牵我的马,我还得到别处看看,本来想在你这里住下,刚才转了一圈,你这里也没啥好吃的。
札兰丁赶紧挽留着:你就住下吧,我还有事求你哪。
巴雅尔停了下脚问:什么事?
札兰丁讷讷了半天没敢说实话:我想去看看巴根。
巴雅尔疑惑地看着他:看巴根?你认得路?
札兰丁一指自己的鼻子:这下边有嘴。
巴雅尔酸酸的口气说:巴根是个有着三个窟窿的老狐狸,他能有你这么个忠实的属下,是他的福分。
札兰丁赶紧挺起胸抬手拍了两下:我现在是您的属下。
巴雅尔连连点头:对,对,你的忠诚可嘉,安排完这里的事,你就可以上路了,我给你令牌。
巴雅尔走了,札兰丁叫齐所有的兵丁和刚回来的百姓,一直把他送到村口,直到他的马扬起的尘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他才挥挥手:散了。
人们散去了,札兰丁一个人顺着大路溜达着来到黄河大坝上。
据回来的百姓讲:黄河是从他们原来驻屯的黄土高原过来,那河里的沙子就是从那里带过来的。这个季节凌汛刚过,是一年中的枯水季节,河水还在中间的河道里流着。到夏天上游一下大雨,整个河槽就会满满的,那真是泥沙俱下,洪水滔滔,弄不好大坝一决口,满坡的庄稼就会被淹到水里,到秋天颗粒不收不说,闹不好挺好的熟地一下子就会变成沙滩,好多年都养不过来。人们都说黄河十年九决口,可老天爷保佑,这里几十年没出过事了。
札兰丁撇撇嘴,又笑了笑:什么老天爷?这世间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的要懂得知感。
百姓还一时弄不明白,他们心里的老天爷和这伙新来的西域回回兵说的真主是不是一个人,只有连忙点着头:是,是,要知感。
大坝很高,站在上面看下边的村子,那一座座房屋就像一个垒起的小鸡窝子一样。村子的外边,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地向远处铺展着,又被地畦田垄和纵横的阡陌分割成一个个方块。札兰丁看着看着觉得不如他过去呆的草原好看,草原到了青草没脚高的时候正是最好看的时候,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花,一抽鼻子就有一股香气侵入人的心脾,可这里除了满眼的绿色,再也看不到一点生动的地方。不过伊斯玛仪说过,一亩土地就能够一个人一年的嚼啯,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有很多的余项。
坝顶上长着高大的白杨、垂柳和槐树,浓密的树冠给这里遮出了一片荫凉。找了一棵粗大的垂柳,札兰丁在树底下坐下来。垂柳轻柔绵软的枝条从树干上一直垂下来,新钻出的娇嫩叶片被河道里刮过的清风一吹,在札兰丁的眼前摇来荡去,树底下一层细细的草芽在旧年的枯草墩上钻出胆怯的叶尖,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混浊的黄水从坝里打着旋流过,宽阔的河面上偶尔还有船只从上游顺水而下,而上行的船则需要有人在河边拉着纤绳拽着船走,来到这里不长时间,札兰丁已经几次看到这种情况了。这会儿河道里没有过往的船只坐在这坝顶上下能看出老远,空荡荡的河道里只有混浊的黄水在奔流着几只衔泥的燕子飞来又飞走了。回头再看看坝外面的田野也没有人影,这是一年当中少有的闲在季节,小麦刚刚返青,那一片片没有种上小麦的地块裸露着土坷垃,不知道原来的主人想种些什么,现在的新主人一多半是刚从蔡城前线下来的兵丁,还不知道这庄稼怎么伺候,听回来的百姓讲现在还不到春播时节,大家也就无事可干。札兰丁只好任属下躲在小院里睡懒觉,或是聚在一起聊天拉呱,头顶上大大的日头悬着,谁也不愿意出来转悠。
札兰丁自己坐了一会儿,就觉得无聊得很,他往树干上一倚,懒洋洋地看着空旷的四周,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离开了战场,离开了那终日厮杀、奔突的生活,他忽然觉得倦怠下来,有时晚上睡不着觉,而到了白天又迷糊糊的。战争结束了,伊斯玛仪预料的下一场战争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打起来。蒙古人没有解散或是遣散探马赤军的意思,他们把探马赤军摆在黄河两岸长长的地带,并没有把那些缴获的战马留下来,而是带回了蒙古高原,很明显取得是一个守势。这些兵丁平时要在这里自给自足,战时就要拿兵器,这是一步很高明的棋子。可是对于这些为他们南征北战厮杀了近十年的士兵来说,未免有点过于残酷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前几日,别的小队有一个兵丁想跑回中亚去被蒙古人抓住了,他们把他五花大绑押着在各驻屯地示众,有些回回兵丁就很不服气,可是敢怒不敢言。
札兰丁又想起了自己的心事,该去接阿茹娜了,反正走不了了,那就随遇而安吧,把阿茹娜接来,按伊斯玛仪的说法,这里比别处养人,那就此落地生根也许就是真主给他们安排的前定。
唉———
札兰丁长长地叹出一口气,顺着柳枝间筛过的阳光看了看天,就要到中午了。他站起身,拍打一下身上的沙土,又抬头四下里踅摸了一会儿,仍不见一个人影,就悻悻地背着太阳回村去了。
过了没几天,札兰丁去找巴雅尔,巴雅尔倒也痛快,给他办好了回蒙古的一切手续,并告诉他由此到哈拉和林老营最近的道路:由此北上到幽州,再取正西北方向二百里出宣德府,就到草原上了,然后一路朝西北扎下去就不会错。而此时的札兰丁已经有点按捺不住,拿到令牌,他回头把驻屯的事务交给伊勒纳赤丁代理,就急急地打马上路了。
从驻屯地往北,有许多条河流拦着去路,要不札兰丁第二天晚上就能到达幽州,他这会儿真的是归心似箭了,一路上不停地甩动着马鞭,他的马掠过一个个村庄,在绿油油的麦田中间的大道小路上疾驰着,可是每道河流都让他颇费一番踌躇,他不得不为寻找渡口伤脑筋,有时会耽误半天的路程,即使找到渡口,那里都有蒙古士兵把守着,严格盘查着过往的行人,札兰丁尽管手续完备,也得耐心地解释一番。这一来,札兰丁就不得不在路上耽搁更长的时间,直到第五天,他才牵着马住进了幽州城外的一家驿站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