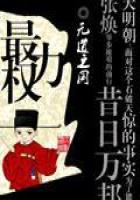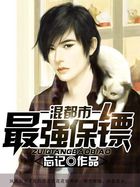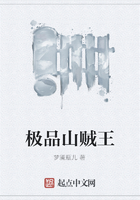站在时光的后面,我看到两万殇魂在宽阔的长江之上,遥远地浮荡,有了书生气十足的伤感。我甚至胡思乱想,假如我是赵炅,假如我是张馀,假如我是白继赟,是不是可以免去这一场屠杀?我没有找出可以免去屠杀的可能。大宋太宗赵炅先生,必定要维护大宋帝国;大蜀元帅张馀先生,必定要破毁大宋帝国;而白继赟必定要放出辣手,杀戮破毁者。当夔州危急时,各自都已经没有选择。吾土吾民,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就在致力于“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圣贤之完整气象在此。而这种理念、这种气象,必定是以天地之大德为形而上背景的。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道德是——敬畏生命。所以《周易》要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所以《尚书》要说:“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所以《论语》要说:“焉用杀!”所以《孟子》要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当吾土吾民种种杀戮连绵不绝时,我与时下“制度论”者的不同思考是:是什么样的邪僻力量在阻遏“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在妖魔化传统圣贤?优良“制度”并不能免去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也不能免去杀戮一样。但优良“制度”从不演绎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从不演绎杀戮一样。因此,“制度”与“圣贤”都不是杀戮之因。那种将历史上的杀戮推给“制度”或“圣贤”的意见,逻辑上都是荒谬而又浑浊的。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与罗马制度或奥斯曼制度无关,他们的制度并没有规定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也与西方历史上的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无关,西贤也从未有过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的理性推演。吾土吾民历史上的杀戮,也与“制度”或“圣贤”无关。杀戮,犹如历史若干重大事件一样,它的呈现,是“偶然”的,是此前多种力量“耦合”的结果。预见杀戮,并同时推演杀戮,太过于邪恶。白继赟、赵炅与张馀,都没有事先即可预知“杀戮两万人”,并推动“杀戮两万人”的理性动因。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在已经预知杀戮人数时,启动杀戮机器,那就是纳粹以及其他极权主义魔鬼。
蜀民两万,殇魂飘散,走入虚空,白继赟立功。
当他将杀戮报告,包括“夺得舟千余艘,甲铠数万计”,汇报给朝廷时,他得到了嘉奖。
但太宗网开一面,下诏言“两川军民被李顺胁众诖误者一切不问”,整个巴蜀,在“李顺之变”中,被李顺借着神秘力量欺骗而趁起的军民,一概不追究、不拿问。当“群盗”溃散,纷纷走入山泽自保时,太宗又下诏,要各州“招诱”,并“倍加安抚”。太宗,为这一场共同体之间的杀戮注入了一丝温情亮色。
查道戴枷督税
太宗一直坚持“招抚”政策。
巴蜀乱后,太宗曾派出使者,访问川、峡诸州的治理地方合格优秀的人物,当时就有知夔州袁逢吉、知忠州邵烨、知云安军薛颜、知遂州李虚己、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称职”上报朝廷,太宗都分别给了他们诏书奖谕。
内中一个通判查道,是过去南唐名臣查文徽的孙子。他做了太宗朝进士,在一个县城做尉官时,收入低,但性情廉介,与妻子甘苦与共,采集野菜与杂米煮粥“疗饥”而已。当地要办理地方租税,几个县吏不得力,被州官招到州郡,上了木枷,让他们回去。其他的县官在回去后,将木枷脱掉,只有他还戴着,而且还戴木枷下乡督税。乡里富民试图贿赂他,以酒肉招待,他不吃,还杖责富民。于是其他民众看到,就很惊讶,于是将拖欠的租税缴足。
转运使樊宗古知道他的节操德行,就打算向朝廷推荐。查道推辞,要求举荐主簿叶齐。樊宗古说:“我也不认识叶齐啊!”查道就说:“公如果不推荐叶齐,我查道也不愿意被公所推荐。”樊宗古不得已,同时推荐了两个人。查道被改为光禄寺丞、直史馆。
不久,查道从遂州调动到果州(今属四川南充)做知州,正赶上蜀中民变基本平定后的零星反抗。有个变民首领何彦忠集结了二百余众,在果州一个叫大木槽的地方,打家劫舍。诏书招抚没有成功,于是地方都请求发兵平定。查道说:“彼惧罪,欲延数刻命耳,其党岂无诖误邪?”他们不过是害怕治罪,打算延缓几天的活命罢了。其中能没有被欺误、胁迫的人吗?于是,他换了普通衣服,一匹马,几个仆人,不带兵器,直接到了变民的驻地,将太宗的诏令陈说一遍,并耐心讲解了大宋的宽大政策。有人认识他,就说:“这是咱们的郡守啊,他可不是害我们的人啊!”于是纷纷放下兵器,跪在地上请罪。查道给他们每人都发了赦免的证书,让他们回家去种地。
查道将此事通过驿站报到朝廷。太宗很高兴,史称“赐诏书奖谕”,颁赐诏书,奖励慰勉了查道。
张馀逃脱,拒绝大宋“招诱”,继续组织力量与大宋对抗。
李顺其余各部也大多拒绝了大宋的“招诱”,两川多个州郡,还在战火中。
变民余部数千人来攻取施州。在知州李鹏的指挥下,施州指挥使黄希逊的儿子黄文卓、黄文范、黄文战,以及兵马使黄延霸,率领城中丁男只有百余人,大多手持木棍,打开城门与敌众搏击,居然擒获百余人,余众大多被赶往江水之中溺死。
又一队变民约数万人来袭取广安军,被峡路雷有终行营击破,斩首五千级,生擒三十人。接着,雷有终又派出主力,在嘉陵江口杀获两万余众。再回师,在合州与宋师友邻会合,破敌万余人,斩首五十级。几天后,雷有终进入成都。这期间,各州郡小股敌军时聚时散,但大多被宋师平定。
王继恩谁都对不起
平蜀,王继恩立功。
王继恩是四朝宦官,服务于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他还有一位张姓的养父。但这五个人,他谁都对不起。
后周时,他以张姓之子张德钧的身份,阉割后进入后宫,服侍大帝柴荣。赵匡胤践祚后,他又成为赵氏宫禁的宦官。江山易色,他没有任何表示,直接投靠新主,对不起故主周世宗。
太祖时,他成为宦官班首,第一大太监。但在太祖死后,皇后要他去找皇子,他却去找皇弟。于是,太宗即位。他让太祖一系在整个北宋期间,与帝位无缘,对不起故主赵匡胤。
太宗时,他升官发财,带兵打仗,获得生命中最高荣誉和成就。但太宗已经定下传位于赵元侃也即宋真宗,他却试图改变这个格局,密谋拥立已经“疯癫”的赵元佐(一说要拥立太祖的孙子赵惟吉),对不起故主赵炅也即赵光义。
真宗时,知道他试图变更继承人,开始并没有给他治罪,但他不思悔改,继续与同伙结党营私,露泄宫中隐秘之事。真宗这才将他发配外地。他也对不起宽宏大量的新主宋真宗。
养父张氏好歹将他抚养成人,到了太祖时代,他做了“内侍行首”,也即大内总管,要求回复本宗,不再姓张,改姓王,对不起养父。
王小波李顺之变,他带领大军入蜀,平定乱局,有功。
太宗之所以肯于让一个宦官带兵,还是对他有信任。他拥立太宗即位,这是一件泼天大事,也证明此人确有某种决断能力,为太宗所赞赏。此前,王继恩也曾在太祖麾下平定江南等战事中表现不俗,所以,太宗继续起用他参与军事行动。王继恩也渐渐开始“恃宠”而“生骄”。
后宫与宦官不得干政
从汉代以来,中国帝制政制就有一条经验教训: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这类人最接近君主,一旦干政,往往可以左右政局。又因为这类人所有的政制干预,并没有经由宰辅廷臣的议事,甚至故意绕开宰辅廷臣,这就往往要诉诸非光明手段,构成一种与“天下为公”政治根本总诉求完全背离的程序不公——而程序不公,往往即导致事实不公。政局由不公而生紊乱,由紊乱而生变乱,由变乱而生权力非正常更迭,于是,皇室内部杀戮,以及由外部权臣以平定皇室杀戮而展开的杀戮,屡见不鲜。而杀戮中改朝换代的所谓“兴亡”,没有例外地将殃及民生。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原因种种,其中直接原因,往往多因后宫与宦官干政而起。不讨论后宫与宦官干政的政治发生原理,从已经看到的历史演绎而言,这是一个经验事实。
所以,历来比较明智的君王与大臣,往往都要为之设防。
王继恩曾推荐文人潘阆做官。太宗开始答应了他。但潘阆得官后,很快流露了他的“倾险”,也即用心“险恶”的特点。他曾多次劝王继恩要太宗“立储”,册立太子。那时候,太宗还没有正式册立儿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但赵元侃名望已经很高。潘阆对王继恩说:“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指的就是赵元侃。潘阆的意思是:如果赵元侃当了皇上,因为没有“我们”的拥立之功,所以不会感谢“我们”。要想让未来的皇上感谢“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要在诸王之中拥立一个没有希望当皇上的人,如此,则“我们”才有拥立之功。这一番话,说得王继恩迷迷糊糊,认为大有道理。然后他弄明白了这个“买卖”的意思,开始有了册立东宫的进言。史称“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王继恩讲述了一番拥立某位亲王的道理,弄得太宗很有点迷惑。
太宗也许约略听到了潘阆的狂悖,也许没有听到;但就在他答应王继恩给潘阆官做的时刻,应该是想起了“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贬黜王继恩,但将任命潘阆的诏书追了回来。这就等于做了一个姿态给王继恩看:你,不得干政。
宣徽使与宣政使
平定“李顺之变”后,王继恩作为招安使,前线总司令,当时朝廷讨论封赏时,中书宰辅和诸臣,都认为他有功,议论给他一个宣徽使来做。宣徽使,是宣徽院的主任;宣徽院掌管内侍户籍,略相当于中央机关人事局长;又掌管祭祀大典,略相当于文化部长;还掌朝廷会议、宴会等,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由来已久,唐、五代就有设置,一般还就由宦官充任。但太宗觉得王继恩做这个不合适,他说:
“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
他认为这个职务很容易走上“执政”,所以不同意。但可以给他一个别的官职来做。
但宰辅认为王继恩平蜀功高,不这样封赏,不符合封赏的规章制度。太宗发火,深深地责备了一通大臣。然后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论如何处理。最后议定专门设立一个“宣政使”给王继恩;与此同时还设立了“昭宣使”,都是宦官中的高级品阶,正六品,但“宣政使”班序在“昭宣使”之上。另外给王继恩一个“遥领”防御使。
至道二年(996)春,又有布衣韩拱辰到朝廷上言,认为“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止得防御使,赏甚薄,无以慰中外之望”。“秉机务”,就是要执政。太宗闻言大怒,认为这位韩拱辰先生“惑众”,将他“杖脊黥面配崖州”。
大臣和庶民要求封赏王继恩,都有“上怒”,太宗大怒的记载。浏览太宗一朝,看他回应言事臣庶,很少发怒的记载。这事发怒,有意味。
太宗一如既往地保留了“曲突徙薪”的智慧,这就消弭了“焦头烂额”的可能。宋人吕中评论王继恩平蜀事,颇精彩:
莫难于除盗,尤莫难于盗已去之后。故既命继恩以讨之,复命张咏以抚之,始威终惠,两得之矣。抑继恩宦者,使之掌兵,得无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继恩虽有功而不敢骄,虽不与宣徽而不敢怨,太宗盖有以处之也。其与童贯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无以制之之道异矣。使当时不知所以制之,愚恐无夷狄之骄,亦必有宦官之祸矣。
平蜀之事,没有比扫除盗匪更难的了;但是更难的是扫除盗匪之后。所以太宗开始命王继恩征讨盗匪,后又命张咏抚慰川中,开始于凌厉之兵威,终结于和惠之仁政,两个方面都有成果。但王继恩是个宦者,要他掌兵,难道不会陷入唐代那样的宦者掌兵左右天下局势的弊端吗?但是考察下来,王继恩虽然有功,但不敢如唐代那些宦官似的,对上傲慢;虽然不给他“宣徽使”的职官,但他不敢发牢骚。太宗一定是有办法处理这事的,太宗的办法与后来徽宗时,童贯手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没有办法驾驭他,完全不同。假使太宗当时不知道如何统御王继恩这样的宦官,恐怕即使没有夷狄的骄狂扰华,也必有宦官的骄狂祸华了。
追回任命潘阆的诏书,就是制御宦官干政的办法。后来又派出另外一个大内宦官卫绍钦前往川中与王继恩“共同带兵”,等于在分权。更在川中大致平定后,立即任命张咏治蜀,而不任命王继恩治蜀。川中撤兵前,又派出张鉴、冯守规带着空白诏书,分掌原属于王继恩的临时任命权。有功之后,不授他执政之始的宣徽使,而另外特设一个“宣政使”职官;“防御使”的军职也只是遥领,而非实际差遣,凡此种种,都是太宗“曲突徙薪”,有意处置之道。王继恩之所以没有成为童贯,原因在此。
有人认为“宣徽使”“宣政使”不过一字之差,太宗在此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实质差不多。这个意见没有弄懂太宗此举事实上含有控驭之道。“宣徽使”由来已久,职权相应,其权,联系宫禁与中书最为便捷;而“宣政使”则是临时设置,有职无权,若无具体“差遣”,等于无事可干,很大程度上属于荣誉职称。看上去与“宣徽使”是一字之差,但就是这一字之差,其“名”不同,其“器”也不同。“宣政使”不见于宋之前,玩笑一点说,犹如“弼马温”不见于各类职官表,因此这属于不承认宦官进入大宋传统职务的一种权宜性设计。
王继恩在蜀,手握重兵,到处摆威风。宴饮取乐之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倒也罢了,还要奏乐。他爱下棋,还备有专人负责带着棋盘棋子。所以上行下效,侍从们也一个个威风凛凛,恣意作恶。平叛的官军,成为害民的兵匪。
所以王继恩平蜀,有功,也有罪。
陷名将马知节于死地
王继恩在川中,还有一大劣迹,挤对名将马知节。
马知节有父风,他的父亲马全义在太祖一朝作战勇猛,马知节更有全局观念。有一年,他知定远军(今属河北东光县),当时有议论,定远军储粮多有霉变,因此要调发河南十三个州的民夫转运粮饷,河北转运使樊知古负责此事。当二人商讨此事时,马知节提出:
“定远军兵士不多,但粮食还不少,将腐烂变质的部分簸筛干净后,估计还能得到十之六七。”
樊知古接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获得可食用的粮粟五十万斛,于是分发给各个要塞,省去了河南十三州的一场转运。
马知节执法也严。
当时有辖境庶民,多走入要塞,躲避契丹入寇。但他的部下有人偷盗妇女首饰,被军中护军也即指挥官发现,鞭笞一顿。马知节知道后,认为此刑过轻。他说:“民避外患而来,反罹内寇,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庶民躲避外患而来,不想到却遭遇内部盗匪!如果这个可以宽恕,那怎么让下属严肃军纪?当即命令执行军法,斩首。
在川中平叛时,王继恩很是傲慢、托大,喜欢要人逢迎他。但马知节不买账,不愿意讨好他。王继恩于是就有了故意陷害的举动。
他命令马知节去守彭州,只给他老弱兵卒三百人,原来属于马知节调遣的精兵都调回成都。马知节知道彭州是李顺党羽一定要攻取的要害之地,多次请求增兵,王继恩根本不听。结果变民来了十万人攻取彭州。马知节带着羸弱之兵与敌人奋力拼战,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士卒很多人都已经战死。马知节长叹道:“死在贼人之手,不是壮士啊!”于是“横槊溃围出”,挥舞着长槊冲破重围出来。直到第二天,才引来援兵,再次呐喊着冲入敌阵,敌人败退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