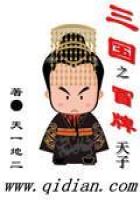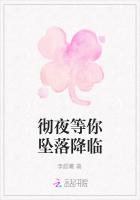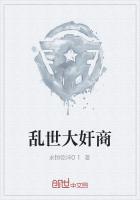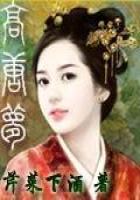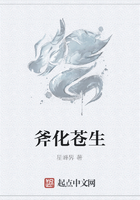至道二年(996),高丽国王王治向契丹请求联姻,契丹以东京(今属辽宁辽阳)留守萧恒德女与高丽订婚,高丽为此向契丹送去了彩礼。但不久高丽王治死了,契丹将彩礼奉还。这一年,契丹还安置了朔州的流民。
大宋则在夏天五月时,令开封府判官杨徽之等按行考察管内诸州的民田,遇到旱情严重的地方,要蠲免当年租税。
这时四川又发生民变,继李顺之变后,有乱党首领名王鸬鹚再次聚集变民四处剽掠,自称“邛南王”。西川都提举、大臣石普上奏说:“蜀之乱,由赋敛急迫,使农民失业,不能自存,并入于贼。望一切蠲其租赋,令自为生,则不讨自平矣。”蜀民之乱,是因为赋敛太急,迫使农民失业,不能继续生存,所以有人就进入到盗贼之中。期望朝廷能蠲免当年一切租税,让农民能够各自为生。如此,不必讨伐,民变自会平息。太宗答应了。石普到四川将朝廷意旨传达给变民,史称“蜀民无不感悦”,整个巴蜀安定下来。
大宋这边有人认为凤州(今陕西凤县)出产铜矿,定州(今属河北)出产银矿,准备收归国有,派遣官员执掌开矿事宜。太宗说:“大地并不爱惜宝藏,肯于出土;朝廷应该与众庶共享。”不允许官营。
这一年契丹则认为南京(燕京)一道新订的税法太重,做了减免处理。
太宗之死
到了至道三年(997),太宗在世的最后一年,只有三个月时间了,太宗还在部署边帅防御反复无常的西夏,而契丹在河西,也有党项人开始背叛契丹,契丹安排边将讨伐党项。
太宗已经病重,还下诏免除京畿死罪的囚犯,流罪以下全部赦免。
与此同时,契丹下诏给南京(燕京)要解决常年不决的“滞囚”问题。还蠲免了多项税收,如四方的流民免租税;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南京一道的欠租,全免等等。还命诸道抓住春天的时机,鼓励民众种树;并禁止诸军官在违背农时的季节田猎。
大帝太宗赵炅,临终前听到的来自契丹的消息是:西夏李继迁再一次背叛大宋,投靠契丹,被契丹封为西平王;契丹大将韩德威击破党项,党项请求归附契丹;于是,契丹向西开拓疆域更为辽远。
至道三年三月壬辰,史称“帝不视朝”,太宗病重,已经不能在朝堂会见诸臣。第二天,癸巳,帝崩于万岁殿。
这一天是公元997年5月8日。
太宗遗制
太宗赵炅,在大唐帝制继承制度紊乱之后,在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与寇准协议定立太子,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顺利交接做出了基础性安排,最后在大臣吕端的决断之下,保证了这个安排的顺利施行。于是,大宋没有乱,没有回到乱唐,更没有回到五代。
但这件大事,险些坏在宦官王继恩手上。
王继恩即使有多少恣横之过,如果不是最后试图改变太宗册立太子之事,也许他这一生会有另外的功过评价。
太宗由“金匮之盟”的“兄终弟及”模式,回归于“宗法大礼”的“嫡子继承”制度,为帝制时代的权力再分配,承担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当这种遗制作为天下已知的规则已经出台,再试图破毁这种规则,就要承担更大的道德风险。事后看,王继恩试图改变太宗遗制,拥立宋真宗赵元侃以外的亲王入继大统,那是绝大的政治冒险,同时也是对天下、对士庶、对社稷、对皇室、对赵元侃与赵元佐,都缺乏责任担当的悖逆之举。
此案,王继恩很愚蠢。
他以为当初可以决定由谁出任第二代帝王,也就能够决定由谁来出任第三代帝王。他不明白的是:第三代帝王已经由宋太宗赵炅、社稷臣寇准,君臣商议决出,已经昭告天下,已经行使了册立太子的大典,已经经由程序规则告知天地宗庙神灵士庶,形势与当初太祖留下权力空白全然不同。势变,而伎俩不变,利欲熏心下的程序变更,必是祸及自身的愚蠢。
赵元侃被册立太子之前,还在做襄王时,已经有不低的“人望”。像太祖太宗践祚前后,坊间开始流布神奇传说一样,赵元侃也有自己的传说。
“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
有一位屯田员外郎名叫杨砺,几十年前,曾梦见一位“来和天尊”。端拱元年(988)二月,杨砺又为库部员外郎,并到襄王府做记室参军。他初到襄王府吃了一惊,原来他看到的襄王赵元侃很像几十年前他梦中所见的那位“来和天尊”。
杨砺乃是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大宋建国第一年的第一个状元。由此人来推演宋真宗的“神迹”,在士庶中,影响颇大。
此人很像太祖时“善天文占候之术”的神秘家苗训。陈桥兵变前的黄昏,苗训仰观天象,发现“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太阳上边还有一个太阳,久久地互相叠加摇荡。军中“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开始时,“天有二日”成为一种蛊惑力量。
杨砺关于“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在真宗皇帝做襄王时就有了江湖传闻,杨砺是始作俑者。这类说法固然有“创作”的可能,但也预表了士庶对真宗的期待和拥戴。所以,真宗一朝待杨砺很优厚,犹如太祖一朝待苗训很优厚一样。
但真宗皇帝并不了解杨砺的履历,他做了皇帝后,有一次问杨砺:“爱卿你是哪年及第的啊?”杨砺“唯唯”不回答。后来知道他是大宋帝国开国以来的第一名状元,真宗不免有点“自悔”,认为不应有此一问。但对杨砺不愿意自吹自擂也甚为钦佩,所以,对他更为敬重。
杨砺年六十九岁时,病逝,真宗甚为哀痛,他对群臣说:“杨砺耿直廉介而又清苦,朕正要大用,不料忽然谢世。”于是冒雨前往杨砺家中吊唁。到了他家住的小胡同,车驾没法进入,真宗就下车,踩着泥泞小道,曲里拐弯地进入杨砺家中,叹息哀悼了很久。
太宗要册立太子,也是经由了反复斟酌。但是有人提议早立太子时,他又发怒。很多人以为他留恋皇权,不愿让渡。但事实是,斯事体大,他在从诸王中慎重选择,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淳化二年(991),他曾与近臣说:“总是有人上疏讨论建立皇储之事。朕还是很读了一些书的,又亲眼见到前代的治乱兴衰,怎么会不将这么重要的大事放在心上呢?不过是因为近世以来,世风浇漓,人心难测,如果建立太子,那必须要让百官认同,太子从东宫到践祚,要有程序,就像百官升迁。现在诸子年轻,还没有成人的性情。所以我给他们各自安排了良善之士作为辅佐,乃至于他们的僚属,我都要亲自拣选,目的就是不让奸巧险佞之辈在皇子左右。他们的读书、听讲,都有课程安排。等到他们成长起来,朕自有裁制。为何讨论这个事的人就不懂我这番心思呢?”
三年后,有一位崇仪副使名王得一,他是一位道士,常到禁中与太宗讨论国事,往往就到夜半。他敢说话,说到外面的舆情,有一次就赞誉襄王有“人望”,请太宗立他为太子。太宗心动,不久,又与寇准一番话,定下太子。于是以襄王赵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就是帝制时代,大宋由皇子升迁为帝王的一道程序:改封王,做京师令尹,以此历练从政经验。
到了至道元年(995)八月,正式册封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
从唐代天祐年间以来,中原多故,乱世中,没有来得及施行册立皇储,于是这个大礼停废几乎有一百年了。太子礼施行隆重而又简捷。太子赵恒处处守礼,甚至在做了太子后,还上书要求一如既往地与诸兄弟一起朝见父皇。诸臣参贺时,赵恒也总是走下台阶答礼。温文尔雅,谦逊冲和,他的做派为人所赞赏,史称“中外胥悦”,朝廷内外都很欣慰。
王继恩试图改变“人望”如此之高的皇位继承人,等于在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实属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
吕端大事不糊涂
至道三年(997)二月,太宗病重,文武百官都到崇政殿问候起居,从皇太子、亲王,到诸臣,都到佛寺去修斋,为太宗祈福。
就在这个期间,宣政使王继恩决计谋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他实在担心现任皇太子赵恒的“英明”。于是找到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来商议“大事”。几个人就经常说一些太子的坏话。恰巧太宗的李皇后也不怎么喜欢太子,而喜欢赵元佐。赵元佐和太子赵恒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李贤妃的亲生儿子,李贤妃已经死去,李皇后大约是看到赵元佐的疯癫,动了女人家家的恻隐之心,所以心理天平总是倾向于赵元佐。这个微妙的情感被王继恩捕捉到,他以为这也许就是一个机会。于是在太宗病重期间,与李皇后故意不安排赵恒在太宗身边。
但这个微妙的安排,却被“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到禁中问安时看在眼里。他承认并赞赏寇准推动赵恒为太子的宏猷。现在太宗病重,太子却不在身边,此事蹊跷,于是就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字“大渐”,令亲吏送给赵恒。“大渐”的意思是“病重病危”。吕端传导的信息是:父皇弥留之际,太子务必前来问安侍奉。但这位太子还是有了疏忽。
太宗在亲王诸臣的祈祷中没有痊愈,反而病情加重,无法推测太宗患有何病,他的直接死因,一般认为是昔日箭疮发作。
太宗死时,赵恒不在身边。
王继恩跟李太后商议后,决计到中书去召宰辅来议论继承人问题。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现在李皇后和王继恩要将问题提出来,是期待侥幸获得宰辅支持。而当时最富名望的宰辅就是吕端。他们要议论继承人问题,吕端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必须重视。于是,王继恩硬着头皮来找吕端,说是要“议所立”,讨论一下立什么人做皇帝。
根本无须“议”的事,王继恩要“议”!吕端顿时感到“严重的时刻”来临了。他也顿时明了了眼下的格局。于是将王继恩带到书房,说是让他看看太宗以前赐给他的种种“墨诏”,亲笔诏书。而后,将他锁在书房中,派人看住不得外出。自己匆匆赶入宫中。
李皇后见宰辅来到,对他说:
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
皇上驾崩啦。按照宗法规定:长子应该有第一继承权,这是合乎礼范礼法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您看怎么办?
李皇后这十四个汉字,分量不轻。她试图按照个人喜好,在王继恩的推动下,“立长”,也即拥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从宗法继承视角看问题,不为无理。但赵元侃也即赵恒已经成为制度规定的继承人;赵元佐则已经疯癫,或假作疯癫,常年没有军政作为;更重要的是:赵元佐并不希望践祚——他对四叔赵廷美之死一直耿耿于怀;更对父亲所作所为而导致的大伯赵匡胤后裔无缘于帝位心怀不满。在这样背景下,拥立赵元佐,实属多事。
但吕端的回应分量更重,他说:
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论!
先帝太宗之所以生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这个入继大统问题。哪里还容得下有其他不同的册立意见!
李皇后闻言,知道宰辅这一关过不去,那就没有了希望。于是,默然不语。
当天,赵恒在灵柩前即位。
但灵柩停在大殿上,皇后与皇帝一起临朝接受诸臣拜贺,前面置放了一道门帘。吕端在阶下肃立不拜,请求将帘子卷起来,让百官看到赵恒。他担心王继恩等人会将生米做成熟饭,万一帘后不是赵恒而是其他人,诸官拜贺后,再试图改变格局,又是一番凶险难测的麻烦。李皇后答应了吕端,卷帘。吕端走上台阶辨认,确认帘后的继承人就是赵恒,这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拜呼万岁”。
于是,大宋有真宗皇帝。
赵元佐不见宋真宗
有意味的是赵元佐。
真宗很敬重这个大哥。几个月后,以赵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再次被复封为楚王,并允许他在家养病,可以不上朝。但真宗要去赵元佐府上看望他时,赵元佐说自己有病,坚决推辞不见,并说:“虽来,不敢见也。”即使是皇帝你真的要来,我也不敢见你的!从此以后,兄弟二人终生没有再见。
赵元佐如此反对太宗、反对真宗,都是涉及皇位的大事,但是太宗也不过将他贬黜、真宗则不但不贬,更多次存问。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赵元佐一直活到仁宗时代,一直很安全。卷入权力问题,平安生存,这在历朝历代中,是很罕见的。大宋帝国三百年,皇室、大臣、士大夫、庶民,是仇恨较少、戾气较少的时代,各类人等,生存在这个时代,很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王继恩自知阴谋不成,局面危险,于是又秘密委托一个大臣胡旦,在朝廷上为自己开脱,并做了一番褒扬之词,还组织了文人给他写“颂诗”。但真宗与吕端等人已经知道了他们往日的阴谋,这事不能装糊涂,于是组织了“王继恩专案组”,调查他的劣迹种种。
王继恩遇能吏
王继恩遇到了一个能吏,名叫魏廷式。
此人自年少时就对“法学”深有体会,太平兴国五年(980)中第后,“释褐”为地方的司法官员“法曹掾”。太宗晚年,他被召入判大理寺,成为国家最高法院的院长。真宗初立,即命他为吏部员外郎,后改为刑部。王继恩的案子就由他来审讯。魏廷式有“严明”的口碑,他刚果敢言,但性情也有“倾险”的一面,喜欢中伤诽谤。所以士君子都怕他的利口而鄙视他的行为。由此人来审讯,王继恩想推脱,难度太大。所以审讯很顺利,史称“逾宿而狱具”,一个晚上审理结果就出来了。王继恩的罪责当然就有“谋逆”一项。
这罪过,要是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王继恩之流就是一个大罪,必遭“族诛”,但真宗皇帝只给予贬官、贬黜的惩罚。王继恩降职,责授右监门卫将军,逐出京城,到均州安置,而“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结及通书疏者,一切不问”,朝廷内外的大臣僚属,曾经与王继恩有交结、密通书信者,一律不调查不审问。这事可以做成一场大狱,但在真宗时代,啥事没有,就这么过去了。
帝国有惊无险。
王继恩被贬后,家产被没收。清理他的财产时,发现了很多从巴蜀带回来的“僭拟之物”,也即不应该属于他使用的皇室器具。
王继恩第二年死在均州。
真宗派遣使者,将其家属接回京师,借给他们官舍居住。又过了二年,允许家属将王继恩灵柩按照他们的意愿归葬。又过了十来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还特意下诏,追复了王继恩原来的官职,并给他的家属后人白金千两。王继恩的养子王怀珪,这一年也转入内高班,成为有高级职称的宦官。
有一部书名《挥麈录》,总四部,其中一部称《挥麈余话》,记载了王继恩试图拥立的不是赵元佐,而是赵匡胤的孙子、赵德昭的儿子赵惟吉。
说太宗时,司天监苗昌裔奉命前往洛阳之郊,为太祖赵匡胤的陵寝选择风水宝地。等到安葬太祖完毕,苗昌裔带着陵寝的总管王继恩登上山巅,指画周边风水形势,并对王继恩说:“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意思就是,别看现在太宗在位,但以后皇位还会回到太祖一系。王继恩记住了这句话。等到太宗“大渐”之后,他就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使赵、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赵惟吉。后来事发,诸人遭遇贬黜。
据说到了神宗时代,李昌龄的孙子李逢知道苗昌裔的预言,还在煽动赵匡胤的后裔赵世居谋反。那是一场大狱,容当后表。甚至到了靖康年间,赵德昭的五世孙赵子崧还在“剽窃”这个说法,与门人歃血同盟,准备恢复太祖一系的帝位。后来知道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入继大统,这才不情愿地罢休。宋高宗不忍心暴露这种事,找了个别的借口,将他贬黜。
太宗的忧心与焦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