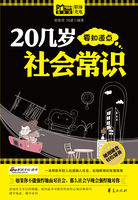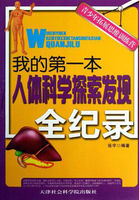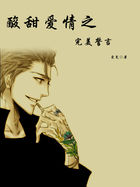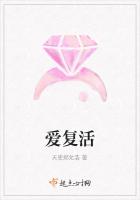至于李零,他是怎么用的这“丧家狗”三个字?能不能用呢?我再来猜一猜。第一,他肯定孔子一生失落的遭遇这事实。李零说得很清楚:“我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史籍记载这个活孔子、真孔子确实一生的的确确“心想事不成”,他一门心思寄希望于统治者用他,可却不为统治者所用,很是失落,失落到产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的地步了。要李零“‘瞒’和‘骗’”,他是绝对不干的。他自己读《论语》,教学生读《论语》,根本特质所在就是要打破对于孔子的“‘瞒’和‘骗’”。复活孔子,复活一个真孔子。第二,他倒是从积极的方面看孔子的“欣然”和“笑曰”。很是“同情地理解”。所以他在封面上标举:“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他把孔子只当作知识分子看,而不深究孔子这种知识分子的追求。这种标举很得到认同。在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有先生就说他自己也是“丧家狗”;谁谁谁也是“丧家狗”。这种积极的“同情地理解”是并不离谱的。孔子无疑怀抱理想,孔子无疑是终其一生没有找到精神家园的人。他的一门心思跑官,也是时代使然。是故,虽然孔子心中的“精神家园”是有主子的,也不妨给予同情。正因为这一点,我不采取这种泛论。我看重孔子周游列国,寻找一个主子来实现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根本特质,看重他不为统治者所用,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一点。如果孔子不希求统治者用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何尝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呢?孔子以降,儒家之所以逃不掉“丧家”的命运,根本在他要说动统治者,重用他来做“王者师”,恢复他所理想的“东周”的气象。而他们拉社会后退的那一套,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不取的;也为历史所不容。儒家,新儒家,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家,“儒家社会主义”,都不过让我辈再来“听说梦”罢了。鲁迅说:“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我是相信鲁迅的。我相信鲁迅对于孔子的评论:“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枉。”最近一个例子。有地方提出“不孝不能当干部”,可东汉的老百姓就有民谚:“举孝廉,父别居。”民众有民众的眼光。
关键还在于:不能再搞“孔子说得,李零辈说不得”的尊尊长长那一套了。不能再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一套了。不能弘扬孟子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那一套了。二十一世纪了,还不能来一个“百家争鸣”吗?只有对于孔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才可能认识孔子;只有把孔子放到他生活的历史时代,才可能认识孔子的伟大,和他的精辟的言论,不至于因人废言,把孔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鲁迅是批评孔子的,因为孔子是个“治民众者”,是为权势者设计治国的方法的;而且直到他生活的时代,孔子还被当作“敲门砖”,权势者及其帮忙者帮凶者还要用孔子来救中国。但是,鲁迅对孔子是采取分析的态度的。他不仅说过:“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还赞同过孔子不少言论。如:“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这绝不是孤例,这里不一一罗列了。看一个人,知人论世,一要看他的根本特质,二要不因人废言,这才庶几近之吧?
2007年7月17日
究竟谁在误说?
秦璜
今年第四期《咬文嚼字》刊有杨宏着先生的一篇短文《琼瑶误说科举》,指出了琼瑶小说中的两处差错,同时概括介绍了中国明清时代科举考试中的有关知识。六月十一日,有一位“长期从事文字编校工作”的黄鸿森先生挺身而出,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琼瑶误说科举)有误说》一文,声称《咬》刊的文章中也有误说。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
据我所知,《咬》刊自创办以来,既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又敢于向自己“开炮”,并不讳疾忌医。我很想看看《咬》刊因何被咬。而我本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曾经有所涉猎,至今仍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为此,在读了《咬》刊上的杨文之后,紧接着拜读黄先生的大作,然而读完以后却大失所望。套用《中国新闻出版报》编者按上的一句话便是:黄先生“对科举制度似不甚熟悉”。他一连“咬”了几口,却咬得不是地方。
第一关于“童试”的范围。《咬》所刊文章说:“按明清科举制度,先要通过地方县、府两级的童试,成为童生后,再参加学:举行的:试:试由学政主持,录取者即为生员,通称秀才。”黄先生说“童试”不是两级而是三级。他引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科举制”条说:“童生要取得生员资格,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试,总称童试。”杨文只说“要通过地方县、府两级的童试”,把“:试”排除在外,因而成了误说。
黄先生的这种断言,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些历史类辞典(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确有把县试、府试和:试三级考试统称为“童试”的,但这仅仅是某些学者的一家之言,其实颇有可议之处。比如着名科举史专家金铮教授便持有不同意见,他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五章中写道:“科举发展至明、清,已形成一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唐代科举仅发解试与省试两级,而明清则有童试、: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往往又分层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金铮教授显然没有像黄先生那样,把童试说成包括县试、府试和:试三级,而是将童试和:试作为前后不同的两级考试来论述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童试”只是要取得“童生”的资格,“表明已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写作能力”,它和“:试”并不能完全扯在一起。在府、州的“学:”举行的“:试”,按照金铮教授的介绍,“又分为‘岁试’、‘科试’两级。岁试是每年举行的童生‘入学’考试,录取后即为‘生员’,通称‘秀才’。科试则是对已在学校的秀才进行考试,成绩优者方可参加下一级考选举人的乡试……”
可见,“:试”既和“童试”有关,又和“童试”有别。“:试”中的岁试参加的对象是童生,录取后即可入学成为生员(秀才),因此可以包括在“童试”之内。而“科试”的对象则是已经入学的生员(秀才),通过考试决定其能否参加上一级省城举行的乡试。这种“科试”怎么还能算“童试”呢?黄先生显然是上了某些辞典的当,把两级不同性质的考试混为一谈。
第二关于“学:”的称谓。黄先生质疑说:“什么叫‘学:’?杨文说‘……再参加学:举行的试试由学政主持……’句中的‘学:’一词有歧解,似为主办者,似为场所,且语义不明。《辞源》‘:试’条释作:‘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因学政又称提督学:故名。’同书‘学政’条(三)释作:‘清代提督学政的简称,也称督学使者、学政使,俗称大宗师、学台。……各省督学统称提督学:官名称为钦命提督某省学政。’由此可见,‘学政’虽有多个称谓,但没有称‘学:’的,所以说杨文写得不妥……”
黄先生对“学:”这个称谓否定得如此斩钉截铁,实在让人吃惊。“学政”(全称“提督学政”)怎么会“没有称‘学:’的”呢?翻开《清史稿·选举志一》,其中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初,各省设督学道,以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充之。惟顺天、江南、浙江为提督学政,用翰林官。……雍正中,一体改称学:省设一人。”(第3114页)
如果说正史翻检不便的话,那就查查《教育大辞典》吧。关于“提督学:”的释文是:提督学:①清代学官名。清初沿明制,直隶与江南、江北各设提学御史和提督学道,选用翰林:翰林出身者任之,故称。康熙末,各省提督学道均更名学:……②提督学政之衙署,与抚:平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3页)
根据以上的引录可知,“学:”之名,见于正史和现代权威的专科工具书。它有两个义项,其一是清代地方文化教育行政官“提督学政”的别称;其二是“提督学政”的衙署,即办事机构。这两个义项的内涵区别分明,怎么会引起歧解呢?《咬》刊作者说:“参加学:举行的:试:试由学政主持。”科举制度中的考试一般都是由国家机构(“衙署”)而不是行政长官个人出面组织的,这里的“学:”指的就是“提督学政”衙署,而主持考试的人则是提督学政。一清二楚,何错之有?
第三关于参加“乡试”的资格。《咬》刊原文说:“秀才能否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还要看他在科试(:试的一级)中成绩是不是达到优等。”黄先生觉得这也有“可议”之处:“秀才能否参加乡试,要看科试成绩‘是否达到优等’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王道成着《科举史话》说:‘生员参加科试,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名列前茅(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者),就取得乡试的资格。’可见,生员只要科试成绩较好就可参加乡试,并不需要‘达到优等’。”
被选送参加乡试者,应当是科试中成绩“达到优等”的生员,这一说法并不是《咬》刊作者凭空杜撰的。《明史·选举志一》说:“[提学官]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即岁试)……一、二等皆给赏……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即科试)……三等不得应乡试。”(第1687页)又如《清史稿·选举志一》说:“科试一、二等送乡试。”(第3117页)由此可见,在通常情况下,保送参加乡试的必须是科试中成绩达到一、二等的生员。所以金铮教授在其着作中根据以上规定概括为:“科试则是对已在学校的秀才进行考试,成绩优者方可参加下一级考选举人的乡试。”至于后来在某个时期由于特殊需要适当放宽尺度,把“三等名列前茅(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者)”的生员也选送去参加乡试,那只是特例而不是常例。黄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竟然撇开正史记载不谈,抓住通俗读物中的说法,在“优等”和“成绩较好”两个词语上纠缠,非要把前者定为“误说”,似乎有点强词夺理。
第四关于“中式进士”的提法。《咬》刊作者说:“明清时期所有举人均可去京城参加会试……会试取中者为中式进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后所有中式进士均参加殿试……”黄先生则认为“‘中式进士’一词,未见于史书”,自然这又成了误说。对于黄先生的这种质疑,我想反问一句:“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你黄先生没有见过的称呼,就一定不存在吗?”为了解开他心中的疙瘩,我在这里引一条清代学者的书证。俞樾(1821-1907)《曲园杂纂》卷三十八《小浮梅闲话》:“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一种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读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成德于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1673)癸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
这段引文中摘录的乾隆皇帝的“上谕”(圣旨),就提到纳兰成德既“中式举人”,又“中式进士”。这两个称谓都不是专名。“中式举人”就是“考中举人”,“中式进士”就是“考中进士”。黄先生说:“‘中式进士’一词,未见于史书。”不知道这条清人笔记转录的乾隆上谕,能不能让他改口。
第五关于会试中式的人殿试以前能否称为“进士”。黄先生说:“会试中式者,明代无任何称谓,清代则给予‘贡士’称谓……会试中式者必须参加殿试后才能得到进士称号。”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黄先生还特地引用《明史·选举志二》说:“[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在这段来自正史的引文中,谈到了三甲的等次及其称谓。这些称谓,最初确实是在通过殿试以后由朝廷公布确认的。黄先生根据正史说话,显得理直气壮。但他似乎并不了解,从北宋开始,直至明、清两代的朝“之间,人们早已把会试中式的人习惯地称为“进士”了,无需等到殿试以后。《咬》刊作者的说法完全站得住脚。
大家知道,唐代的科举考试只分两级,中央一级的考试叫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还没有殿试。殿试是在北宋初年由宋太祖创设的。开宝八年(975),在省试以后举行的殿试中,有不少省试取中的考生被黜落了。这些失意的士子,有的贫无所归,导致轻生自杀;有的甚至愤而投敌,鼓动西夏军队连年入侵宋朝,闹得边境不宁。为此,宋仁宗在嘉佑二年(1057)正式下诏:从今以后,“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燕翼诒谋录》卷五)这项规定,明、清两代承袭了下来,所以金铮教授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的第三章中说:“此后举人通过省试(明、清称会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时只排列名次之差。”参加会试中式的人,只要参加了殿试,哪怕考了第三甲的最后一名,也还能得个“同进士出身”。因此到了后来,只要是会试中式的,人们也就习惯上称他们为进士了。就拿上面所引《燕翼诒谋录》那句话来看:“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与殿试者”就是“参加殿试的人”。殿试还没有结束,是否中式还不知道,《燕翼诒谋录》的作者不是已经提前称呼他们为“进士”了吗?
最后,再举一个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傅增湘(1872-1949)的例子。傅先生是着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他在《清代殿试考略》一书中,记叙自己当年参加殿试的经历时写道:“新进士入殿,皇帝亲临,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礼仪后,礼部散发试题,进士跪受,各就试桌对策……”你看,这里叙述的分明是殿试之前和正在进行时的情景,但应试的人却都已被称呼为“进士”和“新进士”了。读了这段记载,我们是认同当年亲历过殿试的傅增湘先生的生活实践呢,还是跟在黄先生后面一起指摘他滥用“进士”的称谓呢?读者自会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