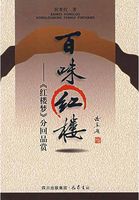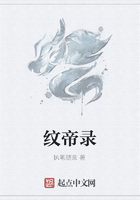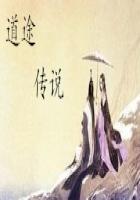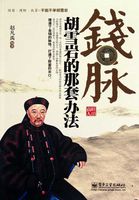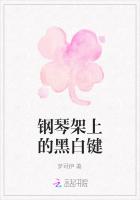一、少年壮志,投身革命
1921年我11岁,从德兴县小学高小毕业。1922年,我12岁时就读于青年会中学预备班。翌年,我13岁,正式离开父母到南昌读中学,先在心远中学就读,后就读于赣省中学。1924年,我14岁,到江西省一中就读。进入中学读书之后,我就已有读书恨少的悔过之心,一改以往不求上进之志,转为勤奋学习。除了认真听课做作业外,还会主动上学校图书馆协助工作。因此,得到了浏览群书的机会,使我大饱了眼福,读到了许多好书,满足了求知的欲望,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在学校中,我不仅仅是读书求知,还对学校中组织的讲演比赛、文体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热衷于篮球和吹奏乐器,在学校里十分活跃。尽管我投篮不在行,但拼力抢球还屡屡得手,被选入了校篮球队。我打鼓吹号都不在行,却因从父亲处学得了吹箫、笛,又被学校乐队选中。当年,我还多少有点口吃,当然口吃不严重,还参加过学校的讲演比赛,还得了奖。由于我学习成绩优良,加上热心课余活动,自然而然的被推选为学生会干部。
1924年,华中运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有湖南、湖北、江苏、河南、江西五省运动员参加。我先是参加欢迎乐队,在队中吹笛,因年小排在队尾,感到有点心酸不忍,立即退出乐队,改加入童子军队,并当上了童子军队长,穿上了学校新制的童子军军装,任务是维持运动会会场秩序。虽然会场也有军警维持秩序,但军警人数太少,只得让童子军凑数。我所在的一中队分配到司令台编辑注册组,就是在司令台和各组协助做运动器材收检、量高度、远度、检查中途犯规等项工作,还有一部分童子军则负责验票进场。由于当时没有无线电广播,比赛节目开始,司令部用传声筒发号令,很难使全场听到。有人给出主意,用自行车挂项目牌全场行走两三圈,就知道号令了。正好二中童子军队队长家里有一辆。那时的南昌自行车极少,很难看到。就由他骑单车手挂木牌绕场走。可是,牌子老掉下地来。于是改由一人骑车,另一人在后座举牌。这样,就轮到我这个最小的童子军上场了。因为,当时的中学生年龄一般都较大,我当时是年龄最小的了。我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举木牌示众,觉得好不威风。还有一件事,我是记忆犹新,那就是会上的免费供餐。童子军只是和杂役一起用餐,在一个篷帐里吃,两个铁锅菜,一菜一汤,还没有包子供应。二中的童子军队长发现了大会工作人员、运动员包括军警吃的好,四菜一汤,大鱼大肉,顿生怨恨情绪。当即和我商量,大家不平则鸣,一呼而起,不知有谁说了一声“罢岗”,童子军便统一罢工了。下午运动会开始后,童子军不守门了,群众蜂拥进场。分配在各赛场的童子军也不工作了,使比赛陷于停顿。大会主持人经过了解才知道了童子军罢岗的缘由,当即召开中学校长会议,校长们提出要改善伙食,主张虽不能和运动员们一样,但也要添加一个荤菜,加发两个肉包。于是到快散场时童子军复岗,结束了一场风波。运动会结束后发给了童子军维持会场秩序纪念镜框,学生高兴,学校领导也高兴。
1925年3月12日,“国父”孙中山逝世,举国哀悼,江西当不例外。江西省会机关、工商会、学联等众多团体组织孙中山追悼大会筹备处。学联则要组织学生参加筹备处事务工作,向各学校要求派人。那时,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临近毕业,不能外出工作,任务就落在初二年级了。当时我正是读初二,又是学生会干部,便被派到追悼大会筹备处工作,具体任务是搞登记和接待,供给中餐,经费由各组织负担。因为第一阶段是由各单位祭悼,然后再开追悼大会。这一阶段大约是半个多月。由于接待组与宣传组同在一个房间里。因此有机会与各报记者大量接触。当时,各报中有许多实习记者,年轻得很,和我相处很密切。这些实习记者我依稀记得有熊文钊、熊文铭、李志远等。由于我忠于职守,每日都早来晚走,受到他们的青睐。实习记者们还特意促我写了一篇悼念孙中山的小文章,登在江西报纸副刊的末尾,尽管当时无一文稿酬,但毕竟我的名字上了报,使得我十分得意,十分陶醉。为此,还特地买了几份报纸送给同学、父母兄弟。在此期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某一天报纸上登出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国子国孙吃国父”,讽刺江西省筹备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主持人(其中也包括学联头头)大吃大喝,耗费各单位所摊费用。我看了后认为是奇耻大辱。从此连中饭也不在筹备处吃了。实际上是这些筹委会头头,每天总有一餐在附近的小有天餐馆大吃大喝,这是一位没参加盛宴的记者所写,引发社会上大议论。我则引以为耻,是因我自己多少也参加吃过几餐。
由于进步思想的熏陶,我早在少年时期就投身了革命行列。1925年9月(15岁少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江西省团委领导下,参加了南昌青年学生运动,并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五卅”运动纪念活动、抵制日货活动。1926年参加江西学联工作。1927年参加了“八一”起义后援工作和随军南下向潮汕进军等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