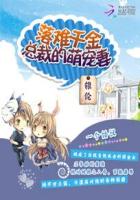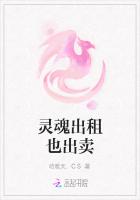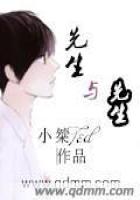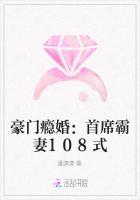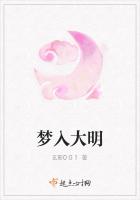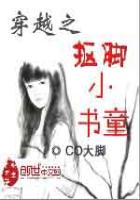第一节 鹏鸟择枝而栖——记西夏国中书令张元
张元,华州人(今陕西省华阴县人),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公元1040年)五月叛宋投夏。张元到了西夏国,不到两年的时间,官至西夏国最高行政长官中书令。“元至夏不二年,官至太师,中书令”,直到西夏天盛礼法延祚七年十二月(公元1044年)卒。
张元,原来并不叫张元,他为了达到叛投西夏的目的,故意更改其名,以引起西夏国景宗皇帝元昊的注意,所以,“既入国,二人(张元、吴昊)自念不出厅无以动听,各更其名,相与诣酒肆,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饮此’”。因此,以前叫什么名字,由于西夏史料几乎散佚湮没,无从查考,这里不进行详细考究,只通过有限的史料,了解到张元是一位才华横溢,出语惊人,智勇双全,抱负远大的人才。但由于宋朝官场黑暗和用人制度不当,致使张元的满腹经纶,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每每不得升迁,更谈不上施展才华,发挥其聪明才智。正在张元徘徊辗转之际,与宋、辽抗衡的西陲小国——西夏,为了发展壮大自己,极力挖掘和吸引各方人才,于是宋朝的一些失意文人张元等,往往由于“举子不第,往投于彼”,于是元昊将张元等失意文人“或授于将帅,或任之公卿,推成不疑,倚为谋主”。这些失意文人到了西夏国,都得到了元昊的重用。因此,史书称,元昊即位后,“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张陟、张降、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者六人,汉人就占了五人,这充分说明了元昊对“往投于彼”的宋朝失意文人的重视。张元虽然“负气倜傥,有纵横才”,但在官场黑暗和钩心斗角的宋朝,他也是“累举不第”的失意文人。虽然如此,他在离开大宋之前,仍然恋恋不舍,“过项羽庙,沽饮极酣,酬酒像前,悲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大怯恸而行。”他虽然舍不得生他养他的土地,但又无立锥之地,无可奈何之下,极其悲痛,于是在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公元1040年)五月叛宋投于元昊。
张元是一位秉性刚烈、桀骜不羁的人。在投奔西夏时,为了引起元昊的重视,就故意“更其名”为张元,毫不避景宗元昊之名讳,于是“逻者执之,元昊责以入国问讳之义”时,张元和元昊却泰然处之,竟直言不讳,说:“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这件事给元昊留下极深的印象,故而元昊听后,“闻言竦然,异而释之,日尊宠用事,后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云。”由此张元得到了赏识和器重,并委以重任,协助元昊治理西夏国。投入西夏以后,由于他知识渊博,并有非凡的才干,加之他“性喜诛杀”,而且十分地残忍狠毒,所以在他的参谋策划下,元昊为了扩大疆土,一统天下,于是就频繁发动侵略宋朝的战事。在宋夏战事中,由于“张)元好谋阴,多奇计”,因而在每次战事中,元昊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得到他深思熟虑的计谋,然后才能发兵征讨。因而史书称张元在西夏国“国有征伐,辄参机密”,而且每参必中,每计必成。逐渐地,张元、吴昊成为元昊的左臂右膀,《宋史纪事本末》卷30记载,“凡夏人立国规模,多二人教之”,在张元的策划和直接指挥之下,宋夏战争,捷报频传。譬如,公元1040年9月攻打三川口,首战告捷;公元1041年2月攻打好水川,又是大获全胜。这两次战争的胜利,使张元在西夏国站稳了脚跟,树立了威望,成为西夏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使朝野上下叹服不已。再譬如,公元1042年9月,攻打镇戎军时,元昊与张元等商议对策时,张元根据时局形势,胸有成竹,深思熟虑地分析说:“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元昊感到张元的计谋正中下怀,于是“元昊从之,遂于天都点集左右厢军十万,分东西两道,一出刘番堡,一出彭阳城,合攻镇戎”,一举攻下了镇戎军,又一次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由此可以看出张元是元昊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要谋士、助手,故史书称“元昊据地万里,有华州二生(指张元、吴昊)为之谋主”。
诚然,作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的张元,在短短五年的西夏宦海生涯中,也有失意的时候,这与西夏皇帝元昊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不听下属劝谏和谋略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导致张元中道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暴露了张元的缺陷和软弱的一面。据史书记载张元“常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一身二疾,势难支矣”。张元的这一远见卓识和远大报负及鸿鹄之志,终因元昊的武断专行而无法实现,最后“既元昊议和,争之不听,及与契丹构兵,知所志不就,终日对天咄咄,未几,疽发背死”。就这样,西夏国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一心为辅佐元昊称帝图黄,为强国富民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一代雄才、谋士——张元,于公元1044年12月因“所志未竟,中道夭亡”,使人为其惋惜矣。
张元不仅是一位卓越超群的谋士,勇武过人的将军,而且是一位“放意诗酒,出语惊人”的诗人。他的诗意境深远,雄浑有力,情景交融,具有一股浩然之气和鸿鹄之志,读来震人心魄。如,田昼的《承君集》载有张元的诗。其中,《鹰诗》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诗中写道:“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从诗句来看,诗人确非凡夫俗子,表明张元鸿鹄般的志向和抱负,希望飞上云头成就一番大事业,做出一些惊天动地之功绩。在诗中又写道:“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这写明了“怀才之士,不为我用,即为敌资”要对这些人委以重任,发挥其聪明才智,不要让他们飞到别人家去,成为你的仇敌。这首诗文笔清丽,气势雄壮,震人魂魄,这足以证明诗人的功力。再譬如,公元1041年2月,大宋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经略使,他一心想吞并元昊,于是利用“揭榜塞上,得赵元昊首者赏钱五百万贯”的手段,诱惑下属捉拿元昊。元昊作为西夏国一代雄杰,“性雄毅,多大略”,加之有张元这样的高参辅佐左右,所以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捉到的。在张元的密谋策划之下,元昊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亦令人入塞,佯为卖箔者,遗其箔于食肆,人以献竦,启之,中有榜‘得夏竦首者与钱三千文’”,进行了深刻的讽刺、挖苦和嘲笑,把大宋朝官员贬得一钱不值。如此还未能完全解除张元心中之恨,于是就在两国交界处寺壁上题诗一首,进行了冷嘲热讽:“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并在诗后署上他在西夏的官职和姓名:“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他在诗里采用谐音,讽刺挖苦大宋官员夏竦和韩琦的无能。这首诗言辞犀利尖锐,讽刺意味力透纸背,意蕴丰富,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声,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综上所述,张元不但智勇过人,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对元昊可谓忠心耿耿,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参谋和助手;同时,他又是一位才华横溢、出语惊人的诗人,当然,更是我们现代秘书的楷模。
(原载《秘书世界》1997年第3期,2009年12月对该文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