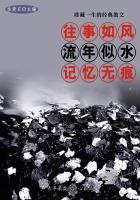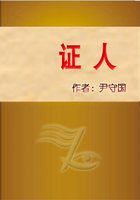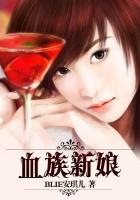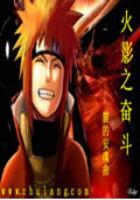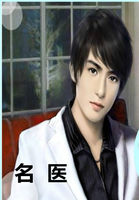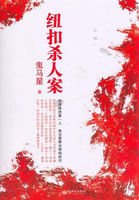故乡的白鹤树
白鹤树是故乡的骄傲。
白鹤树其实是棵皂角树,由于栖息白鹤而得此名。
白鹤树在我们村东北的一条小山沟里,是棵千年古树。据老祖先传说,唐朝初年开国大臣尉迟敬德骑马路过此地,见风景极致,下马坐石歇息观望,顺手将马鞭插在地上,眨眼工夫,鞭杆上长出枝干,接着又暴出叶蕾。正在惊奇,枝叶逐渐伸长,一顿饭工夫遂成一棵碗粗的皂角树。敬德知此地乃神奇之土地,于是跪拜后离此而去。
皂角树迄今1300余年,树干需五人合抱,树高十丈有余,树冠覆盖40多平方米。由于枝繁叶茂,每年开春,数以万计的白鹤就从南方一族一宗、一家一户纷纷飞来,落于树冠之上,逐日增多,直至落满每一个枝枝杈杈。远远望去,似满树银花,如雪落松塔,一片银白的世界。走近,却见千万只白鹤在树权间或上下翻飞,或翩翩起舞,或嘎咕啾鸣,或卿卿我我。
清晨,三五成群的白鹤从树杈间飞出,一字排开,嘎咕呜叫着翔过山沟,越过田野,掠过村庄,四散开去;傍晚,白鹤又接二连三从四面八方徐徐飞回,栖于树冠之上。日复一日,成为我们村一道蔚为壮观的自然景色。
人们传说,白鹤是吉祥之鸟,拥有它,庄稼连年丰收,村民延年益寿。大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开始,白鹤春来冬去,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几十年来,白鹤和栖息白鹤的这棵千年古树,为远远近近的人们所羡慕,成为我们村的骄傲。
为此,公元1983年我写过一篇题为《白鹤树》的报道,发表在当时的《陕西农民报》上。也就是这篇报道,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西安通览》一书将白鹤树作为风物载于书中;县政府和县人武部及时地在白鹤树下立牌警戒:“此鸟为国家第二类保护动物,严禁捕杀,违者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时隔不久,县统战部的同志领着省上大员,前来找我,要我就白鹤树一事撰文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祖国大地上奇妙的风物景观,对台湾广播。这篇文章我确确实实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听说反响很大,那些侨居异乡的千千万万的赤子,听到广播,纷纷勾起眷恋祖国、思念家乡之情,不断有人写信和祖国联系,有人陆续回到大陆。我们村有位早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的旧军人叫许平印,如今已六十多岁,听到广播后,回忆起家乡那棵皂角树,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终于瞒着妻子儿女,通过香港回到大陆。那时,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人,民政部门从省上到县上,层层接待。这位旧军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回到村子后无人认识,连他的亲侄子也不知他是何人。
稍事休息,许平印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去看一看那飘忽在脑海中的白鹤树。县民政局、镇政府、村委会,还有我这个写文章的普通百姓,一块儿领着他去村子东北那棵白鹤树下。跟着去看热闹的村民们闹闹哄哄,相拥相随,一排排站在他的身后。许平印仰望飞舞于树冠之上的千万只白鹤,思绪万千,顿时热泪盈眶。跪拜、烧香、叩首,都在沉默和肃穆中进行……
从此,这棵千年古树,更显示了它奇妙、雄伟、挺拔、博大的神威。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又撰文惦记它,却是缘于一种愤懑,一种不平!
曾几何时,我和千千万万赤子脑海中的神圣之树——白鹤树,被人残酷地用锯子伐倒了,树股做了水车的轮箍,树干做了死人的棺材……谁人所为?我不说,聪明的读者自会猜出一二。
白鹤飞走了,一去不复返了!好端端的令人羡慕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我梦幻中那种作为故乡人为之骄傲的乡情,也随之化为乌有。呜呼!我那可爱的白鹤树;呜呼!白鹤树上那千万只春来冬去的白鹤……
原载《秦风周末》1998年10月23日3版
《金秋》1999年第6期转载
故乡的龙头松
龙头松是一处颇负盛名的人文景观。
二十岁那年,我去灞龙山教书,同事们都说,距学校不远处有一棵龙头松,不但蔚为壮观,而且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于是,五六人相约,由家在龙头松旁边的学生邹海带径,沿着灞水堤岸溯源北上。
步行一个多小时,到青岗坪。此处虽系关中东部的秦岭山脉,但本地人多为江楚移民,所以,民风民俗均与陕南、两湖不差上下。典型的陕南山村,两排低矮的瓦屋,一条石板街道从中穿过。
邹海领我们到家中稍事歇息,茶罢,即向龙头松进发。
刚出村口,就看到沿阶而上的石径大路旁兀立着一棵奇特的松树,邹海手一指说:“那就是龙头松!”
生于斯长于斯的邹海,像大人一样扯起老道的腔调:“话说西汉末年,王莽赶刘秀。一日,王莽的大军来到青岗坪,年仅十四岁的刘秀立即从一户人家后门中冲出,爬上了这棵枝叶繁茂的松树,顺势仰面睡在一股歪斜到悬崖上空的枝杈间。王莽的大军来到树下,只朝两岸青山和大路旁边的溪水张望,压根儿不注意松树中间还仰卧着一名‘通缉要犯’……由于松树的遮掩,刘秀躲过了王莽的追赶,后来登基,建立东汉王朝,称光武帝。为纪念此树救命之恩,光武帝特封它为‘龙松’……”
说来也怪,这龙松从整体树貌观察,颇像一具伸往河水中正在吸水的龙头,有虬角,有龙须,连鼻子眼睛也能意会出来。
只要你用“龙”的意念去体味它,就会发现树干披满周身龙鳞,密密麻麻,与图画中的龙身无异;树股更为奇特,无论大小枝股,皆似一条正在飞舞的龙身,有头亦有尾……
我们五六人合抱,也搂它不严。我们搭人梯,上得树杈间,发现每个枝股朝天的一面,均是平直光滑的,似有人睡过一般。
我们寻觅刘秀当年隐身的那棵枝股,果见伸向河溪中的一条主枝上面,约三尺多宽,既平且直,更有人仰卧于上留下的痕迹,有头枕之穴,有背压之坑,有脚蹬之臼。于是我们轮换着在上面仰躺一遭,体味一下刘秀当年躲避王莽之心境……
80年代初,邹海已在市旅游局工作。那时,我曾担任《西安晚报》特约通讯员,写过一篇风物报道,名《龙头松》,刊在晚报二版上。此文被省上一家电视台看到了,他们当时正在筹拍一部描写旅游干部艰苦创业的电视连续剧,编剧正好是我那学生邹海。
于是,受我那篇文章的诱惑,他们把外景选在了灞龙山,好多镜头也有意放在了龙头松底下;拍电视的时候,导演还特意安排我跟着剧组一块儿去了那块风物旖旎的地方……
后来,电视剧播放了,观众们看到灞龙山那秀丽俊美的景色,看到龙头松那壮观婆娑的雄姿,无不唏嘘称赞。
人们都说,这儿要是开辟一个旅游点,无论那温馨雅致的青岗坪民居,无论那一级胜似一级的石板小径,无论那满坡翠绿的松柏,无论那颇具神话的龙头松,都将吸引着广大的游客。
然而,时光流逝,龙头松依然孤独地奓在河溪之上,依然彷徨地站在石板大路边沿的崖畔上,无人问津,无人开发。
惜乎!是无人认识这一道壮丽的自然景观呢,还是它距城市太远交通不便?抑或是资金短缺,无力开发?
谁要是有开拓的眼光,谁要是有重视人文景观的意识,谁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将故乡的龙头松开辟成为一处颇具诱惑力的旅游胜地!我期待着有人开发的那一天!
原载《西安旅游报》1998年12月21日11版
故乡的自来水
提起故乡的自来水,我常常发出一种莫名的感慨!
故乡虽然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山村,但在我的印象中,人畜饮水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绕着村子流过的河水,时有时无,河槽要比村子低十多丈,而且上游多有污染,人畜无法食用;2000多口人的村子,前后八条街道,守着十多口水井,雨水充裕的季节还则罢了,若遇上干旱年景,村里人就只有望水兴叹了!
改革开放初期,镇上办起了奶粉厂,大力发展奶牛事业,我们村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就买回60多头,成了远近闻名的奶牛村。村子里那十多口老井,再也不能满足人畜饮水的需要了,从此,人畜饮水就成了村民们最头痛的头号大事。
十多天后,我从城南一次就运回来三头花花奶牛。这一下,人吃牛饮,每天至少要挑二十五六担水,全是我这个男子汉用一双肩膀从300多米外那口水井中挑回来的。天长日久,我的肩膀上压出了拳头大两个肉瘤子。
男人不在家,挑水的担子自然就压在了婆娘女子娃身上。记得有一次,我从菜地里送粪回来,见老婆趴在门槛里边,满身满脸都是泥水,两只水桶一只滚在门内,一只滚在门槛外边,我忙扶起她。她缓缓地坐起来,疲惫地叹了一口气,把蓬乱的头发朝后捋了捋,破口就骂:“这鬼地方,吃一口水难死了!”
第二年夏天大旱,村子里十多口井里全没水了。人们只好张着大口,喘着粗气,去河道里挑水,还不过三天,河道里也干涸了。
幸好,我们村北边的龙头岭上有泉水!
一条黄土岭龙舞似的从北山里蜿蜒南下,到我们村北边,突然“扎”住了。这突然“扎”住的岭头,酷似龙头。几堆嵯峨参差的石包,酷似龙眼与虬角。龙口处嵌牛大青石板一面,石板下卧一口清泉。村里人把它叫龙泉。
龙泉旁边常年四季绿草丛生,水气氤氲。泉有笸篮大,清澈见底。泉中央桶粗般一堆水眼,有如莲花状爆出朵朵水花,冲起无数白色的沙粒,在水花中跳跃。这水花,千百年来,涌流不息。
龙泉下边,浇灌着一台台藕塘。夏天,满塘荷叶墨绿,星星点点闪出粉红色的荷花,煞是好看。小时候,我们常常光着屁股钻进池塘,偷人家的荸荠吃,用脚踩出像婴儿大腿样的藕,在龙泉中洗一洗就“咔嚓咔嚓”吃起来,发出脆生生的响声。
我们村出产的是九眼莲,白得跟雪一样。老人们传说,当年慈禧太后西安避难时,这九眼莲还曾经进过贡呢!
说来也怪,用龙泉的水做糊汤——关中农村用玉米糁熬成的稀饭,又稠又粘;用龙泉的水做豆腐,足足比井水一座要多出20多斤,而且又白又嫩。我们村卖豆腐的那个刘老五,常常是把豆腐块挂在秤钩搭上,向买主夸耀的。
井里没水,河里干涸,人们只好赶到龙头岭上去挑水。
要上龙头岭,必须绕着“之”字形石板小径,踏上一台台荷塘的堤坝,如同站立云头,亦似寻觅天庭。上上下下,挑一担水至少需半个小时。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和那力不能及的妇女们,一个小时也别想回来……
吃水难啊!
这种艰难的吃水环境,大约从上古时期有了我们这个小山村开始,就这么一代一代遗传下来。没有人能改变它。
后来,我离开了我那小山村,进城做了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也就不再去操心有水没水的事了……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又一场大旱。我因母亲有病,回了一趟老家。刚走进巷口,就听见锣鼓家伙在不远处“咚咚锵,咚咚锵”地敲个不停。邻家老嫂子扑过来说:“嗬呀,你儿子可是功高盖世啊!他给咱们两条巷子安上了自来水,从今往后啊……”
原来,今天龙头要放水了。
大人、小孩,都拥到街道上,欢呼着,跳跃着,等着龙头喷水的那一瞬间。
邻人们见我回来了,就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说我的大儿子收拾了在城里的企业,自己出资一万元,走东家串西家,商量把龙泉水引到各家各户来。人心所向,大伙儿很快扭成一股绳,几个年轻人立即从县城拉回两车弯弯曲曲的地下水管,婆娘女子娃一齐上阵,把那龙泉挖下30多米深,井底铺厚厚一层沙粒,又用青砖箍了井壁,水泥封了顶盖,水管子从地下送到各家各户的院子里,有的还送到了锅台上……
锣鼓家伙敲得正猛,人们“哗”地一下离我而去……原来总闸放水了!
我立即赶进家门,院子里被邻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隔壁王三爷站在我家院子中央的水龙头下,双手接着喷出来的清水,一掬掬送进嘴里,咂着唇舌……他放声笑了,笑皱了一脸核桃皮。笑着笑着,那笑声却变成了哭声,而且两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望着这清湛湛的自来水,我也抑制不住情感的阀门,想起代代相传的吃水难,我不禁热泪盈溢啊,亲爱的故乡,您从此告别了挑水吃的历史;自来水,这个神奇的梦幻,将世世代代滋润着这方温馨的土地!
原载《太原晚报》1998年10月30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