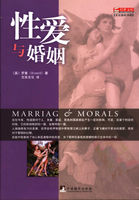司机与狗
司机是朋友的司机,有时受朋友委托,司机也时常接送一下明人,当然是参加朋友的活动。
那次从九华山回来之后,明人看那司机的眼神就有点古怪了,或者说,司机在明人的眼中,变得奇奇怪怪的了。
明人憋不住对司机说了,我看到你,怎么总觉得好怪。
司机很诧异,眼睛疑惑地注视着明人。明人却不说下去了,他痛苦的闭上眼睛似乎要忘却什么。
司机如坠云雾之中。
有一天,明人又憋不住对司机说了,司机也憋不住了,问明人到底什么意思。明人又痛苦的闭上眼睛,让司机迷惑不解。
这一天,很晚了,明人参加完一个活动,朋友让司机送明人回家。途中,明人时不时打量司机。司机也察觉到了,很不自在。明人是朋友高贵的朋友,司机又不能随便发问,这不礼貌。
倒是明人主动又问了一句:“你的属相是……”司机回答,属兔。“不会吧,你不应该属兔的。”明人说得斩钉截铁。
司机说的更斩钉截铁:我就是属兔的,我自己属什么会不知道!司机心里憋着一肚子火。
明人嘿嘿笑了:“我说你不是属兔的。”
“那你说我是属什么的!”司机也不客气了。
“你应该属狗。是的,属狗的!”明人一字一句,说得清晰。司机的脸都涨红了,他也嘿嘿笑了,笑得真是稀奇古怪。
明人,没再吭声,他心里在问:“他真是属狗吗?”他也犹豫了,吃不准这答案究竟如何。他甚至觉得他是连狗都不如的。可是,这感觉更难说出口。
司机讪讪地笑。明人却已灵魂出窍一般,未置一词。司机的形象在他眼前又模糊起来,是人还是狗,还是那个小白兔?明人头痛欲裂,无法明辨。
那次,司机送明人从九华山回家。有一只狗突然从路旁的农舍穿将出来。车子依然快速疾驰。明人很快就听到一阵清晰的断裂声。撕心裂肺,让他不寒而栗。而司机若无其事,继续踩着加速器飞驰。明人当时也蒙了,好久才缓过神来。那断裂声就一直萦回在明人的耳畔,总不能消散。
这回,司机脸红了,明人也明白了,原来这狗的形象一直没离开过,他掂念着那条狗呀!
但人有时真不如狗,他无奈地感叹。他之后就不要这司机相送了,他让他太想起了那条悲惨的狗了!
手心里的痣
很多贵人簇拥着他。对他十分的尊重,包括明人的上司。这个油光满面的人究竟何许人也。明人正襟危坐,不敢吭声。
酒过三巡。召集人絮絮叨叨地介绍之后,明人才知晓面前这个面相几近猥琐之人就是好多人津津乐道的神人——刘马。这刘马据说饱学诗书,通晓天文地理,早年出过家,后还俗并自称居士,会看手相,许多官员商人都愿意与他吃饭一聚。仿佛从他处可得到一丝天机增加一点仙气。
这当儿,那些贵人们纷纷伸出手掌,像袒露自己的胸膛一样,期盼刘马大师的指点。他每个人都说得神神叨叨,出口成章,旁征博引,有立有论,让在场人颇为信服,被说的人也都心想事成一般,有兴致,有些提及的险象,似乎也不以为然,照样神采飞扬。轮到明人了,明人有点迟疑,想起二十年前,他在一家青年干部学院培训,当时也风行看相。他也斗胆为那些年轻人看相。连蒙带猜,竟然说得他们十分信服,一传十,十传百地要来让他看相。后来他甚觉荒唐,心里发笑,又感到在学校如此,影响不佳,于是坚决辞客了,也笑谈洗手不干了。所以,这些年来,他对这些玩意儿总有点怀疑。
他本不愿伸出手掌的,但看着刘马大师殷勤地在凝望着他。大伙儿也在一旁怂恿着他。他犹豫地摊开了手掌心。
明人皮肤并不白皙,但手心光洁鲜嫩,血色隐约。唯有正中心有一颗黑乎乎的东西,十分醒目。刘马的眼睛看得直了,显然那颗痣一样的东西吸引了他。他用探究古文物的眼光,仔细端详着明人的左手心,凝思许久,令气氛也不觉更加凝重起来。
明人瞅着刘马大师,也瞅了瞅大伙儿,有点好笑,但憋住了。这玩意跟随了他这么多年,他心里有谱。
刘马大师这会儿抬起头,定定地望着他,缓缓地吐出几个字:神,神人!神就神在,这一颗痣隐在表层里,无棱无角,无法触摸,隐而不露,又不看自明,凤毛麟角,百万人才会有一个,那是一种神器,喻示你从容大度,玩权术于股掌之间……
大伙儿的眼睛都直了,连上司看明人的眼神都有点古怪,那里面一定酸味浓重。
刘马还在滔滔不绝。明人却一言不能发,如坐针毡一般。
过了好久,席终人散,刘马还紧握着他的手。
回到家,明人就呼呼睡着了,这些鬼话能有什么作用!就当是催眠曲吧。至于那颗痣,完全是一场偶然事件。那还是小学念书时,他拿着铅笔双手叉在身后。人靠在教室的后墙,一位同学不小心靠在他身上。他避之不及,铅笔不巧就扎进了手心里。很久很久,那里留下了一个印记,如淡淡的黑痣一般,无法消散。
大师没把它视作噩运当头,自己就是大吉了。明人想。
秘密
很小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悄悄告诉明人一个秘密:他的母亲不是亲生的。他把明人视为最好朋友。明人一愣,他一时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小朋友解释说,他的亲生母亲上天堂了,他的父亲又再娶了现在的母亲。他哥哥就是继母的儿子。明人的脑子里就浮现出好多后娘欺诲孩子的种种传说,连忙追问:“那你妈,哦,继母,是不是很不喜欢你。”
小朋友的脑袋顿时摇得像个拨浪鼓:“没有,没有的事哦。我妈妈对我挺好的,比对我哥哥还好。哦,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特别是我哥哥哦。”
在明人发誓不会告诉别人之后,他神秘地凑近明人的耳畔,轻轻说道:“每天晚饭,我吃着妈妈盛给我的满满一碗饭,扒拉几口,就会发现碗底有异样,我悄悄察看,不是卧着一个荷包蛋,就是一块大肉。我与妈妈令爸爸和哥哥不易察觉地互视了一眼。我知道,是妈妈厂子里带回的,是偏爱我。”
小朋友说着眼睛也发亮了,有一种幸福感在闪烁。明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妈真好!”
明人后来注意到,这一家人很和睦融洽,哥哥待弟弟也视亲兄弟一般。以后,两人在父母的关照、培育下也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也都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
好多年之后,明人又邂逅了那位当年的小朋友。他已是一个企业的老总了。两人亲热地交谈,明人还问及他的父母。
谈及母亲,也即他的继母,那位朋友一会儿就泪水盈盈了。他说她已操劳过度,也已上了天堂。他说她是多好的母亲呀!
那位朋友忽地问明人:“你还记得我曾经给你说过的小秘密,那碗里的荷包蛋和大肉吗?”
明人说:“知道的呀!”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不可说出去的秘密呢。我怕哥哥嫉妒,你知道,那时我们都小,又分别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对这新家,心里头都既敏感又脆弱着呢。母亲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我们心灵的波澜,甚至影响我们的心理。”
“那后来呢?”明人等不及了。
“也是和你说过之后的好几年,我和哥哥已完全如同亲生兄弟,我们这一家也完全牢不可破了。我有一天,就把这秘密告诉了哥哥。没想到,哥哥淡淡一笑,说,‘我每天晚上的碗里也有一只荷包蛋或者一块大肉。我知道是妈妈偷偷放的。可有一次问她,她说让我别说了,她说这是爸爸特意嘱咐的。我知道,她是让我向着家,向着爸爸,爸爸、妈妈其实真是世上最好的爸爸、妈妈!’”
朋友叙述完了,眼睛里还噙着泪,泪花中还有一种光芒。明人发觉那是在他孩提时代就闪烁过的,一种真正的幸福感!
提前量
明人一到现场,黑压压的,已站满了人。明人赞赏地瞥了刘总一眼:你真可以呀!刚才路上还担心,一早八点的工程开工仪式,别都姗姗来迟了,大领导到了,就尴尬了。
抬腕看表,离八点开始,还有半个小时。早春二月的冷风,还像刀子一样割人肌肤。工人们站在空旷的工地上,冷得脸都发白了。明人仅到了一会儿,就冷得直哆嗦。他走上前,与几位工人握手,他们的手都冷得像冰块。人心都是肉长的,他的心一阵酸疼。他真诚地说,让你们辛苦了,领导到了我们就开始。他问一位工人,你们来了几分钟了吧。一位粗黑的汉子也许是受冻了,嘴唇嚅动了好久,才吐出几个字来:“有、有一、一小、小时了。”明人以为听错了,疑惑地看了看刘总。刘总有点炫耀地介绍,都过一个多小时了。明人皱眉,随即怒火中烧:“谁让这么早的!我让提前十分钟就可以了。”
刘总一看明人真生气了,连忙解释,这不能怪他,他是在明人讲的十分钟基础上,又加了二十分钟。公司办公室主任通知时又加了十分钟。分公司经理通知班组长时也加了十分钟。班组长们不约而同又都加了提前量。这一小时就理所当然出现了。
这一天大领导又迟到了半小时。明人之后宣布,以后类似会议不得如此提前,离会议前十分钟就可以了,谁不把一线工人当回事,他就跟谁急!
一年之后,又召开项目现场会。一位新任的大领导将到会。一大早,明人赶往会场。手机骤响,办公室主任心急火燎地禀报,大领导已到现场。离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呢,咋来这么早呀。明人顾不上许多,让司机加大马力,赶到现场。
现场除了一些工作人员,大队人马还没到。大领导气呼呼的,一脸不悦。他说他还想提前到,提前开的呢,你这是唱的哪一出空城计呀。边上人想说明,大领导打断了:别说我没事先打招呼,你们完全可以多打点提前量,谁不是这样组织会议的!
那天会议是按计划准时进行的,一点没耽误,人也一个不少。会后,明人也未明确什么,但部下又按老办法加大提前量了!
距离
下车时,导游再三提醒,你们别靠太近了,天鹅会飞走的。
明人和游客们兴奋地扑向湖边,但很快一车人几乎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扇形,向赛里木湖边缓缓走去。
初秋的赛里木湖一片静谧湛蓝,蓝天白云和远处隐隐约约的冰川雪峰,让这片天地宛若童话世界。七八个黑点,在湖畔一溜排开,像井然有序的省略号。那是天鹅在湖边优雅地栖息。
愈来愈近了。小小的一个个黑点已显出一个个婀娜多姿的形态来了。大家还在轻步挪近。
该停步了,明人想,并且迅速抓起相机,拍了一个远景。这时,他看见镜头里有一个小黑点已站得更挺立了,翅膀也微微抬起来了。
他轻声唤道:别往前了,再走,天鹅要飞了。
只有边上几人朝他瞥了一眼。绝大多数人依然在往湖边走去。
又有两个黑点亮起了翅膀。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信号了,天鹅们已经开始警觉了。
明人也急了,自己的脚步放得又轻又慢,仿佛在原地无声地踱步。但其他人还大兵压境似的,还在向天鹅逼近。
又有若干天鹅亮起了翅膀。有人相机的咔嚓咔嚓声,也如炸雷一般声响。
这个距离已足够近了,明人又低声唤道:“别再靠近了,别再靠近了。”他甚至伸出手臂,想拦住身边的几个游客,但他们乜斜了他一眼,躲开他,直往前去。
这时,先有两羽天鹅扑棱棱地飞走了,又有几只,也稍稍迟疑了一下,也挥动翅膀,飞掠而去。很快,刚才在湖畔栖息的所有天鹅都远离了,差不多都立于粼粼清波上,又成为遥远的一个个黑点。
明人想,在那些天鹅的眼里,散落的游客,此时也只是湖畔一个个失落的黑点了。
明人无法精确地估算他们与天鹅的距离,但他知道,这些距离是必然存在的,就像他和这些游客,人和人之间,有时也存在不可回避的距离一样。
保安
那个保安来自苏北,一口普通话,带着家乡口音。明人和他聊过,那次他早下楼了,司机还没到,他就和这个保安聊了一会儿。
这个保安长得五大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明人叫不出他的名字,但他的脸很熟悉了。
闲聊中,保安礼貌客气,也知道明人住在哪幢楼。
有一天,明人在外,有一个陌生手机号打了进来,一接,是一个很不耐烦的外地口音。几句话后才听明白,对方是快递公司,有一个快递要送他,家里没人,要等他签收。明人说,你放门卫那呀。对方说,门卫不肯收。明人说你把电话给门卫处的保安,我和保安说。保安接听了,是苏北口音。明人请他帮忙先签收了,保安一口答应了。
以后明人好多事都找这个保安,连房门和车钥匙之类,都放保安处中转。从未误过事。那个保安还是很认真敬业的。
某一晚,在一个即将打烊的超市,刚购了物的明人听到一阵吵吵嚷嚷声。他定睛一看,是超市的保安拦住了一个人,要搜他的身。那人竟是小区的那个苏北保安。他穿着便衣,不穿制服的模样,更显粗犷。
超市保安怀疑他衣服里偷藏了东西。他则百口难辩。明人望了一眼保安,上前为他求情。超市保安问,你认识他吗?他叫什么名字?明人说不出,超市保安就不放行。无奈,明人认识他们老总,打了电话。老总问,你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呢?明人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以自己的人格担保。老总下令放了他。
出了门,他对明人致谢,说他确实没拿什么东西,说完,他还脱下了上衣。明人阻止了他。他相信他。
之后有人问明人,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敢这么保他?
明人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甚至他姓什么,但我知道他的心,心善。有的人我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敢担保他呀!
忏悔
明人刚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一家颇有影响的著名刊物上。在那篇文章里,他自我剖析,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地对自己所谓的成熟,其实是心灵麻木进行了反思和忏悔。所举的事例就是路见摔倒的老人,不敢援手,助上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