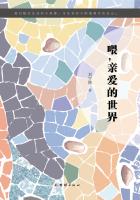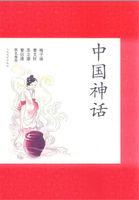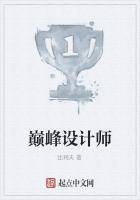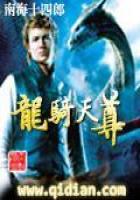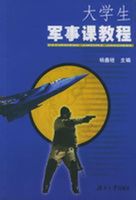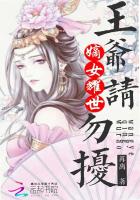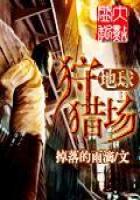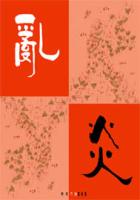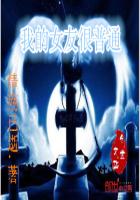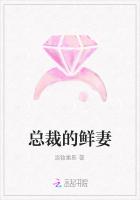1954年,许燕吉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石家庄牛奶场。这年夏天,她结了婚,爱人是同学四年的吴富融。然而,她的幸福生活实在太短了,简直比兔子尾巴还要短。结婚第二天,丈夫就下乡了,未几,她也锒铛入狱了。1955年初,单位搞“审干”,她被当做重点审查对象。到了八月,随着“胡风集团案”的展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肃反”。她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关押了起来,丈夫也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
时间来到了1957,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罕有其匹的“钓鱼执法”事件。像所有的倒霉的知识分子一样,许燕吉也只是提了一些几乎很难叫意见的意见,就被旧账新账一起算,打成了“反革命”和“右派”的“双皮老虎”。他被开除公职,吊销了户口,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失去了在城市生活的资格。她的未足月的孩子胎死腹中。她被捕入狱,丈夫也被迫与她离婚。在监狱里,她吃尽了苦头,也目睹了别的犯人所受的非人待遇,看到了不堪凌辱者的自杀。然而,即便这样,她仍然努力同情和帮助那些像自己一样陷入不幸境地的人。
饥饿是最可怕的一种苦难境遇,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极难忍受的肉身痛苦,也是一种降低人格尊严的精神煎熬。饥饿本是监狱惩罚犯人的一种手段,但在“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则成了一种日常性的痛苦折磨。监狱里的大饥饿,威胁着每一个被关押人员的健康,甚至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监狱里会发生大量饿死人的事件:
风雪上冻的日子更难熬,正所谓饥寒交迫。那天我走过阅览室,见文宣组姓刘的那个男犯拿了个大缸子正仰面而饮,我便进去问他:“你还渴吗?”他说是家里送来点酱油,兑着喝点儿。我告诉他酱油没什么营养,喝这些水还得排出去,要消耗更大的能量,是负能。他也是个知识分子,能够了解,苦笑着说:“没办法,不喝受不了。喝了能缓解一会儿。”仅过了两天,我再见他,他已躺在小车里,睁着眼张着嘴,还在呼吸,又拉了回来。那一天,五六百人的男兵营就死了14个。后来知道,两千多人的省第二监狱,高峰时一天死了37个。
苦难呼唤人的生存勇气和乐观精神,也激发人们自我拯救的意志和潜力。面对苦难,许燕吉没有沮丧和颓唐,而是表现出极为难得的镇定和坚强。狱友们情绪低落,“加上饥苦难挨,许多人低头垂泪,或凝神发呆。监舍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于是,许燕吉便在请示了管教之后,将大家赶到院子里,一起做体操,搞“联欢会”,她想通过这些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朝希望和乐观上引”。在被人问及她如此做的动机的时候,她的不敢说出的“真实的思想”,即“我是怀着一种悲悯之心在同情这些不幸的人”。
许燕吉详细地叙写了近乎圣女的女教徒孙瑶真的虔诚和执着。我们在她的身上可以看见宗教情感的伟大和圣洁。“自由熏陶她的教义,多年修会的约束,造就出瑶真仁爱宽厚、谨慎谦和、舍己为人的品格,在众多类型的犯人中就凸现出来。她很讲卫生,全身上下总是干净整齐,可是一点儿也不嫌有病的同犯,吐的拉的她都尽心地给擦拭。有个年轻女犯恶习不改,在狱中依然小偷小摸,而且特懒,浑身脏臭,大家都不理她。春节前全体都拆洗被子,就她不动,说她不会,从未干过这事。瑶真就耐心地教她,发现她身上虱子成堆,又打来开水给她烫,烫得大铁盆下面淀了几厘米厚的死虱子。大家都转过脸去,省得恶心,而瑶真还赔着笑脸。女犯中老得不能动的、病得卧床不起的、弱智的、精神不正常的,管教把她们都放在瑶真组里,病危的也让瑶真给送终。不论男犯女犯,凡是患眼疾的都由瑶真给医治,甚至干部也找她看病。医务室的男犯是个反革命,但也是个大流氓,和一个常找他看病的女犯有不轨行为,为此受到加刑处分。审问他时,他说:‘瑶真常来医务室,可她像个圣女似的,一点儿也引不起我的邪念。’”1965年,她被释放了,由于她明确表示不背叛宗教,给她加了个“反革命的身份”。她回到故乡,依然坚持行善,人们都感激她,爱戴她。1967年,“文革”造反派宣布取缔宗教,“凡坚持信仰的都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拴上大拇指吊上房梁,有的被捆上两腿,让骡子在铺上煤渣儿的路上拖拉,有的被融化了的沥青烧背,有的被大棒子狠砸‘花岗岩头脑’,仅一个边村就酷刑致死了一位神父和四位教徒。造反派还将一位守贞的女教徒脱去衣服扔进水塘里,说谁要娶她可以捞她回去。所幸瑶真因为有反革命身份,运动初期就捕入了劳教所里。”此后,瑶真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又几次被关进监狱。2005年,瑶真作为天主教徒,安静平和地逝去,享年91岁。许燕吉说:“她是我永远崇敬的人,是我永远怀念的人。”
在孙瑶真身上,许燕吉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信徒的高尚和伟大。她崇敬孙瑶真,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她怀念孙瑶真,是因为她认同那种利他主义的宗教精神。事实上,许燕吉也总是抱着爱的态度,对待别人,总是用怜悯和同情的眼光,看世界,看生活。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崇敬的人。
4
宗教传播的是受苦人的福音。宗教面对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一个真正具有宗教情感的人,他的眼睛总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向权贵阶级唱赞美诗,而是向孤儿唱摇篮曲,向逝者唱安魂曲。彻底的宗教精神就是彻底的底层精神。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近于官的,向来缺乏与权力对抗的独立精神,向来缺乏对底层民众的平等意识。他们习惯于用知识兑换权力,所以,才有“学得百般艺,货与帝王家”的说法;他们的发迹梦的经典表达,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讲了几十年的“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但到头来,却仍然“心存魏阙”,仍然怀着“仰望北斗星”的情结。
许地山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彻底的底层主义者。面对底层人,他总是表现出亲和的态度,而不是高人一等的傲慢。受父亲的影响,许燕吉也有很强的底层意识。许燕吉回忆说:“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她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会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有一回中午,妈妈开车去接他,也捎上了我和哥哥。正在车里等着,妈妈叫我们看,爸爸正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下来,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帮助的。”
以底层人的身份,表达对底层人的悲悯,这就是许燕吉身上最突出的情感特征,也是她的这部自传特别闪光的地方。从许燕吉的叙事中,我们所看到的“动荡年代”和“禁锢年代”的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和细节,如此丰富,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看作纯粹意义上的底层文学。
她对狱友是慈悲的,所以,她倾听她们的叙说,并在自传中记录了她们的故事。善良的尹书金的故事,尤其令人同情,小侄女在门槛上“担着”的细节,简直令人心碎——“农村门槛高,小孩子把肚子压在门槛上,头向下栽着,这样‘担着’可以减轻饥饿的痛苦”。为了活命,母亲把未成年的她嫁给一个30出头的男人。她承受不了婚后的痛苦,杀夫未遂,判了七年,关进监狱才刚刚十七岁。在一个万事艰难的时代,尹书金的不幸命运,绝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