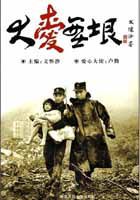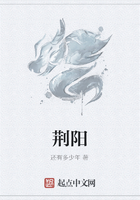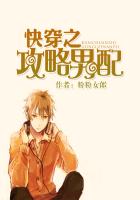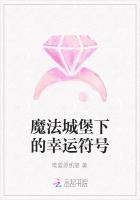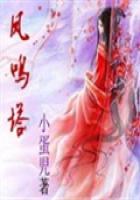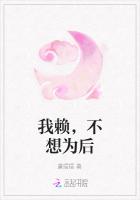现今社会多少有些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缺凑热闹的,不缺啦啦队,真正静下心来,安安稳稳,将民族的东西于无声处传承下来的则是少数。我们之所以从内心深处顶礼那些制壶大家,不仅因为他们高超的制作技艺,更多的是敬仰他们以紫砂壶寄情写意、言志修身的高风亮节。
而这份风骨也是我们民族的根。
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应该在一代又一代的艺术精品之中得以传承和发扬,文化的大旗不仅应在学术界,更应在民间扯将起来,猎猎飞扬。一把小壶,就是中华民族厚重文化的一个着力点,将壶中乾坤把玩到位,便是把一种民族的精神、一份独有的神韵和气息传给了后人。这才是先人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而作者愿意以一己之力,著这样一本小书,本身就是对民族文化传承最好的一种探索。我也愿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汇入文化传承的洪流之中,将世代相传的精品和优秀的文化保存延续下来,使中华文化宝库更加瑰丽华彩。
《紫砂壶》序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风景的力量
与其说倪益瑾爱摄影,不如说他更爱拍摄的对象。否则,他不可能为了摄影跑遍祖国大地上的每一个省区;即便跑遍了,也不见得总能从任何一个区域拍摄到如此绚丽多姿的美景。
据说为了拍到一幅较为满意的照片,他会在居住条件、生活条件很差的地方等待一天两天,甚至等待十天八天。说到底,他相信他所钟情的山河大地是美好的,并深信一定有某一个时刻是最最美丽的。
于是,他等待。在观察中等待,在等待中观察;在思考中等待,在等待中思考。等待春雨秋风梳妆大地的时候,等待夏云冬雪渲染大地的时候,等待朝晖夕照扮靓大地的时候。作为一位挚爱、执着、坚定、坚忍的摄影家,等待与选择就是创作。那是一种创造饱满完美的构图的等待,创造玲珑剔透的光影的等待,创造清晰变幻的层次的等待。那是一次次放弃与一次次追求的等待与选择。
就是在这样的近乎顽固的等待、放弃与追求中,他把宽广的视野给了他的作品,他把博大的胸襟给了他的作品,他把绚烂的色彩给了他的作品,他把缤纷的思绪给了他的作品,他把情不自禁的热爱给了他的作品。于是,我们才突然惊喜地发现,在祖国辽阔宽广的大地上,竟有如此美不胜收目不暇接的壮丽景观。
看得出,倪益瑾是一位特别唯美的摄影家。属于那种古典式的经典的唯美;唯美到苛刻、挑剔的程度。或许,这正是倪益瑾的风景摄影作品里充满了无可挑剔的动人力量的真正原因。那感人动人的力量,从一幅幅中国风景画式的意境中散发出来,从一幅幅西方油画般的色彩中散发出来——这就是那种古典的当然也是经典的唯美的力量。
也许他自己也常常被自己等待与捕捉到的美感动不已,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即兴率性的印象式表达。鲁迅曾经说过不同地域给了他不同的色彩感:“黄河以北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浅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倪益瑾跑遍祖国大地每一个区域,不同区域给予他的强烈的色彩感觉定然非同一般,而主观印象式的表达更加强化了区域性的色彩和不同的色彩构成的特殊的光影效果——欣赏倪益瑾的风景摄影艺术总觉得有些别致的意象,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倪益瑾摄影集《锦绣江山》序言,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
服饰里的文章
中华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素以“衣冠文物礼仪之邦”和“丝绸之国”闻名于世。黄能馥、陈娟娟合著的《中华服饰七千年》,就引导我们领略了这悠久的历史和万千的气象。
我们祖先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磨制骨针缝制毛皮衣服,佩戴用兽牙、贝壳、骨管、鸵鸟蛋壳、石珠等连串的串饰。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农耕牧畜,营造房屋,男子出外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发明纺麻,养蚕制丝,纺织毛、麻、丝布,缝制衣服。根据考古材料,我国在距今七千年前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一百余件带有麻布或编制物的印痕,其中已有平纹、斜纹、一绞一绞织法、绕环编织法等编织方法。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了距今五千四百年的葛布,织有回纹和条纹暗花。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平纹蚕丝绢和浅绛色罗,距今已五千五百年。新疆和青海新石器文化遗址则发现过彩条纹毛布。至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期,已出现用染色熟丝织出彩色花纹的织锦和在绢帛上绣出精美花纹的刺绣。衣冠鞋履、玉石首饰、佩饰与华美的发型配套,构成中华上古服饰文化的繁荣景象。
服饰是人类源于护体御寒等生理需求的物质产品,又是反映人们审美观念和生活理念的精神载体。我们的祖先自从发明了纺麻、缫丝、织毛等手工技术,就能利用纺织品缝制适合护体御寒的配套服装,而且创造了形式美观、具有思想内涵的服饰纹样,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末,中国进入传说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时代;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统治者以“天命神权”为精神支柱,宣扬“道协人天”的思想,把森严的等级制度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服饰是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就成为“礼”的重要内容,作为“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他与天帝沟通的办法即祭祀。《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论语》中说,禹平时生活节俭,但祭祀时必穿华美的礼服——黼冕,以表对天帝的恭敬。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继承和变革发展,到周代就形成了以“天子”为中心的完善的服饰制度,按礼节的轻重规定穿不同的礼服,同时规定按不同的政治地位穿不同礼服的制度,位高者可以穿低于规定的礼服,位低者越位穿高于规定的礼服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后宫后妃及百官的服饰也都有相应的定制。这些服制的思想内涵,完全从属于传扬“天命神权”,巩固阶级统治的政治需要。例如天子冕冠的板前圆后方,前面象征天,后面象征地;冕前后垂旒各十二条及天子章服的十二纹章,象征月之四时运行的十二地支(月令),冕旒以五彩缫(丝绳)贯朱、白、苍、黄、玄五彩玉珠,这五色与季节、气象、方位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星座相对应。天子章服的十二章纹,更具政治伦理的内涵,作为王权的标志,历代传承以至清末。
从考古证知,人类使用首饰佩饰早于使用服装的历史。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如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制作的玉器,包括发饰、冠饰、耳饰(玉玦及耳坠)、颈饰(玉串饰及玉项链)、臂饰(玉瑗、玉臂环、玉镯)、手饰(玉指环)、佩饰(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及鸟、兽、蛙、鳖、龟、龙等象生型玉佩)、玉带钩等,其形式之多样,磨琢之精巧,令人叹止。商周时期,玉器被统治者作为人格道德的象征,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除玉饰之外,商代已生产金首饰,以后金银珠玉宝石镶嵌工艺技术高度发展,首饰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一器一物,往往价值连城,这就形成了中华传统工艺美术的光辉府库。
在中国古代服饰纹样中,龙纹是地位非常显赫的装饰题材。古代神话中,如黄帝、女娲、伏羲等都说成是人头蛇身的神人,《虞书·益稷》把龙作为天子冕服十二章纹中的一章,而龙蛇作为服饰纹样的实例,已见于甘肃临洮出土的彩陶人形器盖中。《诗·小雅·采菽》中说:“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商周铜器铭文,亦可发现赐玄衮衣的铭文。玄衮衣即绣有龙纹的玄衣,可见中国统治阶级首领穿用龙衣由来已久。历朝以龙纹为衣袍装饰的实物形象,留传至今的甚少,唯明清两代尚有流传,尤以故宫博物院收藏最为系统、完整。当年龙袍纹饰款式系由清宫如意馆画师按服饰制度精心描绘,经审准后核发江南织造府织造,材质夏用纱绣缂丝等,冬用织成妆花缎或以缎、绸绣制,表以紫貂、熏貂、海龙裘皮等。织绣工艺精工无比,绣线则采用扁金线、圆金线、龙抱柱线、孔雀羽线等。一袍之作,辄逾一二年,积民间工匠心血智慧之精华。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服饰文化以华夏农耕士儒文化为主体,不断与少数民族的游牧骑射文化相交融,并在交融中发展。华夏民族注重礼仪德化,故服饰雍容宽博,气度万千,但实用功能性差。游牧民族活动性大,生活无定处,故注重穿脱方便,合体实用。当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华夷共处之时,华夏贵族的服饰便对少数民族贵族起到感染作用,如北魏孝文帝的服装改制即其实例,而少数民族的实用功能性服装则对华夏军队与劳动者产生重大影响,如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以后短装在民间日益普及,揭示了服装向科学实用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值得我们深深去研究、弘扬。
黄能馥教授和陈娟娟研究馆员,从上世纪50年代初即追随前辈服饰史学大家沈从文先生研究中国服饰艺术史,历经半个世纪,学术成果颇丰。他们夫妇两人的合著,曾两次荣获中国图书奖、一次国家图书奖、两次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陈娟娟自幼多病,曾患多种高危疾病达数十年,但一直坚持在故宫从事织绣文物的陈列、研究工作,与其爱人黄能馥合作,矻矻于学术著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陈娟娟是故宫博物院培养的一名优秀的织绣文物专家。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不久,曾去医院看望过病危中的她,还想待她出院后再细谈,不料竟成了永别。现在,由她和黄能馥合著的《中国服饰系列丛书》在故宫博物院庆祝建院八十周年之际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好事,它既是陈娟娟、黄能馥在祖国服饰文化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是故宫博物院对祖国文博事业的一份贡献。
《中国龙袍》序言,紫禁城出版社、漓江出版社,2006年
紫檀的魅力
在遍布全国、灿若群星的大小博物馆中,中国紫檀博物馆以其特有的魅力日益引人注目。
紫檀是极其珍贵的木材,紫檀家具是中华的瑰宝,紫檀艺术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精华,中国紫檀博物馆则是中国首家规模最大,集收藏研究、陈列展示紫檀艺术及鉴赏中国传统古典家具于一身的专题类博物馆。由陈丽华女士创办的这一博物馆,虽然时间还不算长,但以其有别于传统的运行模式,颇多创新的展陈方式,注重与海内外同行交流的开阔思路,体现了生机与活力,成为中国民办博物馆的翘楚。
中国紫檀博物馆以保护历史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职志。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工艺的兴盛时期。明式家具是中国家具发展上的高峰,以其设计简练、结构合理、做工精巧、造型优美、风格典雅的特点,备受推崇和赞誉。清式家具,主要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出现的风格,总体来说是“精巧华丽”。由于运用各种新工艺,造出各种新式样,其中亦有精品,是明及以前所未见的。明清家具的工艺技术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陈丽华女士集中数百工匠,营建厂房,搜购良材,在专家的指导下,潜心制作明清式样的家具。人们从博物馆的精品陈列中,可以看到雕作技艺的高超。这些传统技术终于后继有人而不致湮没无闻,实为文化之大幸!当一批批参观者驻足紫檀宫时,当这些珍品在国外展出时,当一些精品被国内外著名博物馆收藏时,中外人士从中所体味到的是中华文明的独有情韵,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决心和努力。
从历史上看,作为工艺品的家具,既有实用的功能,又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者,一般当首推宫廷。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明代的“御用监”,清廷的“造办处”,都曾广蓄天下珍贵木材,汇集南北名师巧匠,专为宫廷制作家具。故宫博物院现收藏的明清家具,种类齐全,精品荟萃,在数量、质量及艺术性方面,国内外任何一家收藏机构都无可比拟,特别是宫廷遗留家具尤多,不少是代表性作品。故宫还有一些著名的家具专家。这一优势,就使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紫檀博物馆结下不解的缘分。朱家溍先生等被陈丽华女士聘为顾问,指导他们的工作,并仿制故宫的一批家具,精心制作了一些故宫古建筑的微缩景观,如角楼,御花园中的千秋亭与万春亭等;宏伟的紫檀宫的修建,故宫的古建筑专家也曾悉心地予以指导。故宫为中国紫檀博物馆提供了多方面支持和帮助,紫檀博物馆则以自己的骄人成果使古老故宫的遗产得到复活,使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