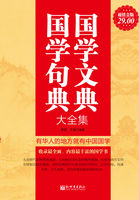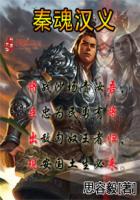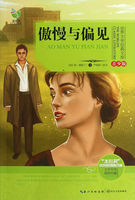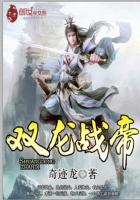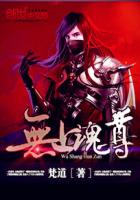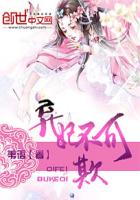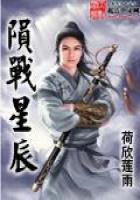正由于编著者深入农村亲自调查、征集刺绣作品,因此作品制作的地点和时间,作品的规格,作者的姓名,甚至作品的用途,包括与此有关的活动的图片等,大都有明确的记录或相关场景的反映。这就使作品有了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也只有在这个“语境”下,这些绣品才不是一件件简单的静止的作品,而是充蕴着灵性与生命力的活的东西,包含着大量的信息。编著者又通过“由物及人、由事及义、由情及史,由具体的链环而及整体的文化链索”的方法,揭示了这些绣品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特点,表现出绣品所反映的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民俗的丰富多彩。本书在书名上突出“乡俗”这一概念,当有深意。陕西由黄土高原及长城沿线风沙区的陕北、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及汉水流域的陕南三部分构成,风土、人情及文化背景各异,即在同一地区,也不尽相同。“乡俗”的差异,就使陕西民间刺绣在具有风格淳朴、色彩鲜明、用线较粗、针法奔放等共同特点的一面外,同样是翎毛花卉,同样是动物植物,但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又有细微的甚至很大的差别。该书通过大量的图片及细致的分析,使读者对此有了深切的体会,也促使读者对这些绣品以审美形式蕴藏着的深层文化内涵做进一步的挖掘。这一著作的学术分量正体现在这种研究中。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绣品本身进一步扩及它的作者——广大的农村妇女。这些终日操劳而又心灵手巧的劳动妇女,一针一线,创造了精美的绣品。本书所选作品,都不是为了赚钱的商品,而是劳动妇女为她们自己、为亲人所用而制作的。它不同于近代市井的作坊绣,也没有现代商品经济时代利益的驱动,而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是她们心灵的诉求。用鲁迅的话说,这就是“生产者的艺术”。本书研究了陕西农村妇女所处的自然、社会生存条件,并从社会心理、历史环境、传统制约和生产技艺进展等综合关系,去把握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农村乡俗刺绣艺术现象。例如,书中选了黄陵县店头乡高水琴绣的“坐垫之虎纹”,侧面虎头的轮廓造型上有一对只有从正前面才可同时看见的眼睛,使老虎有一种古怪而奇绝猛烈的气质,我们在赞叹不已时,再看书中举出的古代文物上(陕西绥德出土汉画像石、江苏徐州出土汉画像石、湖北出土战国漆器)的虎纹,原来两千多年前中国许多美术品上的老虎就是这类处理方法。这说明,这些作品既展示了劳动妇女的创造力,也是厚重的传统文化根脉的延伸。
书名《母亲的花儿》,据编著者说,因为在民间刺绣这种艺术中闪烁的是一种母性的热望、慈爱和责任心。民间美术作为美术最基础的层次,保持着人类创造文化的最初形态,它是根性的艺术、母体的艺术,既是艺术之源,又是艺术之流。这样理解,这个书名似乎就含有更深长的意味。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包括民间刺绣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处境日益艰难、衰退,即如本书所收的东西,许多已成绝品,而一些繁复的技艺也有失传的危险,因此社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即母体文化的保护,政府也启动了规模巨大的保护工程,其意义自然是十分深远的。
原题为《母亲的花儿与母体艺术的保护》,
原载2004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留住”与倾听
几年前,王六拿来厚厚的两本书给我——他新出版的《把根留住——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上下册,这使我大为惊讶。一位公务繁忙的地方干部,竟能成就如此著作?翻阅一遍,更觉不易,还没见有人如此梳理著录过陕北方言,自认为这书对语言文化的研究无疑极有价值。但没有想到,这样一部很专的书却颇受欢迎。前几天,王六又拿来更厚的两本书给我,他说他也没想到一版发行后居然脱销了,很受鼓励。于是校改、增补、再版。再版时把书名也改了,改成《留住祖先的声音——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由故宫出版社出版。
其实何止三千条?方言成语是三千条,但每条成语的使用举例更是地道的陕北方言,再加上注释,又引出一连串的方言词语来,按目录索引,竟有方言词汇一万多条!以三千条陕北方言成语为纲,以一万多条陕北方言词汇为目,还有一千多条陕北民谚俗语,再穿插陕北民歌、剪纸、风土人情图片,洋洋一百二十万字,是典型的陕北方言大荟萃,陕北人文小百科。
不同的区域有各自的方言土语。陕北方言有自己的两大特点:一是富有音乐美。陕北方言讲究修饰、节奏:蓝个茵茵、黄子腊腊、软忽绍绍、硬卜拉拉、明忒眼眼、明的朗朗;更有将一个字读为分音:绊——不烂、团——突栾、杆——圪榄;或将两个词读为合音:不要——biào,不如——bùr。二是直通古代。在陕北方言里,在王六的这部书里,能够听到古代的声音,能够听到方言与文言古语的对话,能够看到浓厚的大中华色彩。我们现在只能从古书古文言里读到的字词,突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陕北老人们的口语里,出现在这部陕北方言辞书里。像被《辞海》归为书面语言,或干脆未收录的词汇,在陕北方言中却鲜活使用,如《诗经》中表旱神的“旱魃”、《老子》中表不善义的“不谷”、《左传》中表祈褫消灾之“禳”、商鞅变法后秦军割耳邀功的“杀割”、帝王躬耕之专用词“耤”、梵文女居士之音译“优婆夷”,等等。至于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史实直接作为成语、民谚使用的则比比皆是:周赧王、岑彭、马武、吴越之仇、胡搅胡、汉搅汉、日南交趾、成古化年、西洋景儿……从这些似曾相识的方言词汇中,我们仿佛听到历史长河的金戈铁马,清晰看到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之壮美画卷。
究竟是古代的书面语言筛选了那时此地的方言口语,还是口语方言口口相传传播了那时的文言?这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话语现象。就像我们在吟诵或聆听陕北民歌信天游时,会想到《诗经》、古诗里的比兴与意韵。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书对研究古汉语、古文化,对研究现代汉语、推广普通话,研究从古至今的语言流变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由此还会想到历史是什么、历史在哪里这样的大命题。历史是文字记载的还是口口相传的?历史在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人的口中?哪一样更真实?更有味道?至少有相当部分的历史真实,记录、隐藏在口口相传的言说中;有更多历史的风俗、习惯、情意,隐藏和流动于口口相传的言说里。尽管有口语流传,但由于缺少对方言的文字记录,因此而流失了许多许多文化符号、文明纹络。也正因此,方言才有了集体记忆的重要价值,方言才有了寻找历史真实的重要价值。以方言为载体的民谚、民谣、民歌,乃至民俗、俗语才理应成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保护。2012年,文化部将陕北审定为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北方言自然成为破解这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基因、文化密码的钥匙。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梳理和研究陕北方言的大书显然是求之难得的。
这部书为什么赶在了点上?为什么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为什么出自非项目课题、非专业人员之手?这与陕北封闭的地理、开放的历史、传统的民风有关,与作者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浓厚的文化情结有关。长城黄河在陕北交汇,大漠草滩与黄土高原在陕北交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在陕北交融,黄帝陵绵延不绝的香火、李自成改朝换代的闯旗,赫连勃勃“美哉斯阜”的感叹、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悲歌,使陕北文化代表性、典型性相得益彰。王六是陕北文化核心区绥米之地的米脂人。他以知青下乡步入社会,种过地,当过兵,挖过煤,卖过粮,教过书,当过村干、乡干、县长、县委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对母语的生命感悟、交流商洛工作后距离产生之美感,使他对传承历史文化有份不能自已的冲动和自觉。
是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正日益成为有识之士严肃思考的课题,也成为政府守护中华文明的责任。今天我们能读四书五经、吟唐诗宋词,徜徉于中华文明大美意境之中,实在是一大享受,这关键在于“留住”。陕北方言成语三千条,留住了祖先的声音,多一份中华文明之多元多彩,让我们有机会打通时空隧道,与古代对话,倾听历史回音,是为善举也。
原载2013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