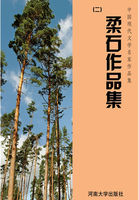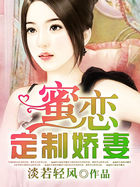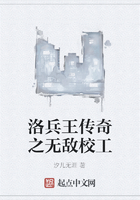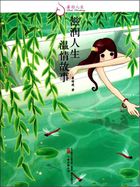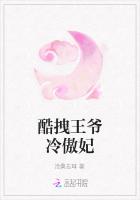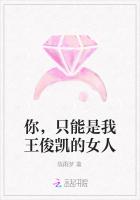以色列散记
一 和平的祈盼
当亲友知道我要去以色列时,无不感到吃惊。这时还是2001年的4月。《中国百件珍宝展》将于8月13日在以色列博物馆展出,我要带一个代表团参加开幕式。亲友的担心不无道理。2000年9月28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参观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圣殿山,引发了与巴勒斯坦持续至今的暴力沖突,不时你死我伤,使这弹丸之地为世瞩目。“危邦不入”,这是孔夫子的古训,但去以色列是工作,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我们只祈盼届时局势能平静下来。5、6、7三个月,以巴冲突愈演愈烈,你爆炸,我报复,你反击,我偷袭,轮回似的事件接踵不断。8月4日,以巴双方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连续攻击的炮火不时划破暗夜的长空,又使即将整装待发的我们心头布上了一层阴霾。征求过我驻以使馆意见,回答说安全没问题,展览可如期进行,我们遂于8月9曰踏上了赴以色列的征程。
我们乘的是以航班机。安检十分严格,但主要是和乘客面谈,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安检人员始终保持的微笑使乘客感到不是审查,而是平等的对话,从而保持了应有的尊严。我们在以色列驻中国使馆一秘安吉道先生的通融下,免去一些程序,顺利过了这一关。据说以航的安全系数相当高,当与这套严密的检查制度分不开。飞机上的服务相当周到,令人有种温馨的感觉。十多个小时的穿云破雾,飞越重洋,薄暮时分我们一行安抵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等待我们的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今天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座快餐店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至少十五人丧生。这是该市近年来最严重的爆炸事件。当时我随展人员正在以色列博物馆布置陕西杨家湾出土的陶兵马俑,以方在确知代表团上了飞机才告诉了这一消息。
车行驶在去耶路撒冷的高速路上。地中海潮湿的热气使我们感到不太适应。大约个把钟头,车子驶入耶市,透过车窗,不时看到公路两旁挂着有关中国展览的宣传画,秦始皇陵跪射俑的凝重与京剧旦角的花俏在同一张画面上相互映衬,在这异国他乡分外引人注目。看来以色列同行已为展览做了充分准备。但是会有观众吗?文物会安全吗?我们思忖着这难以预料的一个个问题。
事实证明,我们有些过虑。《中国百件珍宝展》开幕式是成功的,观众如潮,我们在各地参观时也没遇到什么危险,外界沸沸扬扬的传闻与实际是有一定距离的。但说实在的,那种弥漫在以色列空气中的“火药味”使人总是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我们来时,曾请教在我驻以使馆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她说,到了以色列,如果在路上看到丢弃的箱包千万别动,说不定那就是危险品。来到以色列,也听到这类劝告,自然慎之又慎,不敢稍有差池。我们庆幸未遇上爆炸,但爆炸的消息仍不时传来。在展览开幕的头一天,海法市的一家咖啡馆又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肇事者当场毙命,三十六人受伤。
在以色列,经常见到荷枪实弹的军人和巡逻的军车,其中女军人占比例不小。我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狮子门,门洞中停着一辆军车,两名男军人和一名女军人仔细盘查着进出的车辆,并认真做着记录。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好,应我的请求和我一起合影,其中一个小伙子把冲锋枪横端在手里,蹲在我的面前,列出威严的架势。看样子他们经常与游客照相。我在特拉维夫市,见到的军人更多,有的在路上抽烟,有的三三两两边走边聊,举止有些散漫,但这支队伍却很会打仗。以色列为了自身的安全,付出的代价相当大,那就是全民武装,枕戈待旦。
在以色列博物馆,每个保安人员都配有枪支,严格检查着进馆参观人员。我与一个腰间佩着手枪的二十来岁的女保安攀谈起来,她说曾在特种部队受过训,现在服役期将满,准备上大学。以色列实行征兵制和后备兵役制。按兵役法规定,以色列男女犹太青年和德鲁兹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应征年龄男为十八至二十九岁,女为十八至二十五岁,服役期男为三年,女为二年。除特殊情况外,所有适龄青年必须从军。适龄青年一般在中学毕业时入伍。每名士兵在服完义务兵役后被编入一个后备役单元,男子服役至五十五岁。以色列社会军事化程序之高,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整个社会犹如一座兵营。
在与一些以色列同行谈到巴以冲突吋,他们顾虑最多的是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有人担心自杀炸弹使自己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有种恐惧感。以色列博物馆的比特曼,这位在纳粹魔爪下侥幸逃生的女士,也像政治家一样向我们认真解说,强调以色列必须采取强硬态度,才能消除不安全感。她举例说,以色列必须占领戈兰高地,因为这块山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它关系到加利利海和胡拉谷地的安全,也关系到作为国家供水系统主要来源的约旦河的控制问题。
比特曼女士的观点很有代表性。犹太人在历史上受尽磨难,流离失所二千来年,二战期间又遭到纳粹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处在二十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它的出入也很有限,除了一条通往欧洲的路外,别无门户。
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是令人扼腕与同情的。但巴以冲突的实质是利害问题。按《旧约》的说法,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生的儿子叫以撒,以撒生了十二个儿子,他们变成了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祖先。亚伯拉罕(阿拉伯人称为易卜拉欣)与撒拉的埃及使女夏甲生的儿子叫以实玛利,后来夏甲母子流落到阿拉伯半岛,以实玛利就成了阿拉伯民族的祖先。
这个故事在《古兰经》中也得到了认可。传说只是传说,但从民族学角度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属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至今两种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争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兄弟阋于墙”。在过去一千多年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当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源源不断地移居巴勒斯坦,并在l948年建立以色列国后,他们的成功却成为巴勒斯坦人悲剧的开始。过去无家可归的犹太人有了归宿,已在此地繁衍生息了一千三百余年的上百万巴勒斯坦人却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巴以的频繁冲突,成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及它的支持者美国的对立与斗争。中东是我们这个不平静的地球上的“火药桶”。
巴勒斯坦人根本不是以色列人的对手。据说以色列约有二百枚核弹,每颗核弹的威力比投到广岛的原子弹大十倍,而巴勒斯坦只有区区三万支冲锋枪和少量子弹。但是,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生活水平低下,失业率长期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自然难免出现“慷慨悲歌”之士,而长期形成的战斗性格与烈士心态,更使其不惮于以色列的暴力,常用“人肉”炸弹之类向以示威。以色列提出扩大定居点,但暴力浪潮使从这里移民国外的犹太人数目倍增。2001年2月,沙龙当选总理时承诺将给以色列带来“安全”,但他显然无法做到。经济不景气,旅游业萧条,人心浮动,这都是明摆的事实。我在耶路撒冷老城东边参观时,看到一栋楼房上悬着一面蓝白两色相间、中间是大卫盾牌的以色列国旗,旗子的下面竟乱涂着红油漆。据说这是沙龙的住处,旗上的油漆是阿拉伯人涂抹的。为什么沙龙不换一面新旗子?大约是对那些对他充满仇恨目光的阿拉伯邻居无可奈何的缘故。滥用武力和崇尚暴力只能事与愿违。就在8月9日耶路撒冷那家餐馆发生爆炸后,聚集在附近的一些人大叫要进行报复,另外也有一些人则手举“不要报复”、“报复只能导致血腥的恶性循环”等标语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之间谁也消灭不了谁。理性地抛弃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逻辑,才能迈向长久的安全与和平之路。
不仅犹太人需要和平与安全,巴勒斯坦人同样需要和平与安全。就在我们到达以色列的那一天,一批“国际团结运动”的志愿者在巴勒斯坦开始了为期十天的被占领土之行。他们的活动目的是关注巴勒斯坦的被占领状况,并呼吁以色列结束封锁。来自美国犹太人社团的年轻的伊雷娜·西格尔向记者说:“我是犹太人,我支持以色列,但我无法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非法和野蛮的占领。”同为美国犹太人的萨拉·西蒙说,事实上,美国很多犹太人并不是盲目支持以色列,很多犹太团体,包括他们俩所在的团体,都坚决支持中东和平进程,要求以色列结束占领。国际上对以色列向巴施暴的行为多有谴责。就在以色列,也有一些青年人拒服兵役。
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正确途径是执行有关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这就首先要求双方坐下来进行谈判,彼此让步,实现和平共处。8月13日《中国百件珍宝展》开幕式上,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提前到会,他径直走到临时搭建的大厅,与好多人打招呼,有人关切地询问与巴勒斯坦会谈的问题。这几天以色列电视台报道,这位几经沉浮、屡仆屡起的政治家提出与巴方直接会谈,但沙龙不同意。以沙龙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同以佩雷斯为首的左翼工党是联合政府的主要执政伙伴。利库德集团一贯主张“以安全换和平”的立场。身为外长的佩雷斯坚持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反对将巴勒斯坦人逼上绝路和对巴大打出手。近来他公开挑战沙龙的“不停火不谈判”的立场,扬言政府若再不同意与巴领导人就停火进行谈判,工党将退出联合政府。在我们离开以色列的8月25日,沙龙被迫妥协,同意佩雷斯同巴勒斯坦直接进行谈判。但从中东和平几十年步履蹒跚的历程来看,恐怕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不会那么顺利。
8月的特拉维夫骄阳似火。我们离开以色列前,专程到这座椰风海韵中的美丽城市,参观了前总理拉宾遇害的纪念地,瞻仰了他的塑像。拉宾是为实现巴以和解、推动中东和平而献身的。他接受巴人提出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使中东和平出现曙光。1994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签署“开罗协议”,次年又签署了“扩大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的协议”;1994年,以色列与约旦签署了结束两国战争状态的“华盛顿宣言”,实现了两国的和平。那是一段令人鼓舞的日子。拉宾从一个与阿拉伯人厮杀打拼的战争英雄变成了奔走呼号的和平斗士。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同时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极端分子反对并阻挠和解的潮流。1995年11月4日晚,十万以色列群众聚集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会。拉宾、佩雷斯与内阁成员都出席了集会,拉宾在讲话中提出一定要抓住和平的机会,批判破坏中东和平的敌人,向全世界传达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的信息。拉宾以和平的呼喊结束了后来被称为他的政治遗言的演讲,并同与会者唱起已成为和平运动象征的《和平之歌》。当拉宾离开会场来到自己车旁,忽然遭人枪击,凶手是反对以色列人同阿拉伯人实现和平的以色列极右分子。鲜血染红了他脚下的国王广场,一个伟大的生命停止了呼吸。他死在了人类可怕的偏执和愚昧。已扯起风帆的中东和平进程又是磕磕绊绊的一步三折。
拉宾遇难处已建起正方形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有人们敬献的鲜花。从拉宾黑色的肃穆塑像看,他的眼神饱含着希望与祈盼。他的希望与祈盼也是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希望与祈盼。这时,我想起了佩雷斯在拉宾葬礼上所致悼词中引用《圣经·耶利米书》中的一段话:“耶和华告诉大家,不要失声地呜咽,不要让泪水遮住视线,所做主工必有回报,未来充满希望。”可以肯定地说,中东和平、巴以消除宿怨是充满希望的。
二 安息日
我们星期四来到耶路撒冷,第二天上午便匆匆赶赴以色列博物馆。因为《中国百件珍宝展》再过几天就要在这座以色列最大的国家博物馆展出,而陈列布置中的有些问题尚需研究解决。中午,詹姆斯·施奈德馆长陪同大家在博物馆用餐,并邀请代表团到他家共进安息日晚餐。这是日程上早已安排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