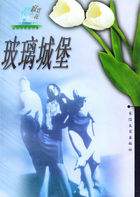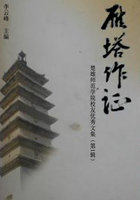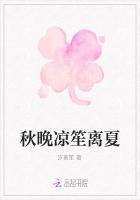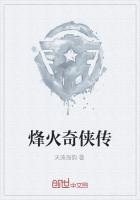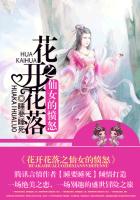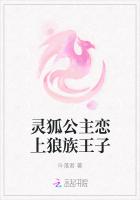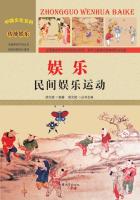犹太人给全世界带来了六天工作、第七天礼拜和休息的工作周。从每个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犹太教徒必须停止工作,专事敬拜上帝的休息、祈祷、学习等活动。这一天就是安息日,它是神圣的,因此也称为圣日。犹太教的节日很多,最重要、最特殊的当数安息日。引起我很大兴趣的是安息日的诸多令人不解的禁忌。在这一天,犹太人不仅全天不工作,不做生意,不购物,不旅行,不娱乐,不烧煮,而且也不能抽烟,不携带钱款,不生火、灭火,不开灯、关灯,不按电钮,不走长路,不准乘车或利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到犹太教会堂,停在港口的轮船不准起航,等等。提前十多天来以的我方布展人员对此深有感触。比如,安息日犹太人不工作,我们的布展工作却不能停,为了赶上开幕时间,还得加班,但展厅的电梯这一天不开,有着偌大包装的展品就无法运到展位。有一个安息日,我们一位同志乘电梯,电梯门关上后,他就习惯地摁了自己所要到达的楼层号码,奇怪的是毫无反应,电梯内的其他犹太人则对他怒目相向,弄得他一头雾水。后来才明白,这是安息日专用的电梯,设计了每层都停的程序,且在星期五日落前就开动了,不管有人没人,它都会在每层停一下,如此上上下下,直至安息日结束。即使你住最高层,也只能耐着性子慢慢上,摁什么都不管用。安息日晚餐是犹太人一周里最丰盛的一顿晚餐,馆长请我们在他家共进安息日晚餐,这是对客人的尊重,也是我们了解、体验犹太人生活的一个好机会。
詹姆斯·施奈德馆长是美籍犹太人,在纽约现代艺术馆工作了近二十年,当过多年副馆长,聘任到以色列博物馆也四五年了。他的妻子、女儿都在美国,自己孑然一身租住在紧邻耶路撒冷剧院旁的一栋小楼。这栋建于l926年的阿拉伯风格的三层楼房,在当地还颇有名气,不仅因为楼前有葱郁的草、鲜艳的花,楼后有耶市不多见的名木荟萃、果实累累的袖珍小果园,还在于它的房客多是些显赫人物。它在英国“托管”时期,曾是英空军负责人的住所。以色列建国后,三层曾为以色列国的创立者和第四任总理果尔达·梅厄的寓室,二层住过总理办公室主任,一层住过大法官。施奈德先生现租住第一层。从我们下榻的因堡饭店到施奈德先生住处不算远,步行也用不了二十分钟。来接我们的瑞贝卡·比特曼女士提议,大家不妨安步当车,领略一下耶路撒冷安息日到来前的风情。我们穿过一条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石头楼房都不甚高,在太阳的余晖里反射着金色的光芒,而且很快地愈来愈暗淡,掩映着楼房的树木也渐渐地失去光泽,院子铁栅栏门上卧着的几只猫儿在探头探脑,道两旁停满了小车,行人很少,偶尔有一两辆出租车疾速驶过。夜幕降临,喧嚣了一天的街道变得沉静起来。这一切都表明,安息日到了。
为了今夜的晚餐,施奈德先生特意请了两位女士帮助准备。除了中国代表团一行七人外,加上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及其夫人,还有博物馆的人员,共十二位。我们坐在铺着洁白桌布的长条桌子两旁,点燃了烛台上的蜡烛。桌上摆了酒杯和盛着白面包的盘子。施奈德先生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后,端起白面包的托盘,请中国朋友无论如何要吃一点。安息日晚餐虽然丰富,最重要的是吃白面包。犹太人管这种拧成麻花式样的白面包叫“哈拉”,通常要吃两个,据说是纪念犹太人在西奈旷野流浪时上帝赐予的“马纳”的两部分。这种白面包除了面粉,还掺和了糖、盐、鸡蛋清、植物油以及一些果仁碎片,吃起来十分可口。
在安息日晚餐上,我们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安息日。这天人们之所以要休息,大致有两方面理由。一是因为上帝用了六天造成天地,第七天便安息,所以摩西《十诫》第四诫说:“六日要劳碌作你的一切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因此“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二是安息日同上帝“救赎”希伯来人的历史相关联。《申命记》中写道:“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就是说上帝把希伯来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从埃及带到迦南,找到了一个安歇之处,为了纪念它,希伯来人受命定时休息。出埃及是犹太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犹太教的逾越节、住棚节等重大节日也都与此有关。在犹太教中,一天不是从日出开始,而是从日落开始,所以,安息日便从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时为止。
施奈德先生并不是犹太教徒,但作为犹太人,他也很重视这个节日。他邀请中国朋友在他家共进安息日晚餐,因为以家庭为中心过安息日是最重要的习俗。据说在“巴比伦之囚”以前,在犹太人心中,安息日远不及其他宗教节日重要,后在流浪中其他节日都不复存在,安息日就变得愈发重要了。后来严守安息日被视为子民与他们的神所立之约的独特记号,不能违背。在犹太教看来,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的生活是神圣的。让所有生活圣化是犹太教伦理的一个特点。安息日的许多仪式都有圣化的意义。在家中过安息日,完成有关的活动,既给人一种尊拜上帝的机会,也使人增强了在陌生土地上的整体安全感。这说明,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表现为道德行为规范和生活习俗的制约。直到今天,家庭在安息日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它既是安息日庆祝的中心,也是家庭团聚的中心。在信奉宗教的犹太人看来,安息日的种种戒律并非负担,而是使人们脱离日常工作的艰辛,全身心地休息,精神上得到更新的一种保证。数千年来,这些戒律已成为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遵守这些传统与习俗,既是作为犹太人的一种标志,也是保持民族特性的一种手段。正如有人所说:“与其说以色列人守住了安息日,还不如说安息日保住了以色列。”
安息日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但休息并非唯一目的。因为在犹太人看来,不禁止工作就会侵扰圣化的过程。祈祷与研读誓约是安息日活动的主要内容。安息日早上,一群群穿着犹太宗教服装的男人带着行过成年礼的儿子,一起步行去教堂集会,进行晨祷,诵读经文,午后研究圣典,在傍晚第三次热闹异常的圣餐中,人们也相互叙述研究经典的心得。这一天是世俗的圣化也是宗教的生活化,弥漫着亲情又充溢着理性,因此是轻松的也是庄重的。
我们参观以色列博物馆里反映以色列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文物,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制作精美、历尽沧桑、大小不一的七杈灯台。它有七个灯座,可以盛油或插上蜡烛,系犹太教的礼仪用具,后成为古代犹太教的徽号。这七杈烛台中,六枝象征上帝创造天地六合,中央较高的那枝就代表圣安息日。公元前516年,首批回归锡安的犹太人重建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并在圣殿至圣所安放了这一座七杈金烛台,后在罗马入侵后下落不明。三千多年来,这七杈大烛台一直是犹太人的象征,在无数地方、以各种形式成为犹太遗产的象征。今天,这以七枝灯台为中心图案的盾徽已成为以色列的国徽。从博物馆望去,不远处以色列议会大厦入口处,很醒目地矗着一座青铜制作的1.524米高的七杈大烛台,在夕阳余晖斜照下闪闪发光。这更使我们对不同寻常的安息日的重要性有了认识。
安息日如此重要,对犹太人来说,那自然马虎不得。凡是亵渎安息日(即工作等)的要判死罪。《出埃及记》说:“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须把他治死。”教条式地对待戒律必然产生偏颇,走向极端。在马卡比家族领导的以色人时代(公元前2世纪),对安息日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一群犹太人受到敌人攻击,只因为这一天正是安息日,他们就宁死也不抵抗,结果一千余人惨遭杀戮。血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不能束手待毙,遂商定,在安息日遭到攻击时也应迎战。《圣经》后的犹太教律法用了大量篇幅,具体地规定了在安息日禁做的种种事情,计有三十九条之多,不过也可变通,以保证生命或维护健康。但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耶稣因主张在安息日行善事并为穷人治病,经常受到墨守律法书上教条的法利赛人的攻击。有个安息日,耶稣和众门徒从会堂讲道出来,一个门徒因肚子饿,便在经过的麦地里掐了几个麦穗用手搓着吃了,法利赛人就责问耶稣,认为耶稣门徒违反了两条戒律:掐麦穗相当于收割庄稼,搓麦穗相当于在麦场打麦,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耶稣反对这种不重视摩西律法要义的僵化态度,便用《圣经》上记载的大卫及其门徒在紧迫和饥饿时吃了除祭司外不允许吃的陈列饼予以反驳,并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在安息日为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治好了病,有人问耶稣,安息日是否可治病,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圣经·新约》上的故事。
当我们享用了丰美的安息日晚餐,在清凉的晚风吹拂下漫步返回饭店时,看到大厅一侧摆着一个木平台,上面是排列整齐的小蜡烛,千百支烛光汇在一起,十分壮观。这大概与安息日有关。第二天在饭店用早餐时,我们发现除了咖啡是热的,其他饭菜都是凉的,餐厅里忙碌着煎鸡蛋的厨师也不见了,一片凄清景象。先是惊愕,继而想起,今天是安息日。安息日安排我们参观耶路撒冷老城。导游张先生说,本应是外交部给我们派车,由于是安息日,虽无明确规定,但还是没有派,加上要去东城,那是阿拉伯人的世界,外交部的车也易惹麻烦,因此张先生要我们改坐出租车。今天会有出租车吗?有的,可坐穆斯林的。真有意思,穆斯林的安息日是星期五,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基督教的安息日是星期日,三天互不相扰,各得其所,大约也是上帝的旨意吧。在老城犹太人的居民区,店铺全关了门。在著名的哭墙,成千上万犹太人聚在那里,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诵读经文,那如痴如醉的情景,使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体验的游客也感到不小的震撼。晚餐是外交部请客,说好晚上八点,但是九时以后才派车来接。饭店在新城一个步行街的入口,我们晚上十一点离开饭店时,那里仍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据说这还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安息日结束了,新的一天到来了。
短短几天,想要对一个不平凡的民族与它的历史久远的宗教有较多的了解是不容易的,我们所见所闻毕竟有限。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像安息日这样的宗教节日,今天还能像律法书上要求得那么严格吗?犹太人在近两千年的大流散时间里,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的唯一纽带。在现在以色列犹太人中,大致有一半人程度不同地信仰宗教,另一半即所谓的世俗犹太人。即使犹太教徒,也有正统派、传统派和改革派之分。正统派犹太教徒主张严格遵守犹太法典,追求极端的虔诚的宗教仪式上的纯正,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世俗国家。我在耶路撒冷老城里看到过这类中的男人,他们在8月炙热的阳光下也穿着黑色大衣,戴宽边黑圆帽,不刮胡须,年轻的则把两鬓的头发蓄得很长,在快步行走时鬓发随意飘动着,目不斜视,旁若无人,很是奇特。保守派意见不一,其中有的主张加以变通,比如允许安息日旅行。改革派极力要求宗教适应现代社会,甚至有人主张废除老传统,改在星期日举行会堂礼拜。世俗犹太人对安息日的神圣看得并不很重要,他们依然娱乐,依然进行社交活动。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等城市,许多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常常在安息日聚集在他们的居住区附近,向过往的汽车掷石头,殴打安息日进行娱乐的人,到电影院寻衅示威,结果引起暴力冲突。以色列是以一个世俗国家的面目出现的,安息日是官方法定的休息日。世俗与宗教在以色列人中造成了两个世界。反映在安息日上的冲突,其实是宗教和世俗斗争的一个方面。在以色列生活了十多年的导游张先生说,这个由来已久的冲突是不会停止的。我同意他的看法。
三 挥之不去的梦魇
把参观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安排在我们最后离开耶路撒冷之时,我以为以色列同行是有深意的。一周紧张的参观访问,我们大致了解了这个民族久远而又受尽磨难的过去,目睹了这个新生国家焕发着蓬勃生机的今天,目不睱接,感受甚多。但是我觉得,主人想给远方客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百万人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横遭屠戮的惊世惨案,这是犹太民族永远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也是人类需要不断反思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