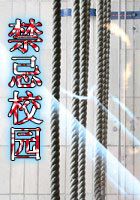既然和谢老转同流合污的人有名有姓,那抓住一干人犯当然也就不是什么难事。李一光、尤艺敏,包括李红发也未能免了干系,连同谢老转一起,统统给逮捕归案。李红发自觉很冤,他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发善心收留这个谢老转,谢老转怎么会想得起来把自己供出来,尤其是自己还无缘无故地多了一项窝藏罪犯的指控,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好在自己口才可以才免了一场窝藏冤案。这几个人本来就算不上什么顶天立地,稍一审问,相互之间的勾当就像袖口里的豆子,痛痛快快地倒了出来。就连王燕也没有逃过尤艺敏的嘴巴,王燕也是一样,一张嘴就把苏强给抖落了个底掉。苏强只是个村里的光棍,哪见过什么大场面,刚一进审讯室没等屁股坐稳当刘振清的事就交代了一个明明白白,刘振清一到场,任建规哪里还有逃脱牢狱之灾的道理。
事实清楚,几个人也供认不讳,没多久法庭就宣判了。
这是几个聪明人,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为自己捞取了万贯不义之财。也是因为他们的聪明,最后连本带利赔了个精光,包括自己的自由。面对数年的囹圄之苦,他们在想什么呢?是无边的忏悔吗?事到如今,再深刻的忏悔对于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无数的教训在他们的身边发生着,凭着他们的聪明,他们怎么会不心知肚明呢?但是他们在进入铁窗之前,他们一直都有着强烈的侥幸心理,而这种侥幸心理都不折不扣的建立在他们的聪明的基础之上,他们不知道过分的聪明就是愚蠢的道理,他们这是自作聪明。有道是天作孽犹可免,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多少年来多少人用血泪总结的真理,而他们所忽视的就是这样一条尽人皆知的真理。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普通的人做任何事都有一定的目的性。他们捞取钱财,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生活得更幸福,但当他们第一次尝到不义之财的甜头的时候,这种物质的欲望便会迅速膨胀一发而不可收,浑然忘记了刹车,于是他们失去了当初的目的,攫取了自己几生几世也挥霍不尽的财产。他们霸占了本应该属于别人或是社会的财产,侵犯了别人的幸福、社会的和谐,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的这种没有限度的掠夺付出代价,甚至是惨重的代价。这就是社会,这就是法治之下的社会。
经过五年的铁窗生涯,谢老转终于刑满释放了。他提着简单的行李,按照李红发临出狱前给他的地址,步履蹒跚地找到了夏冰。还好,夏冰终究还念着过去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过的情分,让他当了门卫。从此,谢老转便安分守己地给夏冰看起了大门。
这是一个寒冷的深秋,枯黄的树叶在凛冽的寒风中颤抖着,冰冷的秋雨挟着寒风的威势,来回卷荡着还残留着些许黄叶的树梢,那一息尚存的黄叶任凭寒风的蹂躏,呜咽着飞向半空,最后坠落尘埃。尘埃的残酷更胜过秋雨的冰冷,它们无情地埋葬着纷落的黄叶,直到黄叶失去踪影、腐烂。
一个瑟瑟发抖、心神不定的身影踯躅在这样没有丝毫温暖的街头上。她右手拄着一条弯曲发黑的木棍,左手斜端着一只破碗,无神的双眼东张西望着,或许是在寻找着能躲避风雨的角落,或许是在寻找着能够讨点残羹剩饭的人家。最终腹中的饥饿还是战胜了寒冷,颤巍巍地把脚步挪向了一扇紧闭的大门前,然后伸出黑糊糊的手指,无力地敲响了陌生的铁门。铁门闪开一条窄缝,一条浑身雪白的哈巴狗呼地一下冲到缝隙前,呲开一口本不锋利的牙齿,清脆冷峻地冲着打破它们安宁的这位不速之客怒吼。狗的主人蓬松着头发、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揉着惺忪的眼睛随着狗的叫声向外张望,然后回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一个馒头飞出了门缝。乞丐见了馒头,扔掉木棍,飞快地从地上捡起刚刚停稳的馒头,也不顾馒头上裹着雨水尘土,三口两口吃了一个精光,然后她伸出舌头舔了舔尚存一丝馒头香味的嘴唇,暗淡的双眼感激地望了一下那早已紧闭了的铁门,拾起木棍,斜端着破碗向另一家走去。
她,就是耶秋萍。
谢老转那爆发式的一刀,差一点要了耶秋萍的风流命,但是救护车及时赶到,经过医生抢救,她才勉强逃过了一劫。但是,那天的那个没有丝毫血性的男人经不住血水的考验,在一路狂喊“杀人啦”的悲声里,永远地疯掉了。他的家人没完没了地把耶秋萍在法院里告来告去,最后以耶秋萍赔偿一百万了事。墙倒众人推,这时干儿子辛海青因为生意赔了本钱也找到了她这个已经几年都没见过面的干妈,明说是借二百万还账,可从这小子的目光中耶秋萍分明看到了仇恨的血丝。但是此时的她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求得这位昔日干儿子的饶恕。也许是出于曾为一个半老女人失去处子贞洁的羞恼,辛海青英俊的脸上竟闪现出屠夫般的暴虐神色。这样的神色意味着什么,耶秋萍当然心里清楚,她害怕了,她害怕再受到菜刀的攻击。于是,她翻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但由于她极度的挥霍,家里已经只有一百二十万了。辛海青狞笑一声:“正好,这套房子还能卖个百八十万。”就这样,她被自己曾经百般爱抚的干儿子扫地出门了。
她虽然已经落魄,但并没有失智。她知道义子尚且如此,那些曾经为了升官发财百般讨好过她的小爬虫们更不会对她有丝毫的怜悯。从此,她便开始了她流浪街头、居无定所的漫长生涯。
长时间的流浪生涯使她的良心终于又回到了她的躯体里。她要找到丈夫,找到那个曾经因为自己而颜面丧尽、锒铛入狱的丈夫,她要当着他的面向他请求宽恕,不管他是否能够宽恕自己。她首先来到了省监狱,但是监狱的人说,她要找的人早已刑满释放了。她茫然了,她怎么能知道一个刑满释放的人走出监狱不回家还能去什么地方?她想到了婆家、他的老家、那个她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回过的老家——安徽省一个贫困的乡村。
她凭着自己对婆家仅存的一点记忆,艰难地行走着。衣服里仅存的零钱很快就花光了,饿了两天两夜之后,她再也忍受不住那难挨的饥饿,从野地里找了一根打狗棍和一只破碗。她趁着肚子里已经有一个馒头垫底,继续向安徽的方向走去。
这常言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更何况耶秋萍在家里一手遮天养尊处优惯了,这种身无分文的流浪日子何曾想过,所以这时的她就显得格外狼狈。本来光鲜的衣服经过多日的风吹雨淋已经是褶皱不堪肮脏透顶了,本来保养娇嫩的老脸露出了应该有的本色,不但皱纹纵横而且污渍斑斑,本来顺直的黑发因为变得干涩杂乱,犹如一头乱草,本来昂扬的头颅像是灌满了铅液沉沉地低垂。握在手里的木棍和那只缺角的破碗也显得沉重了许多,这两件东西目前是她唯一的家当,丢掉它们就意味着死亡,她心里很清楚。看看路标,她知道她已经进入了安徽境内,还好这里的天气要暖和一些,她不至于受冻了,但是浓浓的饥饿却是随着汩汩而下的汗水更加强烈地袭扰着她,无助的眼神茫然地望着眼前不远处一家小饭馆的餐桌,焦急地等待着吃饭的人们赶紧离去,她好像狗一样打扫人吃剩下的冷菜剩饭。好在如今的市面确实繁荣了,人们的残羹剩饭足以填饱她的辘辘饥肠。但是她从家里穿出来的皮鞋却再也不能忍受她无休止的跋涉,鞋底穿了,鞋帮掉了,袜子也磨出了一个连一个的大洞。她只好甩掉鞋子,脱掉袜子,她知道剩下的路她就只能赤脚走过了。赤脚走路是要很大工夫的,不是谁想赤脚就能赤脚的,她那双脚底何曾长有一点点老趼呢,走了不到半个小时,她就觉得双脚生疼,往下看,脚印上已经印上了斑驳的血迹。她无奈地坐了下来,望着漫漫的前途,已经变得浑浊的双眼沁出了混浊的眼泪。但是无论如何,她都要走下去,她要找到自己的丈夫,哪怕是对她说上一句抱歉的话就死在他的眼前,自己也就含笑九泉了。
可是,当她历尽艰辛找到了那个她似曾相识的村庄的时候,她犹豫了。那个村庄自己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来过了,就是自己的公公去世,后来婆婆去世,自己也没有跟丈夫来过一次,想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狠心啊,任凭丈夫泪眼婆娑地哀求自己一起回来给老人送葬,自己也是心如铁石,毫不动摇。如今自己这样狼狈地回来了,乡亲们会像自己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回来时那样热情吗?他们不理我也就罢了,自己的脸已经灰尘满布了,往上吐口唾沫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他们要是故意不认识我那岂不是让我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吗?虽然她的内心交织着这么多的疑虑,但她也知道现实既然如此,那就只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面对了,自己不远千里地回来不就是为了弥补自己以前的一切吗?
想到这,她找个水坑,掬起水坑里有些泛黄的雨水洗掉脸上的尘埃,再用水捋捋头上乱蓬蓬的头发,掸掸身上的灰尘,站起身,还算平静地进了村庄。乡亲们没有像她想象的那么刻薄,朴实的农民压根就没有欺负外乡人的恶习,他们不但告诉了她她要找的人自从他的父母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的事实,而且还做了热腾腾的饭菜让她饱餐了一顿。既然丈夫没有回来,她也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吃完饭表达了谢意,就告辞了善良的乡亲,忧心忡忡地离开了村庄。
但是,她并没有绝望,她那颗强烈忏悔的心还在支撑着她,无论如何她要找到丈夫。可是,丈夫在哪呢?
她坐在村头冥思苦想着丈夫可能去的地方,最后她的思绪还是落到了那座囚禁她丈夫的监狱。于是,她站起来,拖着已经是极度虚弱的身躯,艰难地踏上了回程。
当她到达那坐监狱门口的时候,她已经是羸弱不堪气若游丝了。狱警们听了她断断续续地述说,着实为她的精神感动了,他们为她找到了当时的公安详细地为她回忆了当时拘捕老谢时的每一个细节,指望着由此能够为她提供一个可能的线索。也许是精诚所至吧,她一个瞬间的灵光终于使她断定自己的丈夫就在省城,而且很可能是在李红发那里。
她从监狱那出来,沿着通往省城的大路一瘸一拐、气喘吁吁地挪着沉重的脚步,就在那座城市模模糊糊地展现在她的眼前的时候,她再也走不动了,重重地摔在了冰冷的已浓重的染上严冬气息的水泥路上,木棍甩出去老远,破碗也跌得粉碎。阵阵刺骨的寒风吹醒了她的神志,她咬紧牙关,双手抠着冰冷的水泥路,用着仅存的一点气力,艰难地爬着、爬着……
清晨,老谢看着的那个大门前,直挺挺地卧着一具早已僵硬了的女尸,女尸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灰尘满面,嘴角上血迹斑斑,双手的手指上殷红的血迹早已干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