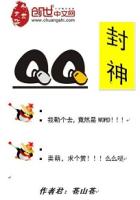雾里笙歌,飘来还散,终于,与她无干了。
兮容坐在窗边,就着月光,写一封家信。她穿一件素色连枝锦的交领长衫,一条黛色素缎长裙,领襟处用烟灰色的素云罗滚了一层细边;头上绾一出堕云髻,髻上只簪一朵丝绢玉茶;脂粉尽扫,神情也冷清清,孤零零的。
月光凄白,映在她的纸上,墨像凝住了一般,又沉又冷。
那信中写道:
父母大人安启,不孝女容跪禀:自离膝前,悠悠五载,倏然似梦。常忆昔时闺中,姊妹厮磨,形影相惜;又绕母承欢,慈颜亲爱。今千里之遥,宫门似海,唯青灯冷月,伴此长夜。容,愚钝懦弱,才智疏浅,无倾城艳貌,难效列女贤操,春秋渐老,君恩不眷。愧父母大人之养,之托。今僻居冷宫,是容咎由自取。幸君王明鉴秋毫,念父亲鞠躬勤谨,未以容之故,牵累家门。容心愿已矣,安身此间,殊无长门之恨,团扇之悲。后与贵妃,虽万人之尊,然与容结交,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有此二姊深顾,想容之余年,亦不至艰难。父母大人当稍宽怀抱,免为容劳心憔悴,更添容之不安。
又逢秋节,明月当窗。伏案作此书,不觉泪随笔下。容之心怀,殷殷想念,笔枯墨尽,亦难尽述。
惟望父母大人垂怜,信此言语不虚。容,肝肠寸断,叩首,再叩首。
不孝女 兮容 字
“娘娘,歇一歇吧。中秋月圆的,奴婢啊,陪娘娘说说话。”说话的是玉宸宫的宫女蕊闲,十七八岁的年纪,着一件浅杏缎交领衫,一条牙色纱长裙,衫子落肩处挨着绣了两朵并蒂素百合;头上简单地垒着一双蝴蝶鬟,余发束在身后,唯有一根束发的淡黄绡绣百合籽流苏小带,聊以装饰。她一面说着,已将一碟豆蓉月饼,一碟合桃酥,一小壶木樨清茶放到兮容手边。
兮容闻声,便将笔搁好,缓缓地回过了头。清秋殿中,寻常只有几个做粗活的老妈子。兮容此际望见蕊闲,想起从前裙钗环绕的绣户光景,才觉出这寂寞。寂寞归寂寞,她也只想念从前的人。
兮容见蕊闲侍立在旁,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遂叹了口气,道:“你也坐下吧,我已不是什么娘娘了。”
蕊闲却不动,只俯首一福,礼貌谢道:“奴婢不敢。”
兮容也不强她,自回转过头,重又执起了笔。
蕊闲见兮容半晌都不说话,方道:“娘娘,往后过日子的东西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已给您准备好了。连除湿的香包都有了,再不怕这地方又冷又潮了。”
“嗯!”兮容只轻柔地应了一声,仍在那纸上划着,头也不曾抬。
“娘娘,有什么想说的么?或是想对二位娘娘说的?或是缺什么,短什么?奴婢都听着呢!”蕊闲试探着,语声比方才更小心恭敬了。
“没有了!”兮容顿了一顿,又抬起头,道:“替我谢谢二位,二位娘娘。还有,还有……”她不自禁地便在那落满了字的信笺上抓了一抓。
蕊闲俯下身,耐心询道:“娘娘是要奴婢将这信交由皇后娘娘或贵妃娘娘,再帮娘娘送出么?”
兮容又斜眼望了望那信,犹豫了一会儿,有些不舍地:“再等一等,下次,下次吧。”
“也是呢!”蕊闲灿然一笑,道:“二位娘娘也说啊,待忙过来中秋,就来看您。”
“多劳她们了!”兮容偶一垂眸,月光正落在她的眉睫间,映出那脆韧洞明的意志,饮伤如砺。
蕊闲瞧着她黯然,失落,故宽慰道:“娘娘,您别难过。皇后娘娘眷顾您,往后日子长着呢。”
兮容摇了摇头,没说什么。
蕊闲一时也没了话,她抬头一望,只见那月亮已越升越高,也越来越明。她又这样默默地待了一会儿,方道:“娘娘,时候不早了,奴婢先回去了。”
“嗯!”兮容点了点头,唇边浮上来一丝浅浅的笑。
“娘娘。”蕊闲又道:“您好好歇着,我明天,再来给您收拾。”说罢,蕊闲俯身一福,才退了出去。
忽地,一阵风起,吹的案上笺纸欲飞,兮容忙用黑石镇纸镇住了。她惊喘未定,那风却吹个不停,云中隙漏下的月光,漫洒如水。兮容置身其中,还是第一次,她这样地看着天上的月,如唔称故,看出了些不一样的东西。人间,呵,迎着这无边皎洁,她竟笑了。
不知什么时候,那把朱漆月琴又挂到了壁上,她触手就能及的地方。
“嗡”地一响,兮容拨动过最粗的那根弦,这声音久久地回来应去着,悠悠沉郁。
她又拨了一声,间杂着上一声的回音,在空中错落地低徊着。
没一会儿,琴弦停了,风声也住了,一切都恢复了寂静。她立在原处,就像做了一场呼呼往来的梦,乘奔御风,游于无穷。
“兮容,兮容。”她正恍惚着,忽听有人在唤她。那声音自渐渐逼来,越离越近。自暗处隐约浮出的轮廓也越来越分明,转瞬就到了眼前。光芒洞开,追魂夺目。
“啊!”兮容惊地一呼,竟昏坐到了地上。心中这一阵壮烈的凸伏,她真愿死了。
“是梦吗?是梦吗?”兮容抑制着不敢呼出声,她不住地颤抖着,眼泪汩汩而下。
那人正是温蕴华,几日忧劳,他已沧桑了许多。他仍穿着御前侍卫的青袍,眼眶明显凹陷了,腮边挂着些零星的髭须,本就秀瘦的面颊越发清削了。也还是英俊,气宇轩昂的。
蕴华俯下身子去扶兮容,兮容猛地抓住了他的衣领,痴痴地瞪着他,却不说话,只是落泪。
“兮容,我来,与你辞行。我就要去边关了。”
兮容缓缓地松了手,蕴华去扶她的胳膊,她却不肯起来,失去了知觉一般,任凭身子向下堕着,一面痛苦地流着泪:“边关,去边关,是服役,服刑?啊!”
“不。”蕴华忙解释道:“皇上恩典我,准我去戍军中供职,步军都指挥副使,明日就要上路了!”
兮容恍惚着,不敢相信似的:“你是说,皇上,他放过你了,还肯,肯让你去军中!”
“嗯!”蕴华见兮容冷静了些,忙将她自那冰冷的地上拉了起来:“皇上他,明察秋毫,有情有义!兮容,事到如今,你不要怪他,啊!”他越说越温柔,眼中泛着酸楚,哀恳依依。
“我谁也不怪,只怪我的命!”兮容将这想法藏了起来,只是望着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嗯!”
“兮容!”蕴华黯黯地一低头,负气道:“兮容,我真是一个愚笨懦弱的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做你该做的吧,你本来想做的,你的武功,你的抱负,我的,我的爱情!”她决绝地说着,眸光晔晔,明艳而坚毅。
“嗯!”蕴华沉重而坚定地点了点头:“兮容,我一定回来见你,只要有你的地方,我一定回来!”
”呵!“兮容沉醉地一笑,双手抱着他的手贴到了腮边,:“我该为你高兴的!我真为你高兴!从前你说金鞍羽箭射单于,将军破虏封侯业。你那时的样子,我一直都记得!你可以去做你的将军了,我的将军!”她笑着,眼中明星迸溅,心满意足。
蕴华也想起了那时的他们,年少的壮志。那时,此时,他若知此生会失去她,兴许早就不做梦了。
他温存地一笑,一只手抚着她腮边滚滚而下的眼泪:“!”
“温大哥,温大哥!”正在二人生离缠绵之际,已有人探了进来,就站在那隔架的帘后,轻声唤道。
兮容猛地抬起了头,脸色被惊的煞白,却仍紧紧地抓着蕴华的手,不愿放开。
“没事的,是明韫!”蕴华一面细声安抚着兮容,一面回头去看。
明韫立在帘后,张望间,脸上仍漾着那薄薄的红晕。他见蕴华回过了头,才又道:“温大哥,咱们该走了!若是让人看到了,皇上也没有办法的!”。他见此情形,心下也替二人不舍。却不得不催促,十分为难痛苦。
兮容闻言,心里陡地冷了。她缓缓放下蕴华的手,目光又恢复了那痴然,茫茫然地,觅向了别处。
“兮容!”蕴华的目光追着她,不忍不舍。
“快走吧!犹豫什么!莫要我,万劫不复!”兮容背着他,一闭眼,横心道。
“兮容……”
“走吧!”兮容抢道,她捂住心口,抑制着不让身子抽颤。
明韫见蕴华仍不肯走,只得走近前来,半拖半拽地带走了他。
兮容不敢回头,也不知那脚步声是什么时候才听不见的。月光照着她单薄的身子,惨白的地上,人世如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