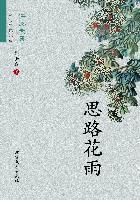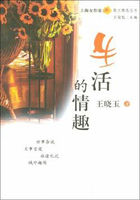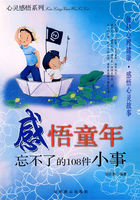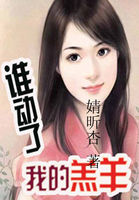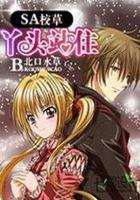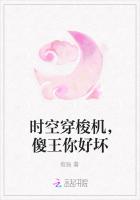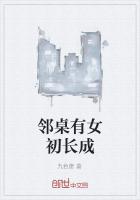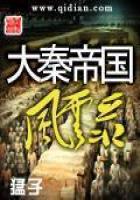文學的主體也就是文學創作與文學欣賞行爲的執行者。中國文論一直注意從作者的角度來談文學,《尚書》所云的“詩言志”也就是言詩人之志,《周易·繫辭下》:“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詩人與詩作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禮記·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正由於詩樂由人心生,所以有什麽樣的人心,也就有什麽樣的詩樂了。
文學屬於精神産品,一個人的精神的形成有種種因素,有氣稟、性情、修習、際遇。宋代對氣質進行修習,對際遇進行超越。宋代道德的要求變得第一重要。先天的才氣剛柔,後天的際遇坎坷,都可以通過道德的固守來填平,而理想的道德是一樣的,道德的最終歸宿必然走向中和平淡。宋代認爲個人修養的中和與否直接關係到詩作的中和與否。宋代重視詩人的道德修養,認爲修養可以養才滋氣,可以使情性歸於中和,這與六朝重先天才氣不同。
第一節 才氣與修習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了氣,這裏的氣主要指人的氣稟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爲人之風、爲文之風。氣論認爲天地皆由氣構成,人亦不例外,人自天稟得之氣,就形成了人之氣稟。與天地之氣分陰與陽相類,人稟之氣,則有剛與柔。{《周易·說卦》有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氣主要指個性、氣質,這些都是人自天稟得,具有先天性,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稟賦。
還有一種屬先天秉賦的主體要素:才。據《說文》:“草木之初也,從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而《六書正僞》說“才,木質也,在地爲木,既伐爲才,象其枝葉斬伐之餘,從木省。”《集韻》通作材。對於材,《說文》“材,木挺也,從木才聲”,徐鉉曰:“木勁直可用,故曰入山掄可爲材者,人之有才,義出於此。”{引自《康熙字典》}這裏可以知道才的本義就是材,於木曰材,於人曰才。這種才就其本質而言則爲質,也就是材質的意思。就人而言,才也就人自天秉得之質。我們可以看出氣與才皆屬質的範疇,但氣更具有元素意味,而質則主要就質料而言的。從前面的材“木勁直可用”的解釋可以知道,才的質料意義的必要條件即是有用性,若沒有可用性,其質料的含義也就失去了。所以盡管才也有質的意項,但“質”的使用情況較少,更多的指“能”,故本章的討論重在於其“能”的方面。
就人之秉賦對詩歌産生影響而言,一是先天的氣質,二是先天的表達能力,那麽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質”,“氣”與“才”皆有此意項,但才就“質”方面而言,與氣相類似,且使用較少,所以我們討論“質”以“氣”爲主。二是能,“才”的使用更多地表現在此一方面,也就與力相類似。所以我們將詩人的先天秉賦分成兩個方面來討論,一是“質”範疇的氣稟,二是“能”範疇的才力。我們先來看看質料意義的氣稟。
一、氣稟與養氣
孟子論養氣,主于修身,未及作文。在文學上,曹丕《典論·論文》率先提出“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主要就創作者的氣秉而言,也就是作者的個性、氣質。氣之清濁也就是指的氣質的剛柔,這裏的剛柔只有類型的不同,而無高下的區別。後來《文心雕龍·體性》
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劉勰在這裏事實上論及了主體的幾個方面的問題:才、氣、學、習、情性、陶染,劉勰對才的認識是“才有庸儁”,就是說才有平庸與傑出的區別,才就有了高下之別了,這裏的才還是就能力而言的。}
也是將氣分爲剛柔兩種,而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云: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疊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他們所謂的“氣”皆偏於張載所謂的“氣質之性”, {張載《正蒙·誠明》“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謂“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也就是人自天稟得的自然之氣。
我們在第二章第一節曾經提到元氣的同一是詩與天地同構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宇宙萬物皆由氣構成,氣稟之在人則形成了六朝所謂的“體氣”,也就是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謂的“稟氣懷靈”,其謂“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疊用,喜慍分情”,氣之有陰陽,而性之有剛柔,氣稟也就與性情相關了。劉勰《文心雕龍*體性》: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
這裏的性情也就是人之氣質,可見性論與氣論的融通。
魏晉南北朝注意到詩人的秉性,也就是詩人的氣質,他們稱之爲“氣”“體氣”“體性”“情性”。認爲民(人)稟氣懷靈,則有“剛柔”“喜慍”等情性之異。這種個性、氣質的類型與詩歌的風格形成某種對應,正如《文心雕龍·體性》所謂的“夫情動而言形,理发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因內而符外,就是指的內在的氣稟與外在的詩風相符,所以才有“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
中唐以後,與儒學復興運動相應,對士人們提出了修養的要求。六朝的自然之氣稟,逐漸被修養之氣代替,如韓愈《答尉遲生書》: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安,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晣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
其謂“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雖還有“氣之清濁有體”的痕迹,“其中”本應指先天的性情、氣稟,但一旦“慎其實”,也就失去了自然的原貌,而成爲人爲的修養了。
宋代的氣論已經脫離了原有的樸素的萬物一氣論,理學家的“理一分殊”較好地解決了萬物一源與個體差異的矛盾。理一分殊,此處不妨改稱氣一分殊,更爲妥當。氣一分殊認爲萬物皆同源於一氣,但萬物稟得卻有分量的差異。就人與物而言,得其全爲人,而得其偏者爲物;就人與人而言,得其全者爲上智,得其偏者爲下愚。趙孟堅《彜齋文編》卷三《孫雪窗詩序》認爲景星慶雲爲天之英氣,朱草紫芝爲地之英氣,而詩爲人之英氣,“英英氣概,形而成詩”,由此他認爲“鄙夫猥徒,定無詩”,顯然因爲“鄙夫猥徒”,本無英氣,自然無詩;而“高人韻士”、“名臣鉅公”,稟得天地之英氣,感遇事物,發而爲詩。可見氣之英與否,爲詩之有無的關鍵。鄭思肖《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自序》引序湯西樓先生《壯逰集》云:“天地之靈氣為人,人之靈氣為心,心之靈氣為文,文之靈氣為詩。蓋詩者,古今天地間之靈物也。”他提出了“詩者,古今天地間之靈物也”,其實依他前面的所論,可以認爲詩爲天地間靈氣之至。他們皆認爲宇宙萬物皆由氣構成,但人與物的氣稟有所不同,上智與下愚亦有所不同,只有稟得“靈氣”“英氣”者,才可發而爲詩。
這樣的氣稟不僅有個體的差異,就一個時代來說,則表現出一個時代的風氣,如晁補之《雞肋集》卷三十四《石遠叔集序》謂: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爲,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
他所認爲的“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也即通常所謂的“文章關乎氣運”,即認爲一個時代的風氣也與天命流行的氣有關。
但宋代詩學討論則主要爲氣之在個人,因詩歌必須由人來創作,所以關鍵還在於個人之氣,晁補之接著指出“巧拙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他所謂的“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顯然受到曹丕“氣之清濁有體”,“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影響。但他認爲“其所養有薄厚”,可見他所指的爲文之“氣”已經不全是稟賦之氣了。
先天的氣鍾秉於人後,就成爲人之氣質、脾氣,也就形成一個人的爲人之風。如真德秀《日湖文集序》謂:
蓋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爲日星之光耀,發爲風塵之竒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視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八}
他認爲元氣,發爲天文、地文與人文,“自是以降”,即謂元氣之鍾稟於人,但於人文而言,他認爲與作者的稟賦與修養有關,“視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再只是稟賦的“資”,而加上了修養的“蓄”。可以看出宋代詩學中的氣論較之六朝的氣論所發生的改變。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六朝時認爲人的氣質與文章的風格相應,這一觀念在宋代依然存在,但已經發生了變化。徐積《節孝語錄》有謂:
公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
指出文如其氣,其意即在於文之風格當如修養之後的氣。他這裏的養氣之後的文“剛而敏”顯然是孟子所謂的“配義與道”的剛正之氣。再如上引真德秀《日湖文集序》又謂:
故祥順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勁。嫚肆者亾莊語,輕躁者亾確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八}
這裏的將氣稟之於人分成“祥順”與“峭直”,還是從剛柔來進行劃分的,而對相應的“言”則可能得出“婉”與“勁”兩種類型的風格。我們雖然依然可以看到曹丕“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與韓愈“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的思維方式。但這裏的“峭直”與“祥順”已經不全是六朝的剛與柔,而是加入了儒家的“義”與“仁”的爲人之風了。因爲在後面他急切地表示“嫚肆者亾莊語,輕躁者亾確詞”,他的抑揚態度較爲明顯。所以他所指與“言”相應的“人”已經密切地與“蓄之淺深”聯繫在一起,而不限於“資之薄厚”了。
這種氣一直分爲剛與柔兩種,也就是一個人性情剛烈與柔和,這兩種氣質本來沒有高下之別,但當這種脾氣發泄出來(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情),情發泄出來可能造成過,脾氣發出來也可能造成過分。張綱《華陽集》卷第二十四《經筵詩講義》:“夫詩之爲變,則以事有不得平者,咈乎吾心,故作爲箴規怨刺之言,以發其憤憾不泄之氣。夫如是則宜有怒而溢惡,矯而過正者,”即指出“不平則鳴”則有可能“有怒而溢惡”,陷於過分。所以必須養氣,濟其不及,而泄其之過,以歸於中和。
我們知道養氣說起源於孟子的養氣說,《孟子·公孫丑》: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孟子所養之氣,是由內心的“義”、“道”生發出來的爲人之氣,至大至剛,擴充之則可塞於天地,這是一種鬱勃而充實的剛正之氣。
宋代養氣有兩個方面,一是滋養,也即是氣之不足則養之以壯,這與孟子的剛義之氣相關。我們以蘇軾《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抑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爲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飢,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壹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慎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蘇軾詩集》卷三十四}
這裏針對郊島之詩所表現出來的窮弱氣餒,蘇軾提出“昌志”與“昌氣”之說,認爲滋此雄大之氣,充塞天地,而且認爲“昌氣”遠在“昌身”“昌詩”之前,因以氣之昌來“昌身”與“昌詩”,所謂執本則末自得,而不可執末以求本。蘇軾更有“養氣如養兒”之說,{《蘇軾詩集》卷一十五《贈王仲素寺丞》}可見宋代“文如其氣”的“氣”已經不是六朝的天稟之氣,而所取則在於修養之後的氣。黃裳《演山集》卷二十一《書意集序》謂:
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養心治氣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後動,合養而爲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書者意耳,不主乎言。孟子曰:不得心,勿求其氣無趨,勿求其言之無害。故其七篇之書,發於心氣之所養,雖其立言亦如與人答問之時,近而遠,約而詳,不爲艱苦輕揚之辭。
黃裳認爲氣之不養,則可能“趨”,“趨”即是偏倚,也就是不中和。心之不養,則可能言“害”,所以當“發於心氣之所養”,心氣修養之中,歸於中和,而得“言”之“近而遠,約而詳”,即得表達之中和,而且“不爲艱苦輕揚之辭”,也是著眼於對氣“餒”進行超越。宋代對郊島詩風多有批評,即是認爲“郊寒島瘦”,多有窮苦之言,愁苦而氣弱。
二是規範,即將過分之氣規範在禮義的範圍之內。上面說的滋養爲濟其不及,此處則爲泄其太過。過分之氣卻似乎總是由於人之剛烈之氣所致,而柔和之氣外現不易讓人覺得過分。所以雖說是對剛柔之氣的雙重規範,但在實際操作中這種規範作用針對的多是剛烈之氣。黃庭堅《寄蘇子由書三首》:
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年矣。……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沈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媟,欲疎之不能忘,雖開形迹闊疎而生平詠歎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山谷集》卷十九}
黃庭堅認爲蘇轍“治氣養心”,“沈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沈潛、致曲皆就柔和而言,得性情平和之風。養氣取的充實剛正之氣蘊於內,而對於外現的氣則傾向於和氣。宋代的理想人格是外柔而內剛,對於“人之文”傾向於柔和。{可參見黃寶華《黃庭堅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P201-222}李石(?-1181)《方舟集》卷十《西江集序》有謂:
雅頌之體博大洪深,紆徐豐衍,怨而不至誹,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厚溫恭之氣不可及也,至於國風二南以降,過則淫佚流蕩,其不及則悲噫憔悴,分量局促。若一日無以自容,豈具有聲音語言以相絕爲異哉?
李石認爲雅頌之體,性情中和,因而“和厚溫恭之氣”不可及。也就是外現的和柔之氣。這裏的和柔之氣即表現爲“怨而不至誹,喜而不至溢”,也就性情中和的意思了。
但我們注意到這樣的和柔之氣與上面所說的郁勃之氣並不矛盾,甚至可以說是來源於氣之充郁的。他所謂的“悲噫憔悴,分量局促”也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氣餒”。他認爲“氣餒”,所以多有“怨而至於誹,喜而至於溢”之言,這樣的發而不中節,即源於其氣之不充,也就是氣之不和。可見他們的氣是一種內在的充實,但卻外現爲和柔的氣。
這裏的道理其實簡單。這樣的氣是充實,“配義與道”的,而道之大,則在於生養萬物,而包容萬物,如上引蘇軾之詩有謂“慎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即謂養氣以充實,即與道相配,所以對於人生的窮餓並不究心,能容物,所以柔和。這樣由守道而帶來的順命與釋老的委命是不同。陸遊(1125-1210)《渭南文集》卷十四《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陽有士曰方徳亨,名豐之。才甚髙而養氣不橈,呂舍人居仁、何著作搢之皆屈行軰與之逰。徳亨晚愈不遭而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