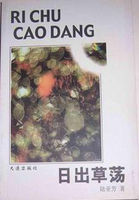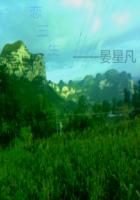于焕生家门灯虚弱地亮着,懒散照在他那辆破摩托上,有点昏昏然,她看了两眼竟然有些困意。这两天太操劳了,昨晚请了一桌客,为二胖的亲事。那一伙子人真能作,喝到后半夜才散。今儿白天,她又翻山越岭去了城山镇另一个媒人家。双媒人请着,她有自己的打算。她总感觉二胖这个亲事有点不稳妥。为了把握性大些,她宁可多搭些钱财和精力了。可不能像两年前大胖第一个对象那样,折腾出去不少钱,人毛没捞到半点。而大胖一年前娶的这个媳妇也挺悬乎的,成亲前半个月差点飞了,多亏媒人压茬子,硬给做了主,这媳妇才千辛万苦地娶到了家。儿子们的亲事,是她心头最大的石头。她是个寡妇,还做这个拿不上台面的营生儿,给儿子成个家比下油锅都胆颤。二胖的事儿不能含糊半点,可得往顺了办。还有一点让她不放心的是,二胖没有大胖懂事。大胖会办事,会说话,还知道体贴人。以前大胖晚上总张罗送她。虽她从不牵扯孩子,可心里还是喜得要命的,当娘的容易满足,都是贱种。二胖就没这个心,他整天除了爱吃喝就是喜欢玩,从不注意别人的感受。临出来时他还在叨咕手机旧了,说:妈,给我换个新的吧,还说:你搭那个人情找两个媒人干什么,有那钱不如买几斤肉吃。二胖从小就爱吃肉,如果把钱省了,他真会一下子买几斤肉搁在你面前,让你给红烧,他就是一个和肉亲的人。
于焕生使劲儿踹摩托车,老摩托呼呼地气喘,噗噗地咳嗽,不满的尖声嘶叫。这时于焕生的老婆拿了两件厚衣服出来,说:这功夫还行,回来夜深就凉了。她接了衣服,于焕生媳妇看着,等着,一脸平静并不说什么,等摩托车启动平稳了,大灯开了,两人稳当坐上去,才说了一句:焕生,慢点开。她忙替答:没事,放心。于焕生也“嗯”了一声,或者根本就没答应,只是摩托车替他“嗯嗯”地叫了两声,反正破车一溜儿烟上了土道,惊起的尘土隐在夜色里,悄然落在道两旁的杂草从中。
在出村口拐弯时,车身稍斜了一下,正好垫在一块石头上,猛颠,她本能地扶住于焕生的腰。那腰厚实温热,有肉,不算年轻也不算老的腰,扶上去很舒坦。这路有很长一段是石头裸露的,她就一直扶着。车上了大道,平稳了,她的手才放下来。
很多人都说于焕生和她有一腿,还说于焕生的这“腿”很长很粗,别说一个寡妇,就是村里别的女人要不对他这腿上心,她们就都是毛病。她没有毛病,但她真把于焕生当成弟弟看。她当然不会知道于焕生的腿是什么样,她只熟悉他的胳膊、他的手或者还有他的腰。最初于焕生胳膊给她的感觉绷起来硬僵僵像根大木棒。那是她出来干这个的第三个年头,那时他们从附近杨村回来,天下起冒烟儿暴雨,刮起大风。那次两人是第三次在一起搭活儿,还半生不熟的。在一个泥坑里她跌了跟头,摔了一身泥,整个人滑溜溜地像个泥鳅,于焕生忙回过身搀她,一抓没抓牢,她又摔倒,把于焕生也带了一个趔趄。再一扶时手就摸到了她的胸上,于焕生忙收了手,有一会儿显得很犹豫,拉也不是,拽也不是,后来他站稳了脚半蹲着给了她一个臂弯,让她自己动手。那次,她就像挂在树桠上的咸鱼干儿一样的滴流乱转在雨里走。等他们跟头把式的勉强回到了于焕生家时,两人都成了泥人。不知为啥这么多年来,只有那次她最委屈,坐在地上哭,哭得泥一把,泪一把,边哭边数叨:妈呀!这叫过的什么******鬼日子啊——妈呀!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啦……一会儿功夫于焕生家的砖地湿了一片。于焕生就傻站在那里。倒是于焕生的媳妇很体贴她,边劝边找来干衣服给她。那件衣服是红碎花的,看上去很新。她转头看到于焕生家锅里冒出的热气,才想起晚上出来得急,没顾上做饭,只留了两个凉玉米饼子在锅台上,家里的大胖二胖一定饿得眼睛发绿了,于是,抹了一把泪脸,爬起来,推开门,摒了息又钻进雨里。
就是那次大雨,于焕生和他老婆的表现,使她生出无边的好感来。她这个没有男人可靠的女人想找个好搭伴不容易。像头三年那两个,夜里搭伴回去时,没风没雨的就往身边靠,嘴上不老实,手更不老实,真一把假一把扶不是地方,摸更不是地方。把她这个寡妇当成公共澡堂子的水,走过路过的都想撩拨一下。她下决心要好好跟于焕生处,而处好的关键是于焕生的媳妇。她没事就找于焕生的媳妇说话。她把自己的甜苦都扒给这个老实安静的女人看,她把心窝里的话都掏给她听,给她买头巾,买衣服;给她做拿手好菜;两个女人在一起喝酒,喝多了伤心的情绪涌上来,她抱着于焕生的女人大哭。最终她就是想让这个女人相信,她不会和于焕生有半点不清白的,她们永远是姐弟那种关系。她还跟于焕生的女人说等将来二胖结了婚,她不干这行当了,找个正经的伴儿过后几十年,没事的时候找几个会唱二人转的,去广场天天过戏瘾,她要唱喜气的戏,欢闹的戏,正经的戏。于焕生的老婆很信她,从来没有用怀疑的眼光瞟看过她,她感觉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在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你又管不住别人的嘴。其实在别人的眼里他俩的关系是挺神秘,十五六年常在一起混,孤男寡女的常走夜路,这能消停吗?可事实上却没一个人亲眼见到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