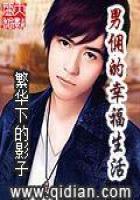凌晨三点,工地上已然热闹起来,大吊车、大铲车、推土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邢法匆匆的吃了碗面条,裹着棉衣钻进了驾驶室,开始了第一班的工作,按要求得开六个小时,他还不知道,就是在这个他生平最厌恶的狭小空间里,他度过了自己最后的人生。
他打着哈欠蹦下来,脚掌被震得发麻,大脑好一阵眩晕,目不识物,胳膊腿好似不是自己的了,这种情况对于睡眠不足,连续几个小时坐姿不变,双手忙乎不停,耳边不得清净的大吊车司机来说,稀疏平常,谁也没想到会惹来杀身之祸。
邢法应该原地休息休息的,而不是意识模糊就朝休息室跑,还跑错了方向,迎面而来的车斗子把里面的烂土坯烂砖头子正正好好的从他头顶浇下来,魂飞魄散的肇事司机把人从废物堆里拔出来的时候,伤者还说没事儿呢。
邢法真的以为没事,除了脸部擦伤外,浑身上下没有任何伤口,也感不到一丝疼痛,只是肚子里火烧火燎的,和拉肚子的症状差不多,他被几个人扶到休息室后还自己倒了杯热水,寻思啃完面包得好好睡一觉。
啃到一半突然出现了红红的不明粘稠物,可能是果酱吧,又啃了两口发现不对,牙花子出血了,紧接着鼻子耳朵分别有鲜红的血液滴下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赶忙站起来却嗷嗷嗷的不停呕吐,血,血,全是血。
临近医院只有一个手术室,有个出车祸的妇女正在截肢,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来了个有点权威的医生,她只看了看邢法的舌苔,扒了扒眼就劝往哈尔滨送,说你们赶快吧,病人得马上做手术,我们医院的情况,无法做这样的手术,赶紧送走,要快,耽误了就完了,真的,就完了……
人真的完了,如果直接送到哈尔滨,或其他正规一点的医院,紧赶出半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死者会不会跑在死神的前头捡回一条命?这都是番外话,邢法死后,没有人检讨,更不关心他到底死于什么,涉事方都想方设法的推卸责任,受害者则琢磨着孩子的命值多少钱。
肇事司机光棍儿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宁肯坐牢,分文不出,其实他也真没有,死者生前跟他最交好,亲手杀了自己的小伙伴,还被说成蓄意谋杀,应该痛不欲生吧,还记得看守所里那个高瘦男人仰头哭号:小邢啊,你咋就往车斗子下面钻呢,那么大的车,我真是掌握不了啊……
没有劳资合同,没有人身保险,还属于违章作业,毕竟出了人命,工地想一点责任不担,那是不可能的。这可忙坏了张岭,省里就跑了十几趟,请客也请了好多回,调动任何可以调动的关系,总算给了老同学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是几个月后的事儿了,之前,所有人还都在为邢法会不会白死而担忧,连神通广大的张经理也不确定能赔偿多少钱,但他每次都拍着胸脯说:放心吧,我一定尽力,钱少不了,少了我给添上。
明白担心不靠谱,每天都打电话催好几遍,后来张岭干脆不接电话了,发过来信息说:大班长,你更年期提前呀?
木有更年期,大班长还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此称谓估计本人听到也会恶心的,可她的确是个姑娘啊?脆弱敏感的内心,多愁善感的年纪,容易把自己圈到一个圈子里,怎么也走不出来。
她永远也忘不了老同学生前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大班长,对不起了,就差你的水耗子鞋垫还没有做成,哎!恐怕没机会了……因为和艾佳恋爱的事儿,大班长曾经把他贬损的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但他一点也不记得了,也从来没有抱怨过,生命的尽头还满心愧疚,对她的愧疚。
她永远也忘不了老同学弥留之际的眼神,他是多想再看看这个世界啊,多看一眼他的父母亲朋,多看一眼他永生的爱人,他哭了,像个即将远走他乡的孩子,但身体已经筋疲力尽,只能默默地流着泪。
她最怕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起多年前的人和事儿,有些清晰明了,有的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片段支离破碎,时间错综复杂,笑声哭声打闹声总会把她吵醒于午夜中,醒来后周围漆黑一片,唯有枕头上的泪迹斑斑。
原来是个梦,一个奢华的梦。
所以当王骁玮说再陪我玩一会儿的时候,她叹了口气,还是坐了下来,她真的不想回到那个寂寞孤独的地方,她原来是那么的恐惧孤独,这么多年了,她第一次想找个肩膀靠一下,找个可以哭泣的怀抱。
漫不经心的打着牌,没有其他可以娱乐的东西,两个人早就没有兴致了但还硬撑着。明白把牌一扔,说,你赢了,我喝酒。王骁玮赶忙阻止:我说让你喝酒了吗,这次要换个花样。明白打趣:违反伦理道德的可不行。
王骁玮想想勾了勾食指说,过来,我偷偷告诉你,明白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王骁玮说你过来,你过来我就放,真聪明,就是要让你闻闻我的臭屁,憋了一晚上了没好意思放,明白捏着鼻子靠过来,笑骂了句:你真恶心。
她没想到他会吻她,还是强迫的,压迫的她无法呼吸,他死死的扣住她的后脑勺,好像要把两个头镶在一起。她拼命挣扎,推他的头,抓他的头发,他也拼命不放手,终于忽通一声,两人四仰八叉的摔倒在地上。
袁野被声音惊醒了,坐起来大喊咋了,咋了,地震了吗,地震了吗,我的‘爱疯’在哪……王骁玮冲过去把他摁倒,说睡睡睡,没你的事,哪里来的地震,你的宝贝没电了,放在那边充电呢,快睡吧你……
他头一次对袁野如此有耐心,把他哄睡了,还找来毛毯盖上,完备之后捂着脑袋上的大筋包恶狠狠的骂:你这个二尾子,从来都这么狠心。二尾子立马回嘴:谁让你的屁那么臭呢,就该把你**缝上。
看着王骁玮坐在那儿呼呼呼的生气,明白幸灾乐祸的笑,脑袋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要是哪天她意外死了,会不会永远错过了对面的男孩,她真的不能勇敢一点吗?她到底在怕些什么。如果真有那一天,他就是她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她脑袋一热,脱口而出:我们上床吧!
他先是愣了,接着严肃的问:你和谁说话呢,这里有两个男人。
她心想豁出去了,闭着眼睛喊:王骁玮,我们上床吧!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真的凝固了,钟摆不动了,空调不吹了,冰箱不响了,鱼缸里的氧气不冒泡了,连袁野的鼾声都停止了,屋子里只能听到两个人此起彼伏的喘息声,和两颗心砰砰砰的跳动声。
明白紧闭着眼睛,心里怕极了,她后悔了,怎么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他为什么不吭声,他应该骂她呀,用最肮脏的话来羞辱她,那样也好受一点,他在想什么呢?最好的情况也有,他会说:你疯了,开什么玩笑,之后两个人一笑了之。
她把所有的结果想遍了,就是没想到他会拉着她的手冲下楼去,穿过马路一路狂奔。
此时皓月当空,华灯高照,北斗星的光芒格外耀眼。多年前,相同的地方,有三个小女孩喝的伶仃大醉,彼此憧憬着心中的梦想,多年后,其中的一个终于长大,拼命的想攥紧手中的幸福。
明白被摇了几下才如梦初醒,桌子对面有一个陌生的女人,不怀好意的盯着她看,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喂喂,你怎么了?她啊了一声,他又说:要用身份证,我没带,你带没带身份证?
她懵懂的摇摇头,意思是没有,他叹了声气开始挠头,样子窘迫极了,继而红着脸问: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开房间?她终于恍然大悟,他把那句话当真了,到此时才发现,两人只穿着里面的T恤衫,都没有穿厚外套,竟然这样子在寒冷的夜晚连跑了两条街。
收银员似笑非笑的说:可以啊,不过要交一千块钱押金,拿身份证才能退房,退房时退钱,不过没有包间了,只有间三张单人床的套房,你们要不要住?王骁玮看了明白一眼,咬咬牙说,好好好,拿钥匙吧。
王骁玮掏掏兜,连说坏了坏了,又俯下身翻明白的口袋,起来开始哀求收银员:美女,能不能打个欠条啊?明白听完当时就崩溃了,掉头想跑却被拉住,只听头顶上说:等等,我有办法,等等……
王骁玮摘下腕上的手表小心翼翼的放到收银台上,说,这表是在意大利买的,怎么也值两万块吧,我抵押了,最晚明天早上我就拿钱赎回去,见对方半信半疑,又补充:我一定会来赎的,这可是去年我过生日时,我姐姐送我的生日礼物,要不是事情重大,我还不放心放你们这儿呢,他转头朝身后的女孩眨眨眼。
终于拿到了钥匙,他拉着她蹬蹬蹬的跑上楼,房门刚关上就把她抵在墙上亲吻起来。他们从门口一直纠缠到床上,嘴唇舌头始终没有分开过,他的手很不老实,游走于她的背部和腿上,还趁机脱掉了她的上衣。
明白忘记两人亲吻了多长时间,她已经完全沦陷在他的温柔之中了,好像她的脸上,耳朵上,脖子上,胸口上,胳膊上,甚至手心中,全是他留下的湿润。她的大脑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身体完全不属于自己了。
她突然推开他,缩到墙角浑身颤抖起来,他刚要靠近她就哭喊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想起了什么,恶狠狠的拿起衣服转身要走,她扑过来抱住他的腰:不要去,隋龙真的没对我做过什么,真的,不要你去找他,求求你……
王骁玮发誓,总有一天要向隋龙讨回公道,他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白眼球上布满血丝,瞳孔紧紧的收缩着,里面藏着重重杀机,明白的心咯噔一下,好像看到了两个男人火拼的场面,不禁浑身汗毛倒数,突生了一种比胸部受袭还要战栗的恐惧感。
当头上缠满纱布的明白躺在午夜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得知隋龙被人谋杀的消息时,立即晕厥过去,栽倒在地的那一刻,三个月前那晚的情景历历在目,王骁玮狰狞的脸在此刻异常清晰,还有那双让人害怕的眼睛。完了完了,她最不愿意看到的灾难,还是降临了。
那个不眠之夜,陈凤也在午夜惊醒,推开胸前那只老男人的手,随便拿了件衣服披上,光着脚走到阳台,许久许久还在回味刚刚的噩梦,她梦见一辆汽车朝自己开过来,车灯很亮,晃的她睁不开眼睛,情景和隋龙分手那晚的一模一样。只可惜此时的夜空没有月亮,也找不到哪里是北方。她轻轻的叹了口气:还有五分钟,她就二十一岁了。
短信的确不是胡小骚发的,也不是隋龙认识的任何一个女人。他之所以那么害怕的抢手机,完全因为他在乎陈凤,他怕是哪个前女友捣蛋,产生误会,他不想再和她吵架了。真的,和她恋爱的日子,直到她离开,直到他死去,他没碰过其他女人,真的。
隋大少和卉卉的孽缘,完全因为那个短信。那天陈凤刚要拨打那个电话,张岭就闯进来说邢法出事了,两人走后,隋龙照着号码打过去,开口便骂,说你他妈找死是不是,要是我和我女朋友有什么事,我他妈就弄死你,操,知道我是谁不,赫拉尔都他妈是我们隋家的天下。
电话那头的女孩赶忙道歉,说是发错了号码,我相好的和大哥的差了两位数,我心一急就发错了,真对不起,要不然我和你女朋友亲自说说吧,隋大哥,好吗?
隋大少忍不住笑,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哪个女孩喊他隋大哥呢,谁敢呀,都隋大少隋大少的叫,冷不丁听见这么个称呼,挺新鲜的,他笑着问:你不知道隋龙是干嘛的?对方传来抱歉的声音:我真不认识隋龙啊!
两人约好第二天见面,在一家西餐厅里,饭菜上来半天,卉卉才风尘仆仆的赶来,说是学校临时加了课,下了课马上就打了车,还说隋大哥你再点点儿什么吧,是我的错,这顿饭我请客。
隋大少越发感觉眼前的学生妹有点意思了,发出那么黄的短信,脸面却纯情无比,昨天不知道隋龙是谁,挂了电话不会问问别人吗?还敢让隋大少等你,胆儿肥吧?不逃课的好学生,却低声下气宁愿做人家的小三?搞逗啊!
卉卉哭诉了自己的经历,男友因为学校副校长的女儿,把她甩了,为了报复她发了那个短信,没想到阴差阳错,哎,丢脸丢的连死的心都有了,然后电眼十足:隋大哥,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
陈凤目光呆滞地问,又像自言自语:他们,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张岭挠挠头说:我就知道这些,两人见面之后就好了吧,发展到什么程度,我真不知道,隋大少现在好些事都瞒着我,我也不好意思多打听。过了一会儿又劝道:要是他变心了,就不要吵闹了,开始我就说过,隋龙这人没长性的,早点离开他,是好事儿。
陈凤说知道了,你去忙吧。她蜷缩成一团,连床板都跟着颤抖,身体冰凉冰凉的,好像刚刚淋过雨,雨已经淋进了心里。他们见第一次面就好了,他一直在骗人,之前他是没有骗过她,之后呢,他没有一句实话。
要不要离开,要不要离开,她想了整整三天三夜,七十二个小时眼睛一眨不眨的想,不再过问美甲店的装修工作,那是他送她美甲店啊!没有他,美甲店装修的再好又有什么用?生意再兴隆又有什么用?他为什么变得这么快,说不爱就不爱了……爱情真的会如此的短暂吗?
三天了,他不见踪影,电话里总说忙,却说不清忙些什么,她终于下定决心去找他。起床洗洗脸,刷刷牙,头发油油的贴在脸上,该洗了,吹风机的风真大,都能把人吹个跟头,还记得每次都是‘小畜生’给她吹呢。
把衣柜里的衣服都拿出来,挨个儿穿上照镜子,皮草把人显得太雍容了,他现在喜欢学生妹了,还是这件韩版连衣裙吧,不好,把脸色衬托的蜡黄蜡黄的,哎呀,怎么忘了化妆,他总说化了妆的女人才好看。
‘赫拉尔传奇’还是那么热闹,她有段日子没来了,服务员竟然还认识,惊慌失措的迎上:凤凰姐,隋大少不在,你先上楼上休息吧,我我我马上把果盘端上去。隋大少明明在里面,连你们也骗我,这里所有的人,都在骗我!
她慢慢朝里面走,一眼就看见他了。‘小畜生’也看见她了,笑容却僵在脸上,他慢慢把头低下去,叼着的香烟也不发光了。卉卉扒了颗橘子,撕下一瓣儿想喂隋大哥,他却把头扭了过去,卉卉果断地拔掉那根儿碍事的烟蒂,还是把橘子塞了进去。
‘小妈妈’还记得‘小畜生’最不喜欢吃橘子了,说总是当成甘蔗,嚼完了吃了汁,其余的全吐出来,橘子那么酸,牙齿都倒了。有一次求了他一上午,他还是不肯吃她做的水果沙拉,只因里面有橘子。
如今他却吃得那么快乐,腮帮子鼓鼓的蠕动,脸部被勾勒成了完美的弧线,弧线还有节奏的跳跃呢,随着欢快的舞曲,随着卉卉甜蜜的笑容,弧线渐渐压低,渐渐消失,直到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有客人吆喝着‘凤凰’来一曲,接着全场的人都跟着起哄,除了低着头的隋大少。卉卉也跟着起哄,拍着双手,眼睛里,满是挑衅的神色,嘴角上翘,似笑非笑,好像等着观看小丑的表演。
唱就唱吧,她本来就是个小丑,在台上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取悦别人的小丑,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还不知道的小丑。她终于明白了,一直以来她的生活,她的事业,她的爱情,她的人生,不过是一场舞台剧,而她,只是个小丑而已。
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下来,视线全然模糊,整个世界也黑暗下来,听不见音乐声,听不见呼喊声,许久许久,她的呼吸好像停止了,她的身体好像飘了起来,这是哪里啊?是大海吗,没错,是海浪,海浪把她抛来抛去,谁也不想要她,好像在说:你的家在哪里呀,我送你回家吧。
我的家在哪里?哪里是我的家?我还有家吗?她一遍遍喃喃自语,哭着说:这里没有我的家,没有我的亲人,我不该回来的,我不该回来的。她哭的伤心极了,就像爸爸去世的时候,她躲起来偷偷的哭,也是这么说的:我不该回来的……
“你的家在哪里呀,我送你回家吧。”
她看清了,那不是海浪,而是一个女孩的脸,挑衅的,戏谑的,幸灾乐祸的。她突然扑过去抓住卉卉,死死的抓住她的脑袋:我没有家,别跟我提家,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我没有家……
所有人都跑过来视图拉开两人,可陈凤下了死手,估计把手锯下来都不会松开,发疯了一般。卉卉的哭号声不绝于耳,已经有头发被扯下来,惨白的脸上血迹斑斑。隋龙从后面抱住陈凤的身体,如何用力还是分不开两人,只加重了卉卉的惨叫声。
人群中有人说:好像是失心疯,快,来个人打她一巴掌,把她打醒就好了,快,这样下去,要出人命了。隋大少几次把手扬起来,又放了下去,最后狠狠心啪的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陈凤向后倒去,脑袋重重的磕在了地板上,她真的醒了,可那一巴掌太重了,她的脸瞬间红肿起来,还被隋龙的扳指刮了条长口子,血液正缓缓的流着。她瞪着大眼睛左看看,右看看,低下头捂着脸摇摇晃晃的站起来,谁扶她,她推开谁,头也不回的朝门口走去……
隋龙气喘吁吁的坐在地上,还对刚刚发生的一幕心有余悸,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他看见陈凤的背影飘飘走远,似一阵虚无缥缈的风,若有若无,看得他眼花缭乱。突然,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朝他嫣然一笑,杏口微张,碧眼剔透。
她的样子美极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她为什么会这么美?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她。
那是她,留在他记忆里的,最后一个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