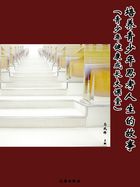无双城中有条河,名唤麟河。麟河贯穿东西两面,是无双城的人赖以生存的必须,因此一些人都愿意生活在这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他们靠捕鱼为生,常年漂泊在麟河上。
在无双城的麟河上有一条花船,名为‘飘零’是整个无双城内最大的风雅场所。整条花船高八丈长约有十几丈。上下布满五颜六色的帐幔,再经烛光照射出去将整条显得格外秀丽。花船上下一共分为三层,每层又分三部分,这第一层除了是姑娘们的房间之外,还另设有舞坊,乐坊,第二层是左边是供达官贵人享乐的场所,中间是饮酒作乐之地,而右边则是富家子弟的场所。最下一层是大堂,堂中设有玉台旁边是从各地请来的乐师。这条花船所经之地必是夜夜笙歌,琴音不断。故此,飘零便被称为无双城内最大的风雅场所。
听霍宇说,这几日凌睿寒皆是在此处,趁着夜幕降临,清婉特意换上一身男装寻到了那里。
远远望去,比起一般的官船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听闻飘零船上是极为的吵闹,在三里之外便可听见船上所传来的嘈杂声,不知为何今日这船上除了一阵曲声悠扬的琴音之外到无其他别的声音,她一撩雪袍便大步跨上飘零的接板。
刚一踏进飘零的前堂,门口一名身着艳红轻纱的女子便走了过来,那女子模样倒是清秀只是图了太厚的脂粉倒,墨黑的眼眸上似有些忧愁不似一般的青楼女子那么熠熠生辉,她细细的打量了清婉一眼,微扬的嘴角扬起一抹嗤笑。
清婉心中清楚,这样的装束极少能瞒得住旁人,她这样做不过是不想被旁人看到他来此地而已。
这样的场面想来那女子也见多了,不能着女装前来,想必是有什么难处,更可况,女子随意前来这种地方,传出去自是要被人误解的,所以,她也只当没看出,道
“公子,今日我们的花船被人包下了,烦请公子改日再来。”
“我是来寻人的。”清婉淡淡的言道。
说着还悄悄塞给那女子一锭金,那女子嗤笑一声,道“到这里来的,哪个不是来寻人的?”说着又将那锭金还给了清婉。
她这么一说,清婉当即也不知该说什么了。却在此时,从楼上传来一阵‘咚咚咚’的下楼声,只见另一位女子匆匆忙忙的跑到那女子的面前,急道“琴姐,楼上的那位公子又要换人。”
“你没说我们船上琴艺精湛的琴师已经被他换了一遍了吗?”
“说了,但那位公子说,你们如此大的花船连一个精通琴艺的都没有,有何资格敢称是无双城中最大的风雅场所?”
清婉抿嘴一笑,这倒像凌睿寒说话的风格,谁知那位名唤琴姐的女子一听,面色当即沉了下来,怒道“我看这人分明是来闹事的,是觉得我们好欺负吗?”
说着正要上楼,却被清婉一把拦住,道“你们既是开张做生意,自然以和为贵,倘若今日得罪了那位公子,将此事传到城中,与你们自然无利……这样吧,不妨让我试试。”
“你也会弹琴?”那女子一脸疑惑的瞧着清婉。
“略懂一二。”
“若是你也被那位公子赶下来了呢?”
清婉莞尔一笑,答“那届时再按你们的意思处置。”
那女子略一思索,许是觉得清婉之言有道理,便让另一位女子领着清婉上了楼,才到楼上,面前敞开的房中便传来一声杯子落地的声音。领头的那位无奈的摇了摇头,将清婉带进了房中。
踏进房间,侧面是一面绣着崇山峻岭的屏风,透过屏风隐隐的看见,凌睿寒正慵懒的躺在后面的软榻上,微敞的衣襟露出他的胸口。
清婉微微蹙眉,在琴边坐了下来,手起,弦动。
婉转悠扬的曲子自她的指尖流出,时高时低,时而如幽泉出山,风发水涌,若闻波涛,息心静听,宛然余波激石,时而又似杜鹃的啼鸣般哀怨。今日弹的这首曲子,名唤红尘赋,是师傅所有琴曲中最宝贵的琴曲,幼年之时,师傅每次弹起这首琴曲,神色中总是带着淡淡的暗伤,后来,师傅教她弹奏红尘赋,每次弹起,这琴曲的后半段,她总是弹的不如师傅那般入魂。
屏风前双目微闭的凌睿寒忽然睁开双眸,凝视着屏风后面之时,有些诧异。忽然,原本悠扬的琴音忽然变得有些烦躁,曲音也开始乱弹起来,凌睿寒有些异样的望向屏风,‘铮’琴音戛然而止,他站起身来疾走的走到屏风后面,坐在琴前的清婉正眉头紧蹙,痛苦的托着额头,凌睿寒慌忙蹲下身子焦急的问道“清婉,你怎么了。”
可此刻的她已经痛得说不出话,贝齿紧紧的咬着双唇已经咬出了血迹,见此景凌睿寒知道她的头疾又犯了“你的头疾又犯了。”虽然这几日,她的头疾也时常复发,可确不如这一次的这般严重,莫不然真的是因为她这几日不曾睡好的原因才致使头疾越发严重。他不由分说的将她打横抱起,不顾随即赶来的一众人诧异的眼神,抱着清婉大步离去。
一路上她蜷缩的凌睿寒的怀中痛苦的抱着额头,不过片刻原本还带着血色的脸颊开始变得惨白,凌睿寒的脚步丝毫不敢停歇,一进侯府他便不由分说的寻着欧阳泽的身影。这几****不在府上,所以清婉的病况他也一直不知,最后还是香儿扯着他的袖子告诉他说,清婉的解毒的药与治疗头疾的药不能同服,若是头疾再犯只能忍着。
凌睿寒瞧了眼躺在床上痛的不能言语的清婉,恰在此刻,欧阳泽从外面几步走了进来,还未等凌睿寒说什么,欧阳泽便急忙上前查看,为了不打扰欧阳泽的诊断,霍宇将哭的梨花带雨的香儿急忙拉了出去。
“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欧阳泽摇了摇头,凌睿寒还想在说些什么,衣袖仿佛被什么人拉住,他转过身来望着痛苦无比的清婉,只见她低吟道“不必再问了,我无碍的。”
身后的欧阳泽见此也离开了房间,静静地将门掩上,夜色越来越深,只是痛得早已疲惫不堪的清婉仍旧没有丝毫的好转,坐在一旁的凌睿寒也一直担忧的替她擦拭着汗水,将她紧紧的抱在怀中。
天色将亮她的头疾方才稍稍减轻,累的没有一丝力气的她倒在他的怀中沉沉的睡去,他动也不敢动只是生怕会惊动了在梦中的她。
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已是下午,她睁开沉重的眼睛映入眼中的仍旧是那个最让她安心的他,见她醒来他面上带着一丝欣慰的言道“你醒了,头可还痛吗?”
干涩的喉间说不出一句话她也只能摇了摇头,在凌睿寒的帮助下她从床上坐起,轻轻地抚上她惨白的脸颊,凌睿寒显得有几分心疼“真的还好吗?”
清婉愣愣的看着他没有回答,只是动了动她那干裂的嘴唇言道“你不怪我了吗?”
凌睿寒垂下头似是有些无奈的言道“我该拿你怎么办?”
清婉的心中一阵触动,她从不曾见过凌睿寒这样,其实欧阳泽说的不错,他们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为命运所累,她心中有苦,他的心头又何尝没有,她动了动嘴唇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不知该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