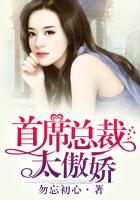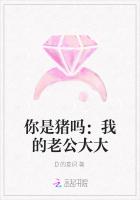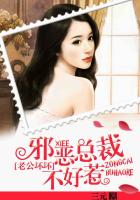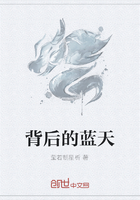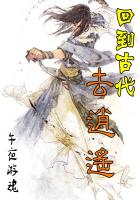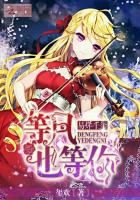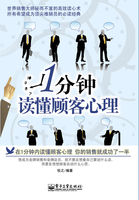《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林秋雨
1975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年。
立冬过后,长江以北已经刮起西北风,风里夹杂着一丝丝来自遥远西伯利亚的冷气,吹面刮耳,寒颤刺心。
父亲林金湖刚18岁,刚从扬州中学刚毕业,一直闲赋在家,备感恍惚,城里同班同学,男男女女们都被招工进了厂,有了自己的工作,领了微薄的工资,而农村户口的他自毕业后就一直闲在青砖灰瓦的农家小院里,无所事事,书是自然看不进去了,一想到茫茫人生路既无去向也没奔头,心生烦躁,日子一下子变得郁然沉重起来。
又是一日清晨,隔壁叔伯们喊他一起去村头旱田里割麦草赚公分。他刚在田埂上拉开架式,挥了几下镰刀,矮瘦精干的生产队林大勇,也是本家一叔辈,站在田埂上大声嘶喊他的名字,并朝他使劲招手。他迅速放下手中镰刀,朝林队长奔去。
林队长急吼吼道:“刚接到乡政府电话,让你晌午前务必赶到乡人武部参加今年的征兵体检。”接到通知后,林金湖一路兴奋小跑了五六公里,穿过西湖乡蜀岗下的一大片农科院的种子基地,来到乡政府大院。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参军本不在自己的长远规划范围内,但是既然被通知了,也是一条出路,特别是在这茫然不知所措的日子里,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乡政府大院的篮球场上,各村适龄男青年们已站成一个长队,在人武部征兵干部的口令指挥下,绕着操场小跑十几圈。短短几分钟,已有一大半小伙子被刷:跑步歪八字脚的、佝偻着背的、秃发癞头的、斜眼歪嘴的、气喘吁吁明显体力不支的,统统半途被剔出了队伍。
父亲一直跑到最后,一米八三魁梧结实的身块,黑黢黢健康的皮肤,让他鹤立鸡群显得那么优越,以及档案表上备注的高中文化学历,引起了征兵干部们一致赏识争抢。
当年十二月,住在蜀岗北坡的林金湖家收到了大红的入伍通知书,寒冬腊月,在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中,林金湖穿着绿色部队制式大棉袄,带着鲜艳的大红花,登上了接兵的绿皮卡车,参军入了伍。
卡车一路北下,首先把他们运送到皖北大别山深山老林里一个新兵团,上午半天抬石头修建水库,下午半天军事训练,晚上学习政治理论,一边劳动一边训练,强化完成了新兵的体能训练和纪律养成。
隔年1976年的春天,高中文化的林金湖北去分配在距唐山二百多公里,海拔一千三百五十米的延庆县佛爹山顶上的雷达站,做了一个雷达观测技术兵。
1976年,7月的26日、27日,雷达站的一台测雨雷达,以及一台空军警戒雷达,连续收到来自京、津、唐上空一种奇异扇形指状回波,这种回波与海浪干扰、晴空湍流等引起的回波都不一样,使林金湖等几个监测兵十分惶惑,然而京、津、唐的人们仍在这个强大的磁场中毫无知觉的穿行。
紧接着营部领导接到几个士兵报告:晚上在阵地巡逻,惊悚地发现,雷达基地正准备施工的一堆钢筋,莫名其妙地迸发出闪亮的光,仿佛一个隐身人在那里烧电焊;又有人反应半夜关闭的日光灯却奇怪地亮起来,在山林矿区,飘来一股淡黄色的雾,障人眼目,令人迷惑。
人们被那股异味熏糊涂了,已经看不清这世界的面目,更弄不清大自然正在酝酿着什么样的悲剧。人们眨着迷惑的眼睛,迷迷蒙蒙、不知不觉地走到七月二十七日深夜。紧接着,在北京时间1976年7月28日03时42分53.8秒,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大地震,地震持续约12秒。强震产生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造成唐山市顷刻间夷为平地,全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中断;造成242769人死亡,重伤16.4万人。
父亲所在部队接到抗震救灾的命令后,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灾区。每个班留下三人负责搭建临时帐篷,其他人全部投入到救援中。100多天的救援,林金湖刨烂了双手、跪肿了膝盖、脚板的水泡破了化脓变成了茧,不断地重复着清理废墟,挖出死者的工作。
城市的主干道两旁沿途摆满了一个个长长的塑料袋,里面都是地震中遇难者的尸体。震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唐山的气候时好时坏,一会儿烈日暴晒,一会儿大雨如注。整座城市的上空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恶臭味,闻上去令人窒息;蚊子、苍蝇成群结队四处乱飞,帐篷顶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苍蝇,电线上被苍蝇裹着粗粗的一层。三个月艰苦的救援工作,锻炼了林金湖的革命意志,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心灵得到净化,灵魂在升华,同时他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品行也得到了上级认可,再加上高中学历显得尤其珍贵,被师部定为提干预备对象,1978年保送到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进修,毕业后分配至徐州某装甲师连队任排长。
此后,24岁那年,父亲晋升到师部做作战参谋,在回乡探亲之际,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扬州城北公的女儿阮菱花,我的母亲。
古城扬州,毓贤街8号,水磨青砖砌墙,铁巴护持,结构井然,丽甍小瓦,就是阮家祠堂所在地。阮菱花系清朝扬州名士阮元之后,阮元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任太傅,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经过大浪淘沙似的历史大变革,其后代子孙,散落在扬州各乡镇,务农、经商、工人皆有,只有每年清明节期间,族人们在阮庙举办家祭,阮姓子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扬州城阮家祠堂,举行祭拜仪式,提醒着自己是名士之后,切勿做辱祖抹节之事。
林金湖与阮菱花互通书信大半年,两情相悦,相见恨晚,尤其是阮菱花写了一手硬笔书法,每封信邮寄到师部,都争相在部队的参谋、干事才俊们之间相互传阅,一个个啧啧称奇:“一个女子,书法写的如此银钩铁画、刚健柔美,真是硬气。”
此外,母亲多才多艺,还拉了一手的二胡,父亲回家探亲,母亲给他拉一首《子弟兵和老百姓》,有礼有节地抒发了人民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曲调朴实亲切,却抒发了自己对林金湖参谋的爱慕之心,让林金湖这样的铁汉子心生柔情,第一次有了要娶妻生子的迫切愿望。
隔年,我的父亲母亲决定携手同行余生,两人便相约在部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的仪式摆放在部队的食堂,战士们把大红的喜字贴满了墙上,用炮弹壳儿做了花瓶,插着一捆捆野花,散发着一阵阵幽香。林金湖穿着绿色的军装,胸口别着红花,脸上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在年轻的战友们起掌声中、哄声中,父亲掏出子弹壳做的戒指,闪烁着金光,戴在母亲的无名指上,大方地亲吻了自己的新娘。
再隔年,七月流火,八月萑苇。金秋八月,收获的季节,我呱呱落地。而此时父亲所在部队,被一纸电报征令南下,驻守在云南老山主峰,负责对~樾~轮换巡防。云雾烟瘴的林木里撒满了越方和美军部下的地雷,听母亲说过有一次冲锋号已经响起,前面工兵还在排雷,工兵最后是几人一组直接滚过雷区的,没有一个工兵活下来。父亲亲眼目睹,说那叫惨烈。有一个战地记者叫宋实诚,军报派他去采访那个工兵连,途中迷路,正好遇到父亲林金湖带的巡防队,正交谈了几句,询问了从哪个部队来,到哪里去,旁边有战士踩到雷炸雷,父亲一把抱卧着宋实诚。宋实诚左手挎相机,被炸飞,父亲的后背被炸烂,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我的父亲为救一名战地记者,踩地雷牺牲,至牺牲,未能来得及与女儿谋面。
母亲阮菱花在乡镇卫生院生产的那天,外面一阵秋雨一阵凉,芭蕉叶被雨打得吧嗒吧嗒想,本来想等到父亲换防回来给女儿取个名字,谁知道等到了一纸《革命烈士证明书》,收到证明书的那天,已是深秋,依旧下着绵长凉透的秋雨。遂,阮菱花给女儿取名:林秋雨。湖水升空变成了雨水,雨水落在脸上变成了泪水。母亲心里每天默念着林金湖,全身心呵护着小秋雨的成长,想等小秋雨赶紧长大了,一起去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去看看,去埋葬了父亲的山林去祭拜。
这是父亲嘎然而止于26岁的一生,他是那个年代有志青年的缩影,他们英武潇洒,他们前途无量,他们有耀眼的青春、炙热的爱情,最后为国殉身,变成麻栗坡烈士林园墓碑上一串串冰冷的名字,巍峨地矗立在国界异乡,与故乡隔着千山万水相守相望。
许多年以后,母亲长期郁然成疾,患病去世,父亲的女儿也进了部队,她一心想成为一个战地记者,但是和平年代,她成了一个文艺兵。不论如何,她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
那一代人的芳华终究是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