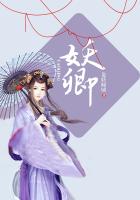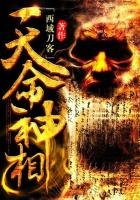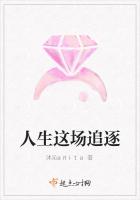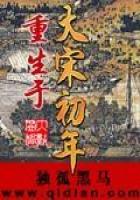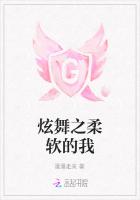之后的四场比赛,几乎就成了教学赛,陈刚队长的脚已经打上了石膏,还好不会影响今后他的球技。
低几级的替补“小混混”们被轮番安排上场感受一下“大赛气氛”,让我们欣慰的是,这些即将接班的小混混的心理素质还挺过硬,秀起自己的脚法从来不带遮掩的。
对一个问题我始终非常迷惑:为什么每一拨选拔上来的队员个子都这么矮呢?这与号称“头球队”的国家队风格明显不合拍嘛。
从这十几年的战绩来看,国家足球队的确是错了,没有秉承曾经的追求技术的路子而一味的利用身体的优势,当RB、朝鲜甚至泰国等原来的亚洲二流球队身高已经不逊于国家队的时候,我们的技术早已经无从寻觅了。
其实十几年前,所有踢球的业余球员们对技术的运用和学习是非常迷恋的,有些还刻意模仿一些著名球星的带球姿势、过人动作,当然有时也把发型、脾气也模仿了来,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脚法精湛的队员一个人过了对方后卫线的情形,但是现在,随着场地的剧减,随着市场经济的诱惑力,随着娱乐业的兴起,踢球的青年人已经很难寻觅了。
就在今年,国家16岁以下青年队竟然可供遴选的注册球员不足350人!还不及国外一个俱乐部的后备人才多。
在最后一场比赛前,我们的战绩是没有丢一球,最大的比分竟然是11:0,平均每个人进一个球,裁判竟然都不忍心吹满全场,30分钟就草草结束了。
在与最后一个对手市一中的比赛前,天空飘起了小雨,凉爽而惬意,但操场喇叭传来的消息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由于州二中擅自违规使用复读学生参加比赛,根据赛会规则,判州二中有复读生球员参加的比赛一律0:3告负。”
我们霎时全愣了,教练故意回避着我们惊异的目光,就在刚才,我们还激烈的讨论着两连冠后我们到哪个饭馆去搓一顿,现在却要承担首场比赛告负的屈辱,大家都无法接受这样的实事。
“对不起各位,我早就知道了会这样处罚,”教练很平静的对我们说到,“之所以仍然派陈刚和猫鼻子上场,是因为你们马上就要离开母校了,离开你们人生中最干净的球赛,离开你们三年来朝夕相处的队友,我不忍让你们留下遗憾。”
说完,他把我们几个老队员单独叫在一旁,让我们坐坐小队员们的思想工作,同时为了报复一中教练的可耻告密行为,让我们集体放水,故意输给市一中,让州一中夺冠化为泡影。
冯玉寿第一个跳起来不干了,我至今还记得他脸上淌满了泪水,推过他的自行车,大声的喊了一声:“为什么?”之后疯了一样消失在濛濛的雨中。18号的家是离学校最远的一个,但他每天也是训练到最晚的一个,还要骑车四十多分钟才能到家,我理解他心里的感受,宁可站着死,不远躺着活。
从此,二中再没有18号。
几个高三老队员也表示不情愿,教练无奈用恳求的语气让他们出场。
我也必须出场,因为只有我一个大门,如果我也罢赛,将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球队,组委会会给予我们队更加严厉的处罚。
教练又单独和我谈了谈,“猎户座,希望你能理解目前的局面,一会儿扑球不要太认真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
若干年后,我才明白,那是两个教练自己的战争,却用我们--二中历史上最具激情的球队做了注脚。
但是我从来没有憎恨过教练,比起今后我所遇到过的假球、假哨,真的不算什么。
比赛开始了,在我的记忆力,这场比赛是灰色的。
雨越下越大,双方象征性地对攻了20多分钟,后卫们故意漏了球,对方一个小的传中配合便抬脚射门,我假装奋力的一扑,摔倒在泥泞的球门线上,皮球在我眼前滚进网窝。
感谢雨水、泥水,遮挡了我的眼泪,我用手拼命的砸向地面,大声的叫到:“够了,够了!”
裁判提前结束了这场没有丝毫悬念的比赛,我们成了垫底。
而一中也未取得冠军,连续两届没有夺冠,重点中学的颜面扫地。
两个月后,我参加了高考,等待通知书的日子里,和这群老队友天天泡在一起打麻将或是打小霸王游戏机。
8月下旬,得知第一个要去外地上大学的叶尔兰要走,我们一起去西站给他送行。
往常很少有人来的WLMQ西站因为我们一群混混的到来仿佛喧闹了不少,旁边几对送行的家长用异样的眼神超我们这边看,还给旁边弱弱的儿子悄声说:“上车后别和那群人在一起的学生答腔啊,一看就不是好学生!”
我心里顿时笑了起来,心里想:“你家孩儿18年来学海里拼搏拿上录取通知书能高兴或者自豪多久呢?”
火车汽笛响了,尔兰从窗户里伸出毛茸茸的大手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我们一行人目送着火车远去,带着尔兰头上某次比赛留下的7针疤痕…
我分明看到火车开动的一刹那,尔兰这个从未掉过眼泪的铮铮汉子拿下了眼镜…
这一别竟然是十几年,我们再也没有相聚过,听说他毕业后留在了BJ某公司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后记:2011年,我和叶尔兰在库尔勒偶遇,之后他又去了哈萨克斯坦)
几天后,学校门口的大红榜单上面不再是空空荡荡的了,隔一会儿就有新的名字填到了上面,每个名字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可就是找不到我的大名。
陈刚-沈阳大学,当我看到队长上榜后,心里顿时一阵狂喜,竟然他在得知此消息后远没有像我这样神经兮兮,原来他想走老家肇庆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没想到重点本科的冷门把他给补录了。
临走的时候,我送给他一支钢笔,没想到再见面时已经过去了9年。